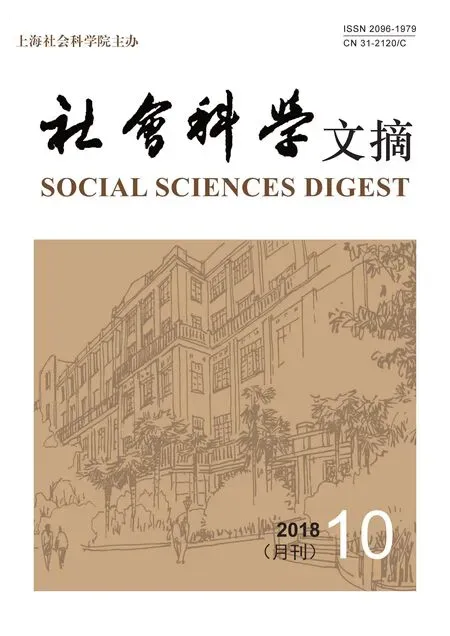美印视角下的“印太战略”:政策限度及中国的应对
自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主动调整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推出以空海一体战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主的涉及安全、政治、经济等内容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特朗普主政后,美国退出TPP,“重返亚洲”无疾而终,为了应对战略形势变化,奥巴马执政后期近乎销声匿迹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被重新拾起。从亚太到印太,最大的变化在于将印度纳入战略视野,企图在西南方向及印度洋地区构筑对中国的“合围”。
同时,源于广泛的相似性与地理毗邻,印度对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存在“攀比心理”。在中国先于印度崛起情境下,印度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强烈。中国海军索马里海域的护航行动、中巴安全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国家的发展与落实等正常的安全、经济交流合作,均被视为针对印度的围堵、遏制甚至挑衅。作为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开展务实行动与广泛合作的回应,印度开始寻求在东亚-太平洋区域平衡中国影响的合作方。以2017年6月莫迪访美为标志,印度开始接纳“印太战略”,寻求在从美国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广阔空间内回应中国的行动并实现印度大国抱负的理想,客观上让美国成为未来中印关系发展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美印战略诉求的契合
受现实主义支配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人性本恶的假定前提下,要求主要大国对实力对比的变化做出反应。美印两国投身“印太战略”,核心诉求是应对中国崛起,不论是美国的对华遏制策略,还是印度的对华防范心理,都是战略层面对中国崛起的“条件反射”。
(一)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的美印安全合作
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原则性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并试图把这一概念理论化。2017年5月,特朗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演讲中首次提到原则性现实主义:“我们正在采取原则性现实主义(We are adopting a Principled Realism),(它)根植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我们将根据现实世界的结果做出决定——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以经验教训为指导,而不是僵化思维的限制。”此后在阿富汗以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时,特朗普又多次提出原则性现实主义概念。2017年底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篇明义:“本国家安全战略优先考虑美国利益”(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uts America first),接着提出“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基于……一种原则性的现实主义战略,是以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导向的”。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印军事安全合作就已经逐渐加强。2015年奥巴马以主宾身分出席印度共和国日阅兵,不但成为第一位受邀参加印度国庆活动的美国总统,也是唯一任内两度访印的美国总统。2016年印度防长两度访美,先后与美方达成两项重要协议:美国给予印度(非北约盟友的)“主要防务伙伴”(Major Defense Partner)地位;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特朗普上台后,两国很快就密切防务关系达成共识。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印度的“主要防务伙伴”地位再次进行了确认。2018年8月,美国宣布印度成为全球第37个,也是亚洲继日本和韩国之后第3个获得战略贸易许可(STA-1)地位的国家。“主要防务伙伴”与STA-1的落实,使印度获得原本仅向美国盟友开放的广泛军民两用科技,终结了自1998年印巴核试验以后美国对印度施加的技术封锁。
(二)对冲防范“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逐渐丰满、合作逐步落实,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版图不断延伸,印度洋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美印两国在“印太战略”构想中找到了相互需要的动机和互为凭借的利益契合点。对美国来说,太平洋-印度洋航线长久以来都处于其控制之下,链接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区——亚太,与世界主要石油资源生产地——中东的关键航线不可能拱手让人。虽然长期内,印度崛起与实力增长也会对美国控制大洋的战略安排造成威胁,但至少目前这一潜在威胁还不足以与中国崛起的现实紧迫性相比较。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如果美国直接进行干预,一是目前美国国内的政经实情恐怕无法支撑,二是不少沿线国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国盟友,都无法认同。因此,尽可能使用离岸平衡策略,拉拢印度参与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就是合理选择。美国拉印度“入伙”印太,既可以利用中印这两个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矛盾,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又可以利用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矛盾,防止亚洲的整体崛起。
相较于美国,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要更为复杂。一方面,印度经济发展面临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外国投资的增长,这方面“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都是理想合作对象;另一方面,南亚与印度洋地区历来被印度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域外国家的介入都会引起印度的高度警惕,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印度始终反应冷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不乐见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但受限于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无力提供替代性的区域合作选择,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季风计划”至今仍没有具备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综合而言,印度虽然渴望获得参与“一带一路”与中国密切合作所能带来的经济好处,但实现“印度的印度洋”的战略企图,以及对所谓“珍珠链”、中国“包围印度”等等战略设想的地缘政治忧虑,却促使印度选择接纳美国抛来的“印太战略”“绣球”,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
美印战略诉求的分歧与“印太战略”局限性
近20年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部分归功于全球化进程中区内各经济体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合作,以中美贸易和东亚生产网络为核心的亚太经贸体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让所有参与国家均从中获益。相较而言,“印太”并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经框架,其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经济内涵与亚太概念迥异,战略构思中还包含若干矛盾之处。
(一)美印与中国博弈的“两盘棋”
中美博弈,是典型的守成大国-崛起大国博弈,涵盖面广、内容复杂、情节波折。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曾经试图把中国的发展纳入西方轨道,在经济、政治体制乃至价值观等方面演变中国。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超过预期,并在实践中发展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变的企图早已破产。同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近些年民粹主义、极端政治冲击,美国曾经对中国拥有的不对称实力优势正在缩小。在安全方面,虽然公认中美军事实力仍存在巨大差距,但以军事资产衡量的绝对差却逐年缩小,部分领域中中国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更重要的是,当前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在零和思维指导下不加遮掩地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一方面阻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主动挑起与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纠纷。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建设聚焦合作与发展,秉持平等、开放、包容原则,本着量力而行态度与沿线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其中蕴含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治国理念,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中印博弈至少在目前阶段仍然是区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发展经济,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必不可少。对印度来说,一方面中美博弈必然增加印度在两国中的回旋空间,保持中美斗而不破格局,同时与中美谈判博弈获取好处,可以说是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印度自尼赫鲁时期就拥有强烈的大国抱负,历史上还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在已经成为公认的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中重要国家的今天,印度保持独立自主大国地位是必然选择。与美国拉拢印度搞“离岸平衡”不同,印度的战略目标在于实现“印度的印度洋”,这一具有排他性的地区战略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不相符。即使印度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接受“印太战略”概念,对建立美日印澳四国或美日印三国安全合作机制兴趣上升,但完全跟随美国,把自己降格为美日关系中日本那样的从属地位,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二)“印太战略”与美国优先存在矛盾
从历史经验看,当守成大国试图构建针对崛起大国的遏制包围圈时,对同盟体系中相对落后国家的让利与扶持必不可少。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对西欧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援助,最终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冷战格局及其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远东方向的战略围堵需求,促使美国采取扶持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政策,最终成就了日本经济复苏与亚洲四小龙崛起。而在今天的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几无可能,甚至一般的自由贸易原则都面临着国内政治的巨大压力。
事实证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并不是特朗普团队“拍脑袋”生造的竞选口号,而是有着广泛社会经济基础的现实诉求。美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主要源于经济不平等。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公布的数据,1989—2013年间美国不同阶层家庭财富增长差异巨大。2013年,美国最富裕10%的家庭占有总财富的76%,排名后50%的家庭仅仅占有总财富的1%。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虽然美国试图在“印太战略”中拉拢印度,以离岸平衡策略制衡中国,但指望美国像二战后那样通过大规模援助与贸易让利手段来构建新的政治安全同盟体系的可能性显然较小。《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维护美国“四项关键利益”(F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即“美国人民和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力量求和平以及增加美国影响力”。在特朗普政府的任务清单中,美国优先或者说美国国内事务优先的重要性远超“印太战略”,当两者利益出现抵触时,保证美国优先是更符合其政治经济需要的选择。
中国的应对
美国拉拢印度加入“印太战略”,走的是冷战思维指导下遏制与对抗的老路。而印度出于平衡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面回应,希望从美方的拉拢中获得实际利益。同时,印度对于介入中美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战略博弈始终保持谨慎态度,不轻易选边站。考虑到美印两国的战略目标差异,特别受制于美国优先原则的政策限度,预料“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将比较有限,美国借助印度实现“离岸平衡”遏制中国的目标较难实现。
(一)以务实合作增进互信关系
随着2018年4-6月间莫迪两次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两国最高领导人引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的预期有所增强。作为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印都需要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捍卫全球化下的发展权益,在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方面有共同需求。
事实上,中印作为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天然地担负着落实发展权利的任务。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印都支持多极化发展趋势,支持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两国联手合作逐渐增加。2018年6月,莫迪首次以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正式展开。在此之前,中印已经在金砖国家、G20、联合国气候谈判等重要国际治理框架下都展开了务实合作。长期来看,政府与民间的务实合作有助于不断提升中印两国的相互信任关系,筑起两国关系长久发展的基石。因此,在两国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印双方需要基于共同需求,在多边和双边层面上继续加强务实合作,中印增强互信的前景将更加值得期待。
(二)加强中印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
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发展落后问题,基础设施发展落后导致的广义贸易成本成为制约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远比关税的负面影响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5—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年均资金缺口在0.5-0.75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亚太30个发展中经济体在2010—202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其中南亚为2.3万亿美元,而印度则占南亚的92%,达2.17万亿美元。
中国是“印太”地区经贸合作潜力最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范围最广的国家。从资金实力、技术水平、工程经验、适用性等各个方面来看,对于印度这种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和幅员辽阔国家的大规模基建,中国的经验显然非别国所能媲美。同时,中印基础设施合作的机制也已经具备,“一带一路”与亚投行都是现成的选项,只要中印两国加强互信,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融资领域的合作可谓顺理成章,进而构成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2015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协定》签订之时,印度以83.67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7.5%投票权成为亚投行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反映了印度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求,也充分表明了印度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的意愿。
(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长期以来,南亚经济发展波动性大,抗风险能力较弱。印度作为南亚发展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同样面临着贸易壁垒高、自由化水平低的问题。中国目前已经与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签署双边FTA,其中中巴第二阶段FTA谈判已经启动。另外,中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FTA也已经启动前期协商,唯独与印度尚无任何双边贸易安排。中印贸易近些年保持了增长势头,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较为显著,2017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517亿美元。有鉴于此,印度对于谈判中印FTA的热情不高。
然而,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制造业水平提升,这必然要求贸易条件的更大改善,在中印双边FTA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两国共同参加的区域/多边贸易安排就成为了最佳替代方案之一。在美国退出TPP之后,太平洋-印度洋区域内最具前景的自由贸易安排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印两国都主张迅速达成RCEP谈判,实现第一阶段成果,在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当下发出亚洲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坚持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声音。一旦RCEP得到落实,中印经贸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两国共同对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的立场也将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