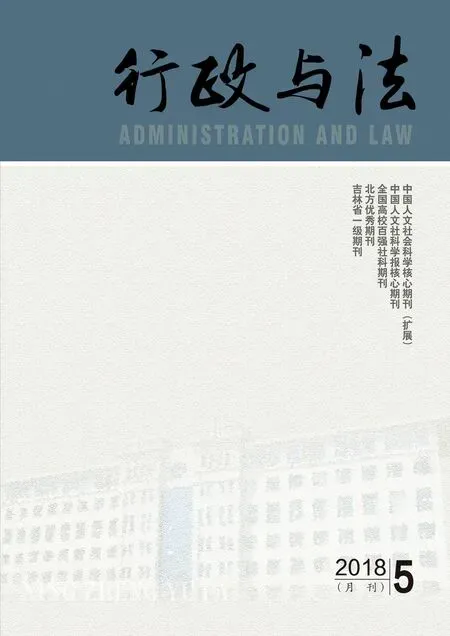绿色财产权理论基础之探析
□ 王晓翔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8)
绿色财产权理论①该理论主要讲述的是所有权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日本学者吉田邦彦将Green Property翻译为绿之所有权,也称为共同体的、环境主义的所有权论。参见(日)吉田邦彦.民法解释与动摇的所有论[M].有斐阁,2000.440.是在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后逐渐发展形成的,并由美国学者拜瑞尼于1990年首次提出。[1]在传统自由主义产权理论无法解决当今环境问题的情形下,绿色财产权理论旨在改革现有的财产权制度,在承认权利人享有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强调隐含于财产权中的对整个共同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我国,雾霾肆虐、土壤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化石等不可再生燃料过度消耗等环境问题正日益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对此,十八大报告首次完整阐述了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的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要求人类遵循自然规律,推行绿色发展。
当下,正值我国民法典编纂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新时代的民法典,它必须回应现实,反映环境问题的时代特色,同时还应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既有成果,以体现后发优势。笔者认为,美国绿色财产权理论所蕴涵的绿色思想符合我国绿色化发展理念,可以为我国民法典特别是物权法的编纂提供些许启示。
一、环境伦理学的形成及发展
环境伦理关心的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而言就是保护自然环境,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和永续发展。[2]这种伦理观深深契合了绿色财产权理论的内涵,因而成为构建绿色财产权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伦理学的建立
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被认为是环境伦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始人。
阿尔贝特·施韦泽在他的人道主义实践中,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要求人们敬畏自身以及自身之外的生命意志,并由此提出了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即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的发展,恶是毁灭和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3]“敬畏”一词同时含有“敬重”和“畏惧”的意思,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虔诚态度。所有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都是神圣的,都具有生命意志,因此,人应当像敬畏自己生命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以往伦理学的错误在于只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人与所有生命的普遍伦理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已。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环境伦理学的贡献在于:他把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纳入到了伦理学的研究范畴,使伦理学变得全面、完整。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那个时代首先看到并揭示出大自然奥秘的人之一,[4]他于1948年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系统阐述了土地伦理学,被视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范式,对当代环境伦理学,特别是美国的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5]奥尔多·利奥波德对环境伦理学的贡献在于:他在施韦泽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学的整体性观点,继续扩大了伦理共同体的边界,将之扩展及于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可以将这些要素统称为“土地”,并将人类视为只是相互依存的土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6]此外,他把对自然的保护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价值尺度,这种伦理以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一种基于整体主义的伦理学。[7]
(二)环境伦理学的不同发展阶段
依据所确认的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不同,可将环境伦理学分为四个主要的流派,即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8]而这四个流派的划分也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不同发展阶段。
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这种伦理观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可以主宰世间万物。人类中心主义完全根据人类的利益来判断对与错,即它主要考虑一件事对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而对环境的关心则完全附属于这种对人的关心。[9]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五种: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灵魂肉体二元论、理性优越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①自然目的论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理念是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大自然就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在上帝的所有创造物中,只有人是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只有人才具有灵魂,他是唯一有希望获得上帝拯救的存在物,所有的创造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的,它们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灵魂和肉体二元论认为人是一种比动物和植物更高级的存在物,因为人不仅具有躯体,还拥有不朽的灵魂或心灵,而动物或植物只具有躯体;理性优越论认为只有人才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因而只有人(因拥有理性)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人类对待它们的行为不会影响理智世界的实现,因而把它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恰当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和人的特殊地位的证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或理性的某种变种。详见: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86-93.而无论何种表现形式,人类中心主义均认为伦理原则只适用于人类,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重要 (甚至唯一)的价值,是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因而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关心只限于那些对人类有用的自然物,而且对这些自然物的义务只是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人类只要根据“开明自利”的原则来指导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0]然而,依据开明自利原则指导和调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使人类忽视甚至毁灭那些对人类没有用处但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物,再加上人类往往受利益的驱使而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一系列环境危机的发生。
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分别由澳大利亚著名伦理学家辛格和美国哲学家汤姆·里根所倡导,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将道德关怀的范围由人扩展到动物。动物解放论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充分条件,也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条件,平等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而不管这个利益的主体是谁。[11]这种理论虽然主张平等原则,要求对所有动物给予道德关怀,但其并不认为应对所有动物以同样的待遇,而应根据不同动物对快乐和痛苦的感觉能力不同而区别对待,即对感觉能力强的动物关心则多,对感觉能力弱的动物关心则少。动物权利论,顾名思义,即认为动物也拥有权利,这种观点认为只有赋予动物以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无谓伤害行为。虽然动物解放/权利论扩大了传统伦理的范围,但其保护对象主要是被拘禁于动物工厂中的家畜以及实验室和动物园中的动物,而未涉及野生动物,而且只关注动物个体的利益和权利,忽视了动物个体也只是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个体利益的实现有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此外,这种伦理观为了提倡对动物的保护而主张素食主义,违背了人类天生杂食的本性,也不符合自然规律。
生物中心主义主张尊重生命个体,并给予道德考虑,这种理论继续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将之及于所有生命,而非仅仅是动物。生物中心主义又可细分为道义论的生物中心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以美国哲学家保罗·沃伦·泰勒为代表[12]的道义论的生物中心主义主张依据人们行为的性质(是否体现了尊重自然的态度和原则)来判断他们对待其他生物行为的道德价值。所有的自然生物都是自身有利益的实体,而诸如沙子、石头、人造的机器等非生命物质不拥有自己的利益,因而它们不会因其利益得到促进而受益,也不会因利益的受损而受害。[13]凡是拥有自己利益的实体,都拥有固有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人对它所做的评价,也独立于它在事实上是否促进了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目的或是否有助于其他存在物的善的实现,都应当成为我们尊重的对象。[14]该派学说在尊重生物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生物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其由四个信念组成: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员;人和其他物种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有机个体是生命的目的中心;人并非天生地优于其他生物。[15]以英国学者罗宾·阿提费尔德为代表的[16]后果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认为,人们行为(包括决策)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它们给受到影响的生物所带来的可预见的后果,如果这种后果超过行为所带来的恶,那么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生物中心主义的优越之处在于:突破了上述动物解放/权利论的局限,把道德关怀的范围同时投向了野生的动植物;缺陷在于:当人们要在保护一种普通生物和一个濒危生物之间做出选择时,生物中心主义并没有给人们优先考虑濒危生物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此外,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的只是生物个体,忽视了共同体的存在,它和动物解放/权利论一样,也没有认识到每一个生物个体只是生态系统的一员,而且整个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还有非生物的存在。
受现代生态学的启发,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由生物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它更加关注共同体而非单个的生物个体的利益。生态中心主义的主要学说有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美国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以及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主要秉承以下信念:其一,自然世界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应当给予自然世界以道德关怀。其二,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其三,重视价值观的改变,认为目前的环境危机源于现代人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因而环境危机的解决必须改变现有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17]
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
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一书中建构的土地伦理对于美国的环境伦理学和财产法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他的土地伦理至少在美国的财产法中被认为是关于环境伦理的最经典表述。[18]绿色财产权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也深受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影响,其内涵以及旨在实现的目标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密切相关。实际上,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为绿色财产权理论提供了基础,绿色财产权理论也主要是寻求一种对生态土地伦理的法律效力。
(一)奥尔多·利奥波德对伦理范围的扩展
奥尔多·利奥波德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伦理用来处理人与土地关系,也没有一种伦理用以处理人与土地上所生长的动物的关系;因此,土地仍好比奥德修斯的婢女一样,仍旧只是一种财产。[19]以经济因素主导的人与土地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则是人类是征服者,而自然只是被征服的对象,如此使得人类对自然的使用变得恣意。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生态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生活。[20]因此,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为了保护生存环境,应当扩大伦理的范围,而这也正是其土地伦理的目的所在,即除了人类之外,道德关怀还应当及于土壤、水、植物、动物,所有这些要素可以统称为“土地”。
(二)土地共同体和土地金字塔概念的提出
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在人和人构成的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之外还存在一个由人类和土地构成的共同体,他将其称为“土地共同体”。这个土地共同体指的就是整个的生态系统,包括人类、土壤、水、动物和植物等。在土地共同体之中,人只是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普通成员,而不是征服者或者统治者,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对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以及对共同体本身加以尊重。接着,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土地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金字塔”的概念,并以此来阐明土地共同体结构的复杂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对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运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个土地金字塔中,最底层是土壤,其上是植物层,植物层依赖于土壤,昆虫寄居于植物层上,鸟类和啮齿动物又在昆虫层之上,以此类推,各种动物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排列至金字塔的最顶层。[21]土地金字塔中所有的生物都依赖植物以维持生存,而植物的生存又依赖于土壤。土壤孕育了植物,为植物的生存提供了空间以及植物生长所需的一切条件,植物经光合作用,从太阳那里获得能量,能量随着食物链的引导在金字塔各层中不断向上流动,而生物在死亡后经由微生物的作用腐烂并重新回到土壤,从而实现能量的循环以及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随着物种的不断进化,土地金字塔的层数也在逐渐增加,食物链的环节也在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延长,如此则增加了金字塔结构的复杂性,而能量的流动和金字塔的稳定正是依赖于金字塔结构的复杂性。当土地金字塔具有复杂的结构时,它可以对外来的干扰做出调节,以适应这种变化,从而使整个生态系统保持动态的平衡和稳定。在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发展和进化是缓慢的,因此土地金字塔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些变化,也就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动,而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以及人工合成的各种化学物质却可使土地金字塔发生空前的、超出其自身调节能力的巨变。因此,其从历史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激烈的人工干预模式使用得越少,金字塔在重新调整过程中获得成功的概率就越大。[2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金字塔启示我们,即使渺小如微生物等低等生物,它们也是土地共同体的基本成员,也与作为高等生物的人类一样;如果没有人类的存在,它们仍能生存和运行,但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却将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共同体的金字塔。因此,应当尊重土地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尊重共同体本身的协调发展,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进而保证土地共同体结构的复杂性,而且人为的干预不应当超过土地共同体的自我调节限度。
(三)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整体论思想
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的结尾处指出:一件事情,当它倾向于保护土地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23]这一结论给出了一个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的标准,而这一标准也体现了奥尔多·利奥波德保护土地共同体的整体论思想。这种整体论的思想认为,并不存在独立于生态系统各种关系的个体,个体的价值是由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决定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着眼于保护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而非如以往伦理学保护的只是每一个生物的个体。人类对共同体的伦理义务在于保护土地共同体结构的复杂性,以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良性运转。因此,从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生物的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因而对于属于珍稀和濒危物种的生物个体应加以特殊的道德关怀,这也弥补了上述生物中心主义的缺陷,为人类优先考虑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三、构建绿色财产权理论的环境伦理
(一)人类认识和保护环境的不同发展阶段
正所谓“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时,如何理解和看待周遭的事物以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它将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可能视人类为万物的主宰,也可能将人类视为整个土地共同体的一员,不同的理念将催生不同的行为,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保护也和伦理的发展过程一样,经历了一个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苏萨·内梅内格尔、阿克塞尔·特申克在《认真对待自然权利》一文中揭示了国际环境法发展史上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也从伦理角度阐明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转变。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一阶段是以当代人的自身利益作为环境保护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阶段,人类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恢复的目的或动机主要是出于功利性的认识,认为这种对自然的保护可能符合满足当代人最大利益的目标。[24]这种对自然的关心和保护是以人类为出发点的,因而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这种保护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前提的,也被称为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将人类的子孙后代也包括进来了,认为人类的后代也可能受益于自然的保护和恢复,当代人的责任是保护我们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维持生命的环境资源的质量,因而环境保护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当代人的利益,还在于保护人类子孙后代的利益。[25]然而,尽管较上一阶段的纯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增加了人类的子孙后代,但这一阶段还是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在此阶段人类仍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的利益将决定环境保护的程度。第三个发展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生物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不管这种价值能否为人类带来利益。[26]这一阶段有别于上述两个阶段,该阶段已经进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称为生物中心主义,人们保护环境的目的不仅着眼于人类自身,还包括承认自然生物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同时,该文还预测了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是生态中心主义,这一阶段会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人类将认识到自然的非生物因素所具有的固有价值,对环境的保护也将是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动态平衡,以使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控制在自然可自我调整的限度内。[27]
(二)绿色财产权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认真对待自然权利》一文中描述的国际环境法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和其预测的第四个阶段与伦理的发展过程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发展相一致。财产法规则的制定与这些伦理的不同发展阶段休戚相关,财产法的发展也深受这些伦理变化的影响。
传统的自由主义产权理论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它以当代人的直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即以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伦理基础,自然要素的价值仅体现在它们能增进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安全等方面,而忽视了自然要素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这种财产权理论影响下,人类的行为可能造成某些对人类无益甚至有害而对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起重要作用的自然要素的灭绝。而灭绝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意味着失去物种的多样性、失去美、失去一种遗传资源、失去一个自然的奇迹。[28]物种内单个个体的消亡尚可以由其他的个体来替代,但物种却是无法替代的,它的灭绝意味着物种的永远消失。而由于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具有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些对人类无益的某些自然要素遭到灭绝,势必影响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并将因此减弱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此外,自然的经济价值还取决于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些看似对人类无益的事物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用途等待人类发现。例如青霉素的发现,青霉素原先只不过是一种对人类毫无用处的霉菌,但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于1928年发现了它具有的天然抗菌能力并使其大为增强后,青霉素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9]因此,如果人类只顾眼前的功利,不考虑长远的期待利益和整体利益,必将不顾一切掠夺资源以满足自己当下发展的需要,从而加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传统的自由主义产权理论无法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与此相对,绿色财产权理论的构建则深受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或者说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影响,这种理论承认生态系统中所有环境要素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只是土地共同体的一个普通成员,人类和其他土地共同体成员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绿色财产权理论要求人类尊重土地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同时也尊重共同体本身。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名的土地伦理中还提出了判断一件事情(一项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即其是否有利于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而我们都知道生态系统本身是动态的、不稳定的,①实际上,生态学的经典范式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或者是平衡、稳定的或者就是走向稳定。英国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先驱乔治阿瑟·乔治·斯坦利是第一个定义“生态系统”一词的人,他在1935年写到:“生物体和无机物都是相对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此外,提出了“生态营养层级”概念的美国生态学家莱曼德·劳拉尔·林德曼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些早期的生态思想家构想了一个稳定的理想体系,他们把自然看成是一个追求平衡的系统,其意味着如果免受人类的干扰,生态系统将保持平衡。而生态学的一些学科获得的实证数据却与上述的经典范式不同,生态学家指出生态系统本身经常受到各种干扰,包括火灾、暴风雨、洪水、干旱、虫害等,这些干扰影响了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分布和数量。这导致了人们观念的改变,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生态系统是开放的、不一定处于平衡状态,并承认干扰是生态系统自然的且必要的一部分。详见:Judy L.Meyer,The Dance of Nature:New Concepts in Ecology,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69,Issue 4(1994),p.876-878.因而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说的共同体的稳定性应当将其解释为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较为合理。因此,对人类而言,如果一项行为是正确的,那么该行为则倾向于保护土地共同体的完整性、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使生态系统有能力通过自我调节适应外部的干扰;反之,该项行为则是错误的。这种对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将对人们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绿色财产权理论还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影响,这种伦理将人类的子孙后代囊括在道德关怀的范畴内,强调代际公平,认为人类的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不能因为当代人利益的满足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因此,绿色财产权理论构建的环境伦理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或土地伦理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整合,它吸取了二者的积极因素,并规避了二者的不足与缺陷,因而是对二者的超越,是一种科学的环境伦理观。
[1]J.Peter Byrne,Green Property[J].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Vol.7,Issue 2(Summer 1990).239.
[2][17]杨冠政.环境伦理学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9-20,106.
[3]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M].陈泽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28-129.
[4]Eric T.Freyfogle,On the Trail of the Land Ethic[J].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Vol.1992,Issue 3(1992).920.
[5][8][10][11][12][16]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56,86,93,95,109,109.
[6]Aldo Leopod,A Sand County Almanac:With Other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6.219.
[7]陈瑜华,王建民.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研究述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71-75.
[9][28][29](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62,291-292,124-125.
[13][14][15](美)保罗·沃伦·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M].雷毅等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44,46,62-63.
[18]Terry W.Frazier,The Green Alternative to Classical Liberal Property Theory[J].Vermont Law Review,Vol.20 (Winter 1995).324.
[19][21][22][23](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舒新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209,220,225,231.
[2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7.304-305.
[24][25][26][27]Susan Emmenegger,Axel Tschentscher,Taking Nature's Rights Seriously:The Long Way to Biocentrism in Environmental Law [J].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Vol.6,Issue 3(1994).552,562-563,56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