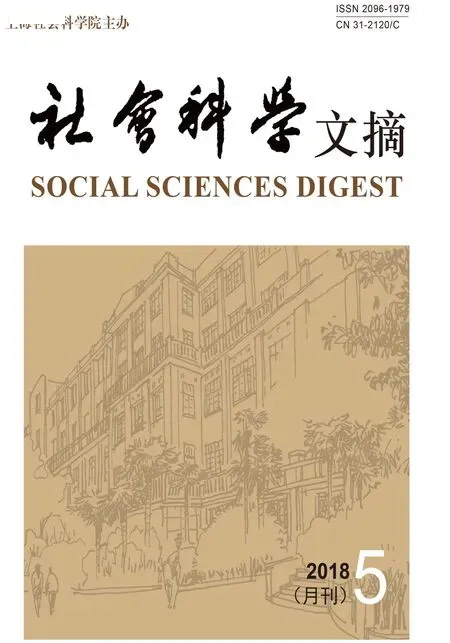国家治理生态: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法合治”
——兼与戴茂堂、余达淮两教授商榷
文/邹海贵
【作者系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自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并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以来,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在此,笔者从分析“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命题的限度、“德法合治”是否排斥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等四个问题入手阐述国家治理生态问题,并与戴茂堂和余达淮两位教授商榷,以求教于同仁。
“德治”“法治”等概念的正本清源
(一)何为德治
在学理上,德治有广义的德治(rule of moral)和狭义的德治(rule by moral)之分。广义的德治,是与法治(rule of law)相对立的范畴,是道德主义的,其核心是强调道德高于法律,道德统摄法律,法律依附于、从属于、服从于道德,道德成为核心的社会控制手段。广义的德治不等于人治,但是具有蜕变为“人治”的内在逻辑和实践取向。人治(rule of ruler)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和模式,是治者之治,根本特征是强调君主至上,统治者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与独裁、专制具有内在相通性。人治作为一种整体模式,既强调德治(rule by moral),也重视以法治民。广义的德治走向人治的内在逻辑在于:德治往往强调治者的德性,强调贤者的治理,治者为巩固个人的统治,不惜在道德上神化自己,进而走向专制和集权政治。狭义的德治,即强调道德规范约束的“德治”,其核心是强调依靠道德维护社会秩序,治理国家和社会。可见,狭义的德治内在于人治和法治这两种国家治理模式之中。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德治可以分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简言之,传统德治建立在传统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基础上,是与传统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相契合的德治,相当于广义的德治。现代德治相当于狭义的德治,其基本内涵是:追求良性的道德秩序,强调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道德的教化功能,也强调官员道德的作用。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有本质的区别。
(二)何为法治
法治,首先表达的是政治模式的性质,是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是“政道”而不是“治道”(治术)。所以,法治不同于法制(rule by law),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狭义上仅指法律制度(legal system),法制与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法制既可以与专制相连接,也可以与民主相结合,既可以内在于人治,也可以内在于法治。法治是一种民主政治理想和政治模式,是一种与专制、独裁相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人民主权、权利平等是其价值灵魂。法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法治起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物,所以法治主要指的是现代法治。法治虽然在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其核心不是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而是强调国家治理中法律的权威性、至上性和有效性,强调法律内容的合理性、正义性,强调良法的制订及其普遍服从。法治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以“人民主权”或“人民民主”为核心;二是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人民的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与保护;五是政府国家置于监督之下并严格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能简单转换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在逻辑上,道德与法律以及德治与法治,这两组关系具有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源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但是,两组关系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严格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简单地把前者转换为后者,或者把后者转换为前者,否则就会犯逻辑上的错误。戴茂堂教授在论述这两组关系时显然认可这种转换,所以在论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把两个命题牵扯在一起,提出了“法律或法治具有强制性”“法律或法治具有外在性”“法律或法治是刚性的”“法律或法治是惩处性的”等命题。显然,这些论述似是而非。法治何来“强制性”“外在性”“刚性”“惩处性”?
(一)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和区别
基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道德与法律是紧密联系的。首先,道德与法律同根同源,道德的产生早于法律,法律起源于道德;其次,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法律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最后,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是人类自由的价值理念,两者在内在价值上具有统一性。道德与法律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道德与法律在性质、功能和外在形态等方面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凸显各自存在的独特性,也各自弥补对方的不足。从基本属性来看,道德具有自律性,法律具有他律性,在价值秩序上,道德高于法律;从表现形式来看,道德具有模糊性,道德没有独立存在感性空间域,它“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高兆明语),而法律具有明确性,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众;从实施手段来看,道德主要依靠舆论、良心和习惯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从效力的角度来看,道德具有柔性,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而法律具有强制性和刚性,以其威慑力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从控制的范围来看,道德规范涵盖的范围广,法律规范的调控的领域窄,主要是人们的“底线道德”领域,重点是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
(二)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整体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德法合治”,或“德法互济”,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关系,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首先,德治与法治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经济基础。其次,法治是德治的基础和保障,以法治为基础和后盾的德治才不会导致人治;德治对法治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德治可以涵养和强化法治精神、法治文化,促进法治建设。最后,“德法合治”并不排斥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两个命题的限度
(一)“道德法律化”命题的逻辑偏差与实践风险
首先,“道德法律化”的命题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问题。化,易也,本义指改变、变化。学界对“道德法律化”比较一致的理解是,“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可见,这一概念既不能理解为把道德转变为法律的性质或状态,也不能理解为把道德作为法律普遍推广。如果道德的性质转变为法律,道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道德具有层次性,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可以转化为法律制度,一些低层次的道德义务可以转化为法律义务,但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也许永远不可能转化为法律,如果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以转化为法律,那么道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其次,在实践中,主张道德法律化容易导致道德泛化(道德万能)、法律泛化(法律万能)两种看似悖论的风险,这样不仅危害道德建设自身,而且危害法治建设。道德(立法)泛化的实质是道德万能论,一方面会侵犯社会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权利,挤占其生存空间,引发社会对立、社会分裂;另一方面也无助于社会道德秩序的形塑,可能带来普遍的道德绑架和道德虚伪。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间接方式对道德行为进行激励和保护,而非通过直接的道德法律化。法律泛化的实质是法律万能论,认为道德不可靠、不可控,主张把道德尽可能全部法律化,主张完全依靠法律的强力进行社会控制和国家治理。
(二)“法律道德化”命题的理论缺陷与实践风险
关于“法律道德化”,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比较一致的理解是,“法律道德化”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守法主体把守法内容转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正如罗金远、戴茂堂等指出的,“法律道德化的过程就是法律主体化、心理化的过程,就是外在的制度、规则内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品质、道德良心的过程”。与此同时,戴茂堂、左辉等也提出了他们的第二种理解:“法律道德化”是指法律必须从道德中吸取力量,道德为法律提供价值保证和合法性证明。这两种理解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理解不仅存在语义上、逻辑上的缺陷,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前者侧重于守法的过程,而后者侧重于立法的过程。对于第一种理解,本质上阐述的是个体守法的境界,个体守法的境界如同个体守德的境界有三个层次,即他律的守法境界(消极守法)、自律的守法境界(积极守法)和自由的守法境界(自觉守法)。“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无疑只是个体守法过程中的一种自律或自由境界罢了,无需“法律道德化”的命题来支撑。进一步说,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达到自由的守法境界,这难道是道德的吗?对于第二种理解,强调“法律必须从道德中吸取力量,道德为法律提供价值保证和合法性证明”,其实质是强调良法(善法)之治,也无需“法律道德化”的命题来支撑。
因此,“法律道德化”作为一个命题本身存在明显的分歧,也很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有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风险。如前所述,如果“法律道德化”理解为把法律的性质转变为道德,那么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与此同时,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来说,一些法律规范可以转变为道德规范,这是合理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的法律规范都可以转变为道德规范。在实践中,盲目强调法律道德化,混淆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无异于主张回到传统社会的“德治”(人治)和“礼治”时代。
国家治理生态: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法合治”
构建我国国家治理生态,必须坚持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德法合治”或“德法互济”不等于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余达淮等认为,法律与道德不是一对矛盾,法治(依法治国)与德治(以德治国)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对矛盾,因此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原理。在此基础上,余达淮等认为法治与德治存在重点之分是不科学的,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次之分、重点之别,两者同等重要。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居于主导性地位,法治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生态的核心标志和关键环节。
(一)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的地位和德治(传统德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闭、静止的、一元的熟人社会,道德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是一个社会结构简单而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开放、流动的、多元的陌生人社会,经济生活无孔不入,道德生活边缘化,是一个社会结构复杂而人际关系简单的社会。与此同时,现代道德的性质和生存机制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范式不可同日而语了。传统道德是精英式权威道德,是一种等级伦理秩序的体现。现代道德是契约式道德,追求的是良序社会,道德与政治分离,是一种个体权利平等的伦理秩序。因此,法治也就成为现代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模式。所以,现代社会是以“法治性”作为核心标志的,法治才能立国,法治才能稳国,法治才能强国。李建华认为,“法治在现代社会所处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也是我们实现‘以德治国’的社会前提,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张文显指出,“在现代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高兆明阐明,“当下,宪法法治是唯一能够将全中国人民凝聚一体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宪法法治秩序是唯一能够使这个社会良序演进的秩序”。
(二)法治的主导性地位是由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人治”历史的国家,权利意识缺失,而官本位、权力崇拜等人治理念根深蒂固。当前制约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法治问题,而不是德治问题。作为德治问题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社会良性伦理秩序和道德建设的期待和需求与社会道德失范问题频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界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陈金钊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独到的、有深度的分析,他指出,我国当今社会虽然各种矛盾云集,但从矛盾主体的维度可归结为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三种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可以转化为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利三种法律关系,这些矛盾的化解路径及法律关系的调整非法治莫属。由此可见,作为法治问题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创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与政治、行政和社会生活领域内的权力滥用、权力冲突和权利侵犯等现象盛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制约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
以上分析表明,构建国家治理生态的根本路径是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包括“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特别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国家,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注重发展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治与德治的密切协同,以此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新征程,习近平特别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法治中国”思想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强调法治的主导性地位,强调坚持重点论,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性战略,并不是主张法律万能,也不是主张不要德治。“德法合治”的科学内涵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相互协同,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一言以蔽之: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法合治”才真正构成我国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