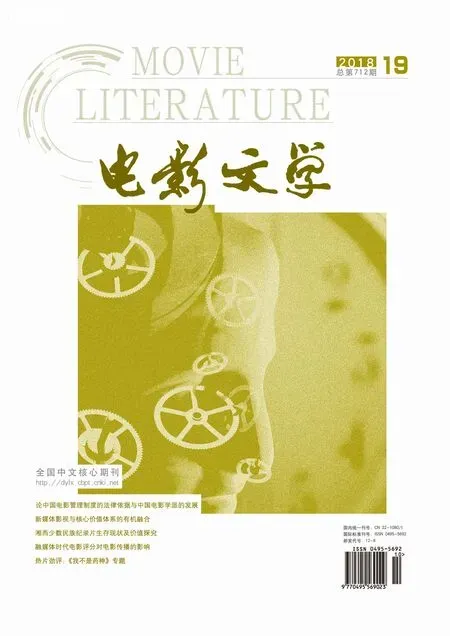李沧东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赵 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诗人李沧东:以女性视角追问人生意义的典范
李沧东是韩国电影史不能绕过的一座丰碑。他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导演,由其亲自执导的电影只有6部,但这些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使其囊括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等诸多大奖。李沧东在成为导演之前,是一名剧作家,除电影《燃烧》外,“他的电影总是亲自撰写剧本,从而保证了其影片普遍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故事情节既曲折生动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饱满、性格丰富而不脸谱化、 概念化”。李沧东用自己对人性的感悟、对社会底层的人性关怀、建构了一个属于他的诗意影像世界,他是一个社会解剖者,对人、对生命、对生活痛苦本身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探讨,将个体人物异常平静地置于残酷的历史和现实之间,虽然冷静,但不冷漠。他始终在自己的诗意世界中,提炼一切人类的共同情感。
李沧东善于以女性视角去捕捉大时代熔炉中女性的家庭关系、个人欲望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意影像世界是通过符号化的女性角色去描写建构的,他都无一例外地通过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去窥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寻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女性角色才是其电影叙事的核心驱动力,笔者考察不同时代李沧东的电影作品,探析起电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二、被抛弃的阶级:边缘女性社会地位的同一性
(一)社会底层的女性脸谱
李沧东身上对于时代和社会有一种敏感的嗅觉天赋,他深刻了解到社会的变革下,底层人士所受到的痛苦,因此他将自己的视角始终放在底层人物的个人经历以及情感表达上,用现实主义的题材,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变迁下小人物的心理挣扎。无一例外,李沧东的电影《绿鱼》《薄荷糖》以及《燃烧》中,女性角色都承载着社会底层人民的厚重底色,她们的人生本就是痛苦不堪的。
电影《绿鱼》中,男主角莫东退伍回家,在回家的列车上发现有流氓在欺负美延,血气方刚的莫东和流氓们厮打但并没有占到便宜,只留下美延抛给莫东的一片红色丝巾。美延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而是一名歌女,一名被黑社会老大肉欲所侵占的“个人财产”。美延独自一人在城市打拼,无依无靠,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陪酒、唱歌,与男人们发生关系,过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于她而言,活着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莫东的母亲,她的社会职业是保姆,她的家庭角色也是保姆,每天生活的日常就是照顾莫东患有脑瘫的大哥,唯一的消遣就是削着水果看着电视剧笑上一阵子。莫东的妹妹金顺玉,是一名陪酒女,整天穿着性感的衣服、黑丝袜,陪着男人喝酒,以此为生。
电影《薄荷糖》中,金永浩的妻子洪是一名餐厅服务员,餐厅的服务对象是本应该象征正义的警察们,但警察却在餐厅调戏并抚摸她的大腿,并且是当着她丈夫的面羞辱她,无奈的她只能靠着略带愤怒的娇嗔言语对抗着生活的不堪。洪与金永浩结婚之后,成为家庭主妇,她终日生活在家庭琐碎之中,哪怕是因为家中的一条狗,她都会与金永浩争吵并扭打,生活的意义对于她来说也只是苦难罢了。中年金永浩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并与公司年轻的女职员厮混在一起,女职员白天是公司员工,晚上则是金永浩的专属情人,与金永浩偷情是其生命中的短暂欢愉时刻,她的存在则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影像符号。影片后半段以光州事件为故事背景,讲述金永浩奉命镇压学生运动,但一名女学生被以金永浩为代表的部队军人开枪走火射杀致死,这名女学生的生命如草芥一般任人蹂躏,没有人会在意这个脆弱生命的消逝。
电影《燃烧》中女主角惠美是一名商品促销女孩,生活开支要靠贷款才能维持,为了去非洲旅游,她攒了很长时间的工资;在精神层面,离家打拼的她得不到家庭的支持,没有亲人的关怀;情感方面也一直处于孤独状态,只能靠找人调情作为情感寄托,生命的意义于她而言,就是挥霍时间,虚度光阴,如同惠美在影片中说道,“非洲沙漠中的布须曼人,对于饥饿的阐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生理上的饥饿,第二种是精神上的饥饿”,无论是生理还是对精神层面而言,惠美都是一个十足的饥饿者。
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中,女性角色都毫无例外地打上社会底层的底色,经济层面的窘困导致角色个人命运的苍白、无力,这些女性角色都展示了底层人民的挣扎与痛苦。
(二)卑微命运的无力把控
《绿鱼》中,卑微的美延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美延渴望与莫东的爱情,但是黑社会大哥培社长是两人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对于憨厚的莫东来说,与大嫂有染违背江湖道义;另一方面,莫东和美延都必须依靠培社长才能获得财富,他们无法与培社长划清界限。美延与莫东也尝试着去主宰自我的命运,美延与莫东从列车上回来,两人的感情从模糊、不确定到彼此确信的伴侣关系,两人本可以乘着列车离开这座城市,但此时,黑社会大哥打来电话,美延告知莫东:“培社长叫我过去,我跟随你的选择,要去吗?”但是得到莫东的回复却是“大哥说了,就要去”。美延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同样被束缚的莫东,她无法做自我命运的主宰者。
《薄荷糖》中,金永浩的初恋情人尹顺仁是一位温柔的姑娘。尹顺仁对他倾情,金永浩对她倾心,青年时期的金永浩在服兵役时,尹顺仁从首尔去探望他,迫于规章,两人未能见面。金永浩服役完后,尹顺仁再次探望他,但金永浩当着她的面抚摸服务员的大腿,这让尹顺仁很难过,但她还是强忍住内心的波澜,将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钱给金永浩买的相机送给他。车站分别后,两人再无交集。直至金永浩中年时期,尹顺仁仍然没有忘记这位初恋情人。即使她已嫁作人妻,即使她成为植物人,当金永浩拿着一罐薄荷糖出现在尹顺仁的病床前,他才感叹,原来自己与尹顺仁分别之后过得如此狼狈,而病床上的尹顺仁也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假如当时尹顺仁能够与金永浩打开彼此的心结,假如尹顺仁没有嫁为人妻,假如尹顺仁没有出车祸成为植物人,金永浩与尹顺仁一定能够成全彼此的幸福,但这一切都只是假如。
《燃烧》中,卑微的惠美更是如此。惠美与钟秀自幼相识,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有一份未对钟秀说出口的爱恋,整容后,两人成为恋人。卑微的惠美在旅途中结识了富人本,她被本所吸引,但惠美心中给钟秀留了最重要的位置。影片中期,惠美消失了,钟秀拼了命地去寻找,去惠美的出租屋,去惠美曾经跳舞的地方,与惠美的同事交谈,但都无果。唯一的可能就是,惠美被本所代表的富裕阶层以祭祀的方式杀害,但她死前仍然表达了对钟秀的爱恋,“惠美对你的感情很特别,她说无论如何都会站在你这一边”,影片最后,钟秀将本杀死,但逝去的惠美却再也回不来,一个人的生命被本所代表的富裕阶级无差别地杀死,如同烧掉乡村的蔬菜大棚一样容易。在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以惠美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的女性角色命运,任由他人书写。
三、男权的牺牲品:被男性欲望裹挟的无差别性
(一)自我意识的黯淡消退
女性自我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价值、位置、能力等的自我认知,即女性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并能够肯定和实现自身的需求和价值,笔者将从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个人情感两方面进行探析。
《绿鱼》中美延的角色社会定位就是社会底层的夜总会歌女,在夜总会谋生的她没有任何独立性而言,所以她必须找到能够让她依附的黑社会大哥培社长,以培社长的黑社会背景以及财力作为支撑,艰难地在这个城市中活下去;而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则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培社长的姘头。美延的自我意识在影片中得到过两次明显挣扎的展现:一次是在夜总会唱完歌后拉着莫东的手想逃离培社长的控制,但是结果却是被培社长的小弟强行塞进车中,身旁的莫东也被打得鼻青脸肿;第二次则是影片后半段,美延与莫东在列车上准备出逃,完成自我社会角色“肮脏”属性的救赎,不再做歌女,而是与莫东生活在一起,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培社长的身边。个人情感方面,美延渴望与莫东之间的爱情,与莫东做出实质性的出逃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最终还是回到培社长身边,没能彰显自我意识的独立性。
《薄荷糖》中永浩的妻子洪的角色社会定位是社会底层餐馆的服务员,终日在餐厅打工谋生,生活得过且过,让永浩教她骑自行车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为生命增添意义的画面。婚后,洪成了家庭主妇,从之前的服务员的工作到如今的家庭主妇,她的社会角色定位都是依靠永浩的人生轨迹而发生转变的。情感方面,身为基督教徒的洪理应对感情有洁癖,但是与永浩结婚前,洪就被永浩的同事们抚摸大腿,而且与永浩发生关系,结婚后,更是与驾校教练发生了一夜情。
《燃烧》中惠美的角色社会定位是底层商品推销女郎,通过暴露的衣着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但是惠美的自我意识相对来说是较强的,她不满足现有的自身的阶级固化状况,她渴望向上层阶级流动,从而结识了家境富裕的本并与之交往,但是其骨子里的卑微注定了她悲惨的命运,她成为富人阶级玩弄的对象。从本为代表的男性视角看,她与本的相识、交往、被害都是本所设计好的,惠美如同猎物一般走进了预先设定好的圈套中,惠美会刻意迎合富裕阶级的喜好,比如谈非洲的奇遇怪事,在酒吧中跳笨拙的舞蹈,自我意识逐渐消退,直至黯淡。情感方面,惠美心中始终给同样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钟秀留了一席之地,但是她被富裕阶层的本所吸引,刻意隐藏了自己对钟秀最本真的原始情感,终日与本厮混在一起,成了本所代表的男性欲望的附庸。
这三部影片中,女性角色的自我意识都只是男性欲望期待的简单内化,是附属于男性的“他者镜像”,这些女性角色都不能自觉地肯定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是都遵从了恋人或者丈夫的价值需求,自我意识处于黯淡消退的状态。
(二)男性欲望实现的道具
郑圣一曾撰文批判李沧东电影中女性“道具化”的问题:“李沧东的电影一直如此。在他的电影中,若没有女性的牺牲,男性的灵魂无法完成净化。而女性的灵魂却必须要停留在原处,最终什么都不是。”李沧东电影作品中的女性都无法避免被“道具化”,都只能成为男性欲望实现的工具而已。
《绿鱼》中的美延彻彻底底就是男性欲望实现的道具,一方面,她是黑社会大哥培社长肉欲宣泄的工具,即使在美延喝得烂醉、生理不舒服的时候也必须随时侍奉在其身边;另一方面,美延最终也成为男性欲望实现的背后推手,影片后半段,莫东杀死了培社长的竞争对手,但是培社长怕惹麻烦,残杀了莫东以此来保全自己,而这一过程中,美延作为亲历者,除了恐惧,没有尝试阻止培社长,她的心上人惨遭杀害,她的无所作为也是莫东被杀背后的推手之一。
《薄荷糖》中永浩的妻子洪亦是男性欲望实现的工具,年轻的洪在一家小餐厅打工,或许是由于身处社会底层会被漠视的原因,永浩的警察同事们会调戏她,抚摸她的大腿,她成为男性情欲的宣泄对象,婚后的她更是因为家庭琐碎,成为永浩的暴力欲望的泄愤对象,无助的她最终选择与永浩离婚,逃离这让人痛苦的境地。
《燃烧》中的惠美出身于社会底层,她亦是男性欲望实现的工具而已。首先是生理上,惠美对钟秀从小就有爱慕之情,但苦于自己丑陋的外表没有对钟秀表白,但在其整容后,她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钟秀的喜爱并最终与其交往。但于钟秀而言,惠美首先是他肉欲宣泄的对象,并且随着这种欲望的变态加剧,钟秀在脑海中幻想着惠美的容貌,并手淫进行宣泄。其次,于本而言,两人在一次非洲旅途中相识,并厮混在一起,但惠美不过是用于满足本异化的杀人欲望,一种视底层女性为草芥而随意杀害的欲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