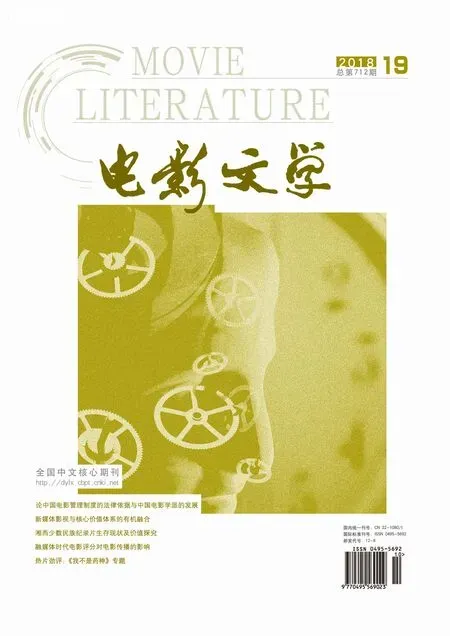《脆弱地带》心理焦虑辨析
王亚鹏
(临沂大学沂水校区,山东 临沂 276400)
影片《脆弱地带》改编自19世纪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由布莱恩·科兰斯顿饰演的中年律师霍华德·威克菲尔德,忽然之间不告而别,实则躲进自家车库上方的阁楼里,一边窥视妻子与女儿的生活,一边抛弃所有身份属性,成为避世独居的“隐形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效应,导致他几乎从自我放逐变成无家可归。影片导演采用了开放式结局,霍华德的命运不得而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
本文通过对霍华德一系列行为的研究,从亲密关系的角度分析霍华德潜在的心理危机与心理焦虑,阐述其成因,以期引发思考。
一、困境:驱赶与放逐
伴随着不停切换的镜头以及急促紧迫的音乐声,诉讼律师霍华德·威克菲尔德穿行在人潮当中。繁忙的都市景观,焦躁忙碌的中年男人,即便坐着车,也在接听工作电话。与此同时,画外音传来:“当你累了一天想要回家时,你会觉得所有这些小分歧一点点聚集在一起,像极了文明陷落的漫长过程。”
音乐渐渐变得舒缓清冷,霍华德一边发着牢骚,一边走进院子,由于他和妻子买的房子在郊区,时常有各种小动物不请自来,闯进他的院子里。此处,兔子、浣熊和其他小动物暗喻着生活里各种令人烦躁的挫折。霍华德朝它们吼叫着,驱赶着,却徒劳无功。只要稍有松懈,挫折便会像那些惹人厌的小动物一样冒出头来。
霍华德鬼使神差般走上了平日里无人光顾的阁楼,从阁楼望出去,属于“家庭”的房子那边,方形的窗框意味着规则和秩序,里面透露出暖色的灯光;属于霍华德的阁楼这边,圆形的窗框则暗喻着偷窥的眼睛,眼睛后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在一片黑暗之中,霍华德能看到不远处窗子里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这一刻,霍华德仿佛抽离了自身,从生活在其中的“在场”,变成了“离场”,从生活中的“自我”,变成了远远观望的“他者”。这种带有“偷窥”意味的窥视,令他既获得了窥探他人生活的刺激,又获得了暗中“掌握”他人人生和隐私的权力感、控制感和满足感,这是霍华德在婚姻生活中无法获得的体验。
在持续15年的亲密关系中,这个看似平淡温馨的中产家庭,实际上已经在不停的争吵和猜忌中分崩离析。霍华德将猜忌视为婚姻生活中最有效的刺激,然而这刺激也渐渐失去了效用。他生活在家庭之中,却感受不到自己的重要性和存在的意义,失去了对妻子的支配权以及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掌控力,这让霍华德无所适从,因而,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脆弱的亲密关系带来心理危机与心理焦虑,面对无法破解的困境,霍华德选择了最错误的途径——“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霍华德·威克菲尔德”,即放逐自我。
二、暗示:敌对与攻击
整部影片中,霍华德在不断暗示自己:我是一家之主,我是顶梁柱,我是不可或缺的人。他的心理危机来自亲密关系的逐渐解体,而心理焦虑令他产生了敌对心理与攻击性,这反而令亲密关系加快了解体速度,逐渐到了不可逆转的悲惨境地。作为伴侣的亲密关系,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指征即“信任”与“依赖”。这两个指征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亲密关系都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继而产生危机。
霍华德躲进阁楼以后,快速切换的镜头不再出现,音乐声变得舒缓空灵,故事节奏自此开始变慢。接下来的日子里,霍华德好整以暇地观看着戴安娜和女儿们的生活,在她们偶然的小失误里自得其乐。看到戴安娜到处打电话寻找他,霍华德发出恶作剧成功的得意笑声。那一刻,他是轻松的,就像是个逃了一天课又闹离家出走的孩子,既暂时摆脱了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压力,又不会因此承担什么损失。所以他可以一边吃着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食物,一边伸长颈子看着窗外,一边不断发出笑声。然而,成年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打乱其他人固有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可预期的伤害,又怎么可能靠几句谎言搪塞过去?霍华德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和焦虑之中,远比孩子一次偶然的逃课和离家出走更可怕。
安娜遍寻不到“失踪”的丈夫,无奈报警,警察却没把霍华德的“失踪”放在眼里。警察离开后,戴安娜在窗前独自哭泣,霍华德第一次陷入感动与愧疚之中,可惜,这份动容维持的时间极其短暂,随着“安慰者”的出现,霍华德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自信、理智和继续看下去的乐趣。他躲在黑暗中,喃喃自语地夸赞着自己的身体,达成精神上的暗示与慰藉——我是强壮而富有魅力的,就像橄榄球后卫那样。处于婚姻当中时,作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霍华德表现出了如同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攻击性,他不断从言语和行为上“攻击”着妻子,控制着对方的举动。
霍华德认为自己依然在暗中保护着妻子,关心着她,照顾着她,甚至因为她的情绪起落而焦躁不安。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他自以为是的“关爱”罢了,他不负责任的“失踪”,已经打破了家庭的秩序,造成了妻子心理上的恐慌。而他的“在场”,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霍华德甚至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说:“你得自己照顾自己啦!……如果给我时间,我会那么做的(转走银行里所有的钱)。”看着未成年的双胞胎女儿,他一边愧疚于自己的“失踪”会让两个孩子陷入难堪的境地,一边又觉得自己目前身为父亲的状态竟然是比之前要好的,毕竟“我现在看她们两个的时间,比以前几年几个月加起来都要多”。
除了脆弱的亲密关系,霍华德还面对着中年危机带来的焦虑。人到中年,普遍从身体上感觉到了年龄增长带来的压力,血压、血脂、血糖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开始困扰身体健康。生活上,对于金钱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就东方人来讲,还同时面对着抚育子女以及照顾老人所带来的金钱和精力的损耗。对体能不自信的同时,工作压力与职场困顿带来了更深的心理焦虑。
三、谎言:欺骗与多疑
影片进行到中段,终于揭示出霍华德内心不安的根源——他与妻子的感情来自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和数不清的谎言。当初,他利用自己身为律师的口才、心机和卑鄙的策略,将戴安娜从当时的男友德克·莫里森那里“抢”了过来。霍华德在德克面前将戴安娜塑造为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轻浮女孩,又让戴安娜误会德克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最终赢得了戴安娜的信任和依赖。这一切卑劣的举动表现出霍华德骨子里的自私与强烈的男权主义倾向。
霍华德对自己横刀夺爱的举动十分自得,然而这也为他和妻子之间的不信任埋下了长达十余年的危机。回顾霍华德与妻子的关系,“信任”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当“依赖”也不复存在时,亲密关系自然岌岌可危起来。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一件事彻底打破了,即双胞胎女儿的诞生。
新的亲密关系的建立,令旧有的亲密关系被打破,一切秩序与规则将重新建立。在秩序建立的过程中,霍华德意识到了妻子与女儿们对自己的影响力,这在他潜意识的深处象征着夫权和父权被侵蚀、被动摇,并因为自己自然倾注的爱而变得恐慌起来。“我意识到一切都有意义,一切你爱的东西,爱的人,都能够因为一些偶然事件而被夺走。”他因此恐慌、不安,表现于外便是强烈的攻击性,用语言攻击,用性占有,以此获取安全感。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短暂的征服过后便是无尽的空虚和不安。不安令危机感加剧,随即霍华德的攻击性变得愈发强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只能将妻子与自己的关系越推越远,从而发展到在霍华德眼中,妻子与任何男子的接近都是另有目的的,是在意图与其他男人调情。
在夫权与父权受到挑战之后,从觉得自己因为情感的投入而受制于妻女开始,霍华德便被权力与欲望驱使,他狂热地相信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与支配权力,同时又深知自己外强中干下的软弱与不安。他看着妻子艰难地挪动着两只巨大的垃圾桶,嘲笑着她的无力。他一直将传统意义中划分给男性的职责部分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且是界限分明的责任。以屋子内外为界,里面是“女人”的地盘,外面是“男人”的世界,他嘲笑妻子的工作,想到妻子将为从没有处理过的信用卡账单、按揭等各种费用焦头烂额,他几乎要笑到不行。因为那是他所认为的“男人”的领域,是他在养着这个家。如今,作为家的“主人”消失了,他简直等不及看到妻子脸上的不安、恐慌、沮丧和悲哀,通过妻子的“无能为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且让妻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方可离开阁楼,如同一个骄傲的国王那样,回到这个家庭,并且让妻子和女儿们对自己俯首称臣。
四、囚徒:囚禁与回归
可以说,自霍华德藏到阁楼那一刻开始,他一直处在极度的矛盾当中——在“继续藏下去”与“马上回到家里”之间徘徊不定。他蓬头垢面翻街道上的垃圾桶,却用不屑的语气形容其他流浪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自己是在“城镇探险”。这说明,虽然霍华德在行为上已经与流浪者无异,但是在内心中,他并不认同自己的流浪者身份,他既非正常的社会成员,又不认同自己的流浪者身份,霍华德此刻是真正的边缘人,游离在任何身份地位之外。当他躺在别人丢弃的床垫上,打开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收音机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充满了调侃与嘲弄的暗喻:“由于之前的表现,我们已经出局了。”
霍华德将自己与他人划清了界限,将自己囚禁起来,却觉得是婚姻和家庭令自己窒息。在这段亲密关系中,他的患得患失和唯我独尊令他与其他人渐行渐远,直至找不到弥补和修复的可能。他将自己放逐出了家庭,同时也将自己放逐出了爱情与亲情维系的亲密关系。他仿佛拥有了更广阔的自由天地,却失去了赖以生存和皈依的真实家庭与心灵家园,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理,都丧失了原有舒适度的边界。霍华德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抛弃了社会身份的同时,也抛弃了作为丈夫的责任,抛弃了家人,或者说,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不肯承认。他就这样坐在阁楼上,看着妻子再一次开始教舞蹈课,看着她疲惫地坐在椅子上陪伴着两女儿。看着她照顾这个家,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成长。
外面下起了暴雨,闪电的照耀下,玻璃上流淌的雨水的影子映在霍华德的脸上,像是连绵不绝的泪。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嫉妒、愤恨,自私的强迫。”“我爱我的妻子,以前我从未‘真正’爱过她。”
故事层层递进,事态逐步升级,直到霍华德发现妻子与德克·莫里森即将旧情复燃,疯狂的嫉妒令他再次穿戴上象征着束缚的西装、领带和手表,“真奇怪,又要受到规则支配了”。霍华德的脸上撑起了假面一般的自信微笑,推开家门走了进去……
就像霍华德独白中说的那样:“霍华德是受害者,霍华德也是迫害者,霍华德是控制狂。”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男权主义视域下的男人对于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绝对权力地位的争夺。然而,一旦亲密关系被打破,权力又从何提起呢?在亲密关系中,不存在输与赢、主与从,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都需要平等互助才能共存。正因为霍华德选择了一条荒谬的抗争之路,却抛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才使他躲在阁楼上的行为既可悲又可笑。他所面对的心理危机与心理焦虑,原本有着更适合的解决方法,然而一步错,步步错,他虽然最终打开了那扇他亲手关闭的家门,然而,霍华德真的能“回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