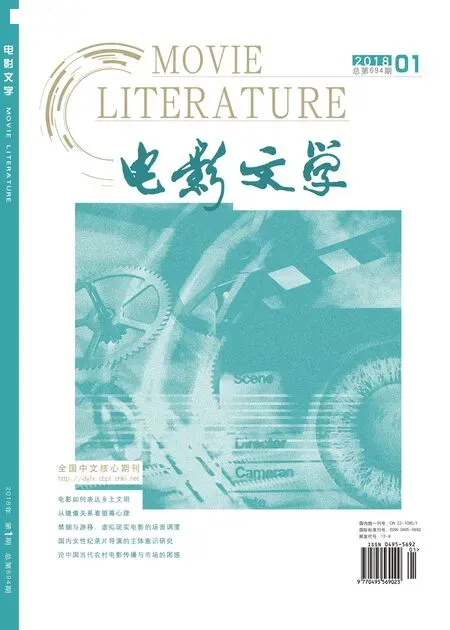论电影《乘风破浪》中乡愁乌托邦的建构
平方园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乡愁是现代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后果”。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具体表现在其“(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观念与态度,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未来的观念和态度。现代性是一种理想、一种时代意识的觉醒、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与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发端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裂变之中的乡愁,折射出来的是对传统社会的敬畏与崇洋,对“时空压缩”(哈维)的现代社会一次明目张胆的反抗与挣脱。在此意义上,对于乡愁的读解过程也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独特认知过程。当现代化以纸醉金迷、变更求新、资本利益、精尖科技诱惑人们覆盖原生价值取向,而裹挟于现代需求之中,“绑架”“束缚”着个体的灵魂,直至枯竭、榨干,成为毫无生命气息的行尸走肉。通常而言,人们对国家、家园都有着深深的眷恋,不仅是人们的生养之地,更是灵魂之家、文化原乡。于是,向流逝的岁月及渐远的家园寻找慰藉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也是重塑心灵的驿站。
提及乡愁,其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从中国儒家推崇的“落叶归根”情怀、道家“返璞归真”理念、诗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名句、鲁迅先生的《故乡》、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校园怀旧民谣《同桌的你》直至当今时尚流行的绿色食品、复古风等,皆传递着人类情感记忆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与怀旧情结。然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表达机器的电影,也在用影像描摹着对时下人们的切肤之痛。集多重身份的韩寒在作品《乘风破浪》中重温往昔的美好,将小镇空间、时代镜像及港式情结建构为充满集体记忆与怀旧色彩的乌托邦,以“返本”明晰身份认同,消解现代人的情感焦灼,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
一、小镇空间:乡愁乌托邦的表达
如果说韩寒年少成名、因文字真知灼见而享誉文坛的话,那么小镇空间的书写则是定格韩寒电影世界不可或缺的风格标签。韩寒曾在采访中如此表述故乡(亭林镇):“我很喜欢故乡,而且我觉得文化人或多或少都有故乡情结,我在上海的时候每周都会回去看爷爷奶奶,回老家街上走一走,小时候觉得很长的路回头一走很短,还是很喜欢故乡。”这番言辞可以说是韩寒小镇空间的真情流露,此时的小镇空间已不单单是人物所处的客观地理位置抑或故事背景发生的场所,而是承载着韩寒的情感体验、经验和记忆,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载体。
自韩寒转行做导演以来,小镇就成为其电影关注的重心被繁复书写,继处女作《后会无期》中的“东极岛”到《乘风破浪》中对故乡亭林镇的呈现,小镇倾注着韩寒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斑驳情愫。相较于《后会无期》故乡的坍塌与落败,新作《乘风破浪》对故乡倾注的情感则更加直接与率性。故事发生的空间场域定位于“亭林镇”,位于上海市金山区东北部,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与历史风貌,地理位置优越,是工业发展的重镇,也是韩寒魂牵梦绕的故乡。然而,社会增速发展的今天,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正在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日益繁盛的都市空间正在无声之间淘汰小镇空间,展现其蓬勃的发展潜力,消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沦落为无根的都市漂泊者。当然,亭林镇也不例外,身为亭林镇人的韩寒亦是如此。于此程度上,集作家、导演身份于一身的韩寒敏锐地捕捉到此气息,不吝笔墨地对准故乡,展开一次温情而梦幻的还乡之旅。片中,市井风情浓郁的“亭林镇”只是韩寒心目中故乡的剪影,是韩寒想象中的故乡。以嘉兴、丁栅等为代表的江南小镇,迥然不同于现实意义上亭林镇的真实复现。但地理空间的高度描摹,勾勒出了一幅人人心向往之的“世外桃源”图景,承载着青年人过滤都市喧嚣的情感驿站。此时,凝聚本土记忆的小镇是个体对抗现代化、全球化,投射身份认同的特定空间,超越物理空间的角色限制,被塑造为一个兼具指涉意义的乌托邦,抚慰着现代人的焦灼心理、成长经验及对家园的重构。
彼时,时间维度的设置避开通俗老套“闪回”营造的新旧时空叙事,直接让主人公太浪所在的未来时空(2022年)“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1998年)。堪称离奇的“穿越”事件,一方面增强时空交替的张力,使得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不再仅仅满足于叙事的需要,而成为见证人物成长的必备空间。从另一层面来讲,“穿越”给故事带来一定的浪漫色彩,赋予小镇如影梦幻的特质,更像是导演精心策划的一场梦,一场触摸不到、渗入肌理的乡愁之梦。
在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正在主动或被动接受现代性的影响,其正在不可避免地带来断裂、巨变、压力与独孤,使人们普遍产生不安定感。然而,故乡、家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何时,乡愁永远是个体心目中挥之不去的情愫。尽管故乡附带贫穷凋敝的标签,甚至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它时刻固存着缥缈殆尽的记忆,为个体成长提供丰沃的精神信仰。无可厚非,小镇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情感投射,是个体精神失落的避难所和情感栖息地,也是一剂治愈“现代病”的偏方。片中,亭林镇的空间造型也是极生活化的展现,各种文化景观的拼贴与堆砌使小镇犹如静止的画面,靠留在20世纪90年代,弥漫而来浓郁的怀旧气息。其中,小镇里的旧街区、街道的旧建筑、杂货店铺、KTV、自行车、穿行其中的人们的衣着装扮、公共汽车以它们比汽车缓慢的游荡感,更接近于旧时光的节奏,将小镇呈现为一个具有强烈归属感和脉脉温情的社区共同体。然而,韩寒并没有刻意渲染或夸大亭林镇的“伤感落寞”,而是呈现了其日常性与人文性的一面,进而表达亭林镇蕴含的温情与美好。正是如此,乡愁与怀旧不禁而起,尽管韩式桥段幽默横生,也无法克制小镇已逝美好的惆怅与感伤。
二、时代镜像:怀旧符码书写集体记忆
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推而论之,存储、聚合于社会中的每单个元素、群体及事件的记忆皆是构成集体记忆的分子,即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而植根于特定情境生成具有高度标志的个体记忆交会凝聚、重组交流、共同组成独具象征的时代记忆,拨动着同时代人乡愁怀旧的心弦。片中,导演精心建构的一系列附带时代表征的文化符码,堆砌、拼凑成一幅弥漫着20世纪90年代江南小镇独有的浪费风情画。细节层面的精雕细磨,赋予其明晰的时代轮廓,召唤着八九十年代观众的集体记忆与乡愁。
于此程度上,标志或验证时间流逝的流行符号成为时代镜像的重要手段,也是营造怀旧引起受众共鸣的选择。如有年代标志的KTV和录像厅,BB机,日立牌电视机,热播台剧《新白娘子传奇》,小花房间窗户上小虎队、白娘子的贴纸,正太录像厅墙上挂着的周润发、刘德华、李小龙等画幅,电影院上映影片《英雄本色》等,皆是20世纪90年代具备较高人气、余温不减的怀旧符号。从而召唤起观众对特定时代的历史感知及观众自身在“那一刻”的私密个体记忆,也在无形之中触碰着90年代人内心最柔软的回忆。在此意义上,怀旧所具有的独特美学价值,展现出一种忧郁的感伤美学。影片最能表现怀旧基调的莫过于国内外流行歌曲的情感渲染,怀旧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式怀旧上升为“全球性”怀旧。片中出现的歌曲,皆在原作的基础上经过了微妙的修改,重新改编之后变得舒缓、忧伤。罗力唱给爱人的日本歌曲《一方天地》,甜蜜之余透露着小人物爱情的痛楚与酸涩 、日本歌手佐田雅志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歌曲《关白宣言》被改编为《乘风破浪歌之男子汉宣言》出现在小花的婚礼上,小马离开时的配乐《别送我》,改编自民谣Five
Hundred
Miles
,再次被更换为带着淡淡忧伤的浅吟低唱,营造出忧郁和感伤的怀旧气息。以上带有丰富时代记忆的歌曲,成为连接国内外观众的情感纽带,也构成其共同的情感记忆。自2022年到1998年的时空交接、从浮华都市到恬静亭林小镇的时空转换,太浪以现代人视角审视90年代并由衷感叹:这个时代多好,当你想静静的时候,没有人会问你静静是谁,不用每天发微信、刷朋友圈,不用手机定位,出门得靠狗。对于携带焦虑、浮躁标签的现代人太浪来说,90年代纯真而美好,青年群体的梦想单纯而透彻,即使社会发展步履匆匆,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时代变革的呼声与日俱增,身处封闭小镇的青年群体仍保持着“农业文明”下清悠闲适、安稳不羁的生活范式。穿梭于乡土社会语境中建立起来的熟人社区,邻里乡亲相处融洽,而这恰恰是陌生分层的现代人望尘莫及的,也是对现代社会人际淡漠的一次深刻反思。片中,警察根据六一的名字可以准确揣测出其父之名,足可见亭林镇人际关系的和谐。于此程度上,纯真时代滋养下的小镇青年,在不断分化的社会面前,透如明镜,梦想纯粹。就像答应等待太浪的正太,忠于承诺,直至太浪归来,并自带优越感地认为:“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正是秉承如此理念,正太坚守放映录像带与囤积BB机发财致富的梦想。此外,与小花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完美爱情的向往;憨厚笨拙的六一对“正太帮”的兄弟们真诚忠实,对KTV小姐的爱情真挚有加,即使被拒绝仍一心对其好。
然而,正如小马所言,“这个世界肯定会变的”,身为小人物的六一、罗力等人,其纯真品质虽浓缩着时代的标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特定时代小人物对抗世界的奋斗史。大龄儿童六一,是90年代普通人的真实写照,看似浑浑噩噩,但一直在努力博得外界对他的认可与肯定,尽管没能如愿,但并未丧失一颗上进之心;同样,对于罗力来说,爱护妇女儿童,坚守职业准则,只为可以给爱人过上优渥的生活,不料工作归零,爱人背叛。道出了身处90年代的较大群体的普通人空有一腔热血,无奈被环境左右,犹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无力地挣扎飘荡,以此隐射万千普通人的梦想与失落。此外,作为影片“彩蛋”级的人物设定马化腾,代表那些可以敏锐嗅到时代先知、富有梦想的人群,在变革之时,勇敢追逐梦想,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与其相反,奔走于香港内陆的房产大亨黄志强,试图不惜重本获取挚爱KTV的地理位置,以期实现其楼市梦。与马化腾一样皆是有梦之人,宿命却迥然不同。影片最后,信心满满的黄志强死于正太帮之手,楼市梦不攻自破。由此可见,社会在接受一项新兴观念之时,需要多少先知之人付出代价?以上三类群体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青年人在社会分化的浪潮中的镜像,浓缩的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于此意义上,陪伴鲜花与掌声的赛车手太浪在见证了所处年代小人物的至真至纯,青春梦想的追逐之后,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
三、港式情结:黑帮掠影映射文化认同
电影《乘风破浪》是韩寒在充分借鉴陈可辛指导的《新难兄难弟》基础上的一次全新翻版,并将香港黑帮电影的内核移植到叙事之中,构建出一部港味十足、温馨而怀旧的“伪黑帮”电影。堪称港产重要商业类型的黑帮电影,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一道独特的文化奇观。作为成熟的商业类型,其成功离不开香港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更无法忽略影片中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尤其所折射出来的兄弟情、忠诚、义气等元素,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时下,物质资料、科技信息丰富斑斓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严重扭曲,失去了信仰的依凭与安定的归宿,精神世界渐趋空疏化、游魂化、庸俗化。于此程度下,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慰藉成为不二选择,而脱胎于侠文化、济施普生的“英雄”成为安抚现代人价值失衡的救心丸。
作为80后的韩寒,香港电影是其年少成长的文化记忆,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黄金期的香港黑帮电影。当韩寒将黑帮电影所凝聚的共同的历史与情感记忆加以提炼、重述的时候,一种共同的怀旧情怀油然而生,关于自我与群体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已经悄然塑形。回归到电影《乘风破浪》本身,影片以90年代最具记忆标签的香港黑帮电影为基础对人物进行包装升级,选取黑帮片中折射出来的英雄主义重塑黑色浪漫,也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一种期盼。影片中正太帮帮主徐正太留有中分发型、身穿喇叭裤、称呼警察为阿sir,流露出浓重的港味怀旧,把观众迅速拉回风华卓越的90年代。正太帮是其年轻之时在亭林镇创办的“黑社会”团体,打着“收保护费”的口号等,在小镇上如鱼得水,游荡自如。而小镇则是正太帮的江湖,所谓的“江湖不是一个‘组织’,它只是游民共同生存的地域,而且是一个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隐性地域,是一个隐性社会”。与此同时,正太帮帮主徐正太梦想着制霸亭林镇、成为像杜月笙一样的人物,无不流露出大陆式的“黑帮梦想”。与此同时,亭林镇“叱咤风云”的正太则完美继承了香港黑帮电影中大哥的形象塑造,不论其外部造型的呈现还是内在精神的渲染,皆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受众对于“英雄”的想象。尤其凸显出来的兄弟情义、赤胆忠心、义气等精神气质作为现代社会的乌托邦,而此种乌托邦中体现着浓重的香港情结,以期表达对香港情结在当今社会中的怀旧与崇洋。而对于英雄的品质塑形,首先体现在,英雄有着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的江湖豪情。影片开始,乡村蝙蝠侠化身的徐正太对素未相识的太浪出手相助、慷慨解囊,并在警察盘问正太之时,机智解围,其身上流露出的正义与其名达到一定程度的谋和。其次,韩寒将香港黑帮片中极具感染力的兄弟情义移植到电影中,通过影像的叙述,细腻地书写惺惺相惜、生死与共、建立在虚构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兄弟情义,并通过维护社会秩序和维护男性情谊的内在矛盾中实现自我牺牲,从而以其为依托来表现正太的英雄气质。
片中,电影院播放着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银幕上演的是忍辱负重的小马哥为兄弟(宋子豪)报仇的英雄主义情节。无疑是正太内在精神的一次投射,也是引导其价值追求的隐性目标。对于“黑社会”团体正太帮中的徐正太,不仅对兄弟两肋插刀、肝胆相照,此外,保护亭林镇上的歌舞厅也成为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求达到“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房里只洗澡”,从利己之爱荣升为人间大爱,有着英雄的气度与胸怀。可以说,导演对英雄情结的致敬与怀旧在正太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然而,为了制造戏剧性效果,突出英雄形象,增强观众对英雄的认可与接受,一般会刻意丑化反派的形象。以黄志强为代表的反派试图通过大量金钱及团伙威慑正太帮,为了争夺挚爱歌舞厅的地理位置不惜一切手段,无视正太帮道的价值底线肆意污蔑。正太帮看似寡不敌众,但以情义堆积起来的凝聚力足以粉碎团体散沙。影片中,当得知小马遇害,正太帮一起出动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小马(名华腾);在六一被黄志强谋杀,正太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前去为其报仇,可谓一种英雄主义的呈现,而英雄主义的表现直接来源于中国文化中“侠义”文化,也就诠释了对英雄的崇拜实则是对中华文明中“侠义”精神的怀旧,而英雄恰是中国古代侠义精神的现代演绎。由此,串联起港澳台及内地观众共同的怀旧体验,抒发着挥之不去的港式乡愁。
四、结 语
物质丰盈与精神的失衡是现代化带来的一次深刻反思,个体的认知焦虑与身份危机致使现代人不断寻觅安身之所、立命之根。而韩寒影片构建的小镇乌托邦,至真至纯的时代、热血沸腾的青春梦想,重塑的黑色浪漫折射出来的是对自然的亲近、人际交往的期许、传统文化的敬畏,成为人们的情感避难所,凝结着最基本的价值参照,凸显出文艺青年创作的文化自觉。为此,只有“返本”才能“出新”,铭记乡愁,勿忘初心,方能不骄不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心灵自由。
注释:
① 现代社会是现代化的社会、现代性的社会,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展开与实现,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历史性的自觉。历史性意味着一种条件性、过程性、流动性和生成性。
② 集体记忆的概念出自莫里斯·哈布瓦赫,正如在《集体记忆》一书中所指出来的:“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
③ 脱离了宗法网络约束的自由民,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伙伴,以结拜兄弟与组织社会形式进行利益的追逐,逐渐就形成了“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