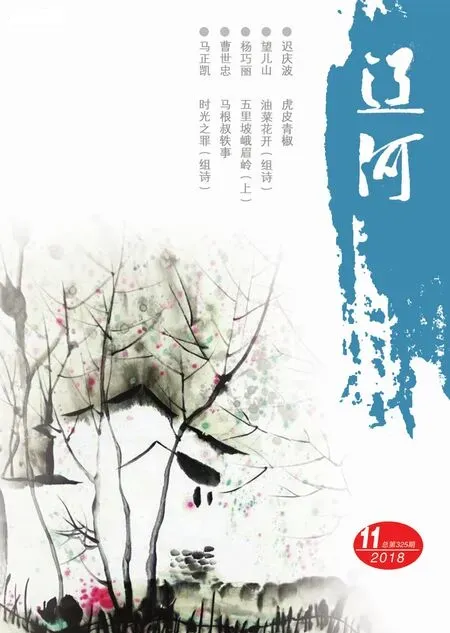以圆规的姿势飞翔
张勇
1
自从葛晓辉回来后,刘子平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听课时,他经常走神,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座位上,他像是在听课,又感觉啥也没听见。窗外山花红紫,心里百转千回,思绪在窗外的影像和室内的光线间游移。黑板前,嵇老师身影翩翩,踩踏得木质的讲台空空有声。“老师的鞋跟太尖细,真怕它卡在讲台的木板缝隙里。”刘子平为此一直担心,但毕竟担心得有些多余,嵇老师出丑的情况一次也没发生。
有些让人泄气。在这点上嵇老师经验丰富,有意无意中,竟避开了所有陷阱。听说嵇老师正和一个退役军官恋爱,爱与不爱拼的可不光是知识和容颜,她也靠鞋跟的高度来弥补与军官的距离。处心积虑呀,可她真不该佩戴鲜红的发卡。这让她的头矮了三分,也与脸色很不相配。刘子平眼里,嵇老师的发卡融化成了赤橙黄绿多姿多彩,她目视学生的眼神,也幻化出色彩斑斓中的一片碧绿牧场,满屋的学生,都是这牧场上的牛羊。
黑板前,嵇老师面对“牛羊”不遗余力,正讲解氯化氢的歹毒个性。“毒性这么大,用它自杀最好了”,刘子平脱口而出。接这句话时,刘子平正偷读一本小说,小说写的正巧是下毒杀人的情节。嵇老师粉嫩的玉手扬起,一个粉笔头砸过来。“想死还早了点,至少,你得把这节课给我听完全。”
对于听课,从前就像玩似的。从前的刘子平可不是这样的,刘子平羡慕死了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身后的葛晓辉还没回来。彼时的刘子平在课堂上,就像鱼在水中,平静的表面下,思维紧跟老师的授业解惑,简直是游刃有余。
那时候,刘子平经常进入似睡非睡状态,聚精会神的表象下面,多余的思绪竟绕着校园游走。他可以看见,看门的刘大爷在操场上跑,跑得飞快,步子细碎。前面一群鸡四散炸开,鸡群散尽,地上滚着一支篮球。刘大爷对篮球不屑一顾。他俯身快跑,追赶着一颗从菜篮子里越狱的土豆,一颗一直追随他晨练的漏网之鱼。
那段时间,刘子平一直品学兼优,成绩在全年段名列前茅。他经常上台领奖,各种各样的奖都拿完了,为此羡慕死了一大堆女同学。可是,如今这一切再也没有了,都让葛晓辉的一张破嘴给毁了。
此刻,刘子平已经没有心思读小说,他在座位上提心吊胆,心生恐惧。恐惧的情绪最是要命,它扼杀了刘子平的所有灵感。刘子平一直害怕一张脸,一张看起来挺亲切的脸。他很担心,也许不经意间的某一时刻,教室门口会露出那张脸,可能还声音火急地喊他,“子平,跟我去医院做检查!”
这种担心一直纠缠着他,像喉咙被卡住似的,令他呼吸困难。他总感觉头脑中生长起一只圆规,一只特立独行的圆规。刘子平感觉圆规一直扎在脑仁上,悠荡着两条细脚,搅拌翻腾刺碰得他脑袋生疼翻江倒海。他经常痛苦之极,弯腰俯身在书桌上做抵抗状。他因疼痛满头生发出细碎的汗珠,汗珠们正手牵着手急迫地汇成大滴,聚拢在额头上摇摇欲坠,变换着形状进行各种垂死挣扎。
刘子平身躯弯曲成虾米一样的造型引得同桌一阵笑。扈菲菲鼻尖高挺,长圆脸型,看来胸部又大了一寸。她笑得有些夸张,用手捂着嘴,头低得挨着桌面,双肩耸动,歪着头斜视刘子平,笑意朦胧的眼神里明显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刘子平觉得扈菲菲的笑合情合理,对于自己一副标准的憋尿造型,扈菲菲不笑才怪。扈菲菲朝刘子平挤眼睛,拿圆规尖扎向他腰部。刘子平立即收拢身体端正坐姿。比较而言,被扈菲菲扎一下也比嵇老师的粉笔头袭击来得畅快。自从嵇老师和退役军官同居后,她发射粉笔头的力道就像打出的子弹,杀伤力巨增。好几个同学受打击后,竟然被点石成金,成绩提高得让其他同学莫名其妙,进而开始怀疑人生。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否则生活就难说精彩。扈菲菲身后的葛晓辉就声称自己受内伤了,尤其智力受损,要求嵇老师给予赔偿。自从身边有了军官,嵇老师脸上的粉刺不见了,说话声音的含糖量开始大增。嵇老师说葛晓辉,智力这件事的根源应该在你爸身上,和老师的粉笔头关系不大。葛晓辉辩解说这些和他爸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我爸他也识得几个字,是集团公司的电工,胸前别着两支电笔呢,也应该算是文化人。”葛晓辉的分辩显然苍白无力,这又引得扈菲菲一番笑。
扈菲菲的嘲笑并没有引起葛晓辉的反感。相反的是,葛晓辉觉得扈菲菲对自己的言语有了积极回应,越发心里高兴。他朝扈菲菲挤眼睛,表明自己已经收到信息,而且兴奋。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他坐在扈菲菲身后,就算是把眼球挤爆炸,扈菲菲也是看不见的呀。
葛晓辉的举动却被刘子平捕捉到了。对于身后的葛晓辉,刘子平感觉很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道说道,或者直接与他面对面干一仗,揍他或是挨揍都无所谓,反正不能对他再听之任之,必须得有所行动。自从葛晓辉从南方回来之后,刘子平就觉得很有必要与葛晓辉对决一次,打烂他的嘴,看他还咋胡说八道。
其实之前他们关系一直挺好,刘子平帮过葛晓辉好多次。葛晓辉经常和父亲吵架,有时还出手,弄得鸡飞狗跳。葛晓辉的父亲经常没有缘由地揍葛晓辉,揍得非常狠,用皮带、用棍子,用随手摸到的东西。
葛晓辉挨了打,好像也没有表现得如何,挨完打啥也不说,该干啥还干啥。有时候葛晓辉不犯错,葛晓辉的父亲就引诱葛晓辉犯错,和葛晓辉大吵,之后葛晓辉便遭到疯狂的打。有一次,他们吵架正被刘子平撞见,显然葛晓辉是真生气了,他眼见葛晓辉当着他父亲的面,把一盆和到一半的白面举过头顶,然后狠劲地摔在地上,白面扑了一地,盛面的铝盆摔变了形状,盆底凹凸,贴在屋地上,极像一坨自由奔放的屎。
让刘子平奇怪的是,葛晓辉父亲打人很有技术含量,葛晓辉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伤,根本显不出挨过打的样子。挨打之后葛晓辉经常不回家,就吃住在刘子平家,直到刘子平母亲烦得不行了,刘子平才把葛晓辉送回去。
最近这次,葛晓辉被打之后竟然离家出走了。他走得好像不太坚决,遇见的人说葛晓辉犹犹豫豫拖泥带水,脸上明显挂着两管鼻涕。他走得匆匆忙忙,准备得极不充分,根本就是逃离,或是存心给他爸找难堪。他啥也没带,书包是背了,除了书包之外他只带了他爸喝水用的大搪瓷缸子,那是电站竣工发的纪念品,整个集团公司的职工家里都有。
葛晓辉回来后声称自己去了叫南方的大城市,还拿回来几大本子的诗,说是自己在流浪的途中写成的。扈菲菲对葛晓辉写的诗简直不屑一顾,她嘲讽葛晓辉说,少炫耀你的破诗,去过南方了不起呀,我恨死南方了。
葛晓辉不知道,扈菲菲母亲一个人去了南方,再也没和扈菲菲联系过。扈菲菲一直不理解母亲为啥如此心狠,抛下她和父亲,走得十分坚决,不留一丝痕迹。葛晓辉呢,他的心情丝毫没有受到扈菲菲痛恨南方的影响。“风流的才人,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芽,被冻死在酒壶的外边。”葛晓辉眼神明艳,盯着扈菲菲的后背,嘴唇外翻着,像复读机一样不停地重复自己得意的诗句和喷涌而出的唾沫星子。
刘子平不太懂葛晓辉的诗句,但是他知道葛晓辉喜欢扈菲菲。葛晓辉背地里祈求刘子平,要求换座位。之前刘子平与葛晓辉关系好,他们的好是从父辈继承过来的。刘子平听父亲说过,他和葛晓辉的父亲是39军的战友,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但是在换座这件事情上,刘子平毫不退让。他不喜欢葛晓辉的同桌房美美。在刘子平眼里,房美美简直是一只猫,一只无声无息的猫,没人注意她的存在。谁愿意和一只猫一样的人坐在一起呢?这个真不能答应。所以刘子平拒绝得理直气壮,丝毫也没有顾及葛晓辉埋怨的眼神。
扈菲菲并没有察觉到葛晓辉的眼神。扈菲菲喜欢不喜欢葛晓辉,刘子平一时判断不清。很多次,刘子平盯着扈菲菲的高鼻子看,搜寻肯定或是否定的答案。扈菲菲不置可否,冲刘子平媚笑。扈菲菲的圆脸越发俊美,眼睛一眨一眨,粉红色的镜框也跟着眼睛跳跃,如律动的火苗。自习的时候,扈菲菲把葛晓辉写给她的情书拿给刘子平看。刘子平读了,觉得葛晓辉将来有成为诗人的极大可能性,他写的诗,刘子平竟然一句也读不懂。
2
刘子平和扈菲菲呢,除了同桌的关系外,其余的刘子平似乎没有多想,一直懵懵懂懂的。平日里,刘子平是个极其安静的学生,从不像其他男生吵吵闹闹。他母亲为此一直怀疑他有病,曾几次押着他要去医院做检查。
此刻中午的教室里没几个人,刘子平歪在座位上,手里捧着小说,眼神迷离,不知道读还是没读。扈菲菲凑过来捣乱。扈菲菲捣乱的方式极其特别,她总是拿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让刘子平解决。刘子平觉得扈菲菲简直莫名其妙。
扈菲菲学习成绩一直超好,刘子平当然不相信扈菲菲有啥难题需要向自己请教,她这样做简直是捉弄人。刘子平有种要逃离的冲动。但是扈菲菲却不知收敛,还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她拿出生物书,问刘子平为啥阿米巴虫又叫变形虫,啥叫变形虫的卵器。“这个东东到底是啥,是不是你们男生都有?”扈菲菲把一张妩媚的脸凑在刘子平眼前。刘子平绝望地抬起头,把小说丢进垃圾桶。他回答扈菲菲:有,当然有了。然后拍拍自己的脑袋说,就在这里呀!对于刘子平的回答,扈菲菲及其满意。他斜靠在座位上,斜着眼睛看着身后的葛晓辉。
自从葛晓辉从南方回来后,到处宣扬刘子平家的事情。刘子平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简直要崩溃了。他一直心神不宁,无法专心学习,经常战战兢兢的。每节课至少有好几次,刘子平突然把头转向门口,很紧张的样子,生怕母亲会突然出现。他手里捧着小说,长时间也不翻页,心事重重,只是装作读书的样子。
扈菲菲感觉到了刘子平的异样,很想帮助刘子平。但是刘子平每天迷迷糊糊的,手里一直捧着小说。扈菲菲感觉刘子平对小说的痴迷,胜过了对学习的兴趣。刘子平成绩开始下滑,而且势不可挡一发不可收拾。为此扈菲菲急得不行,总找时间给刘子平补习落下的知识点。刘子平对学习一点也不上心,扈菲菲的努力收效甚微。刘子平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他小说不离手,被扈菲菲清理了一批又一批。刘子平塌陷在小说的世界里越走越远,像是难以回头了。
扈菲菲生气了,她不许刘子平再摸小说,把他书包里的和书桌里的一切课外书扫荡一空,全都扔进了女厕所。扈菲菲时刻注意着刘子平,她的尖鼻子快顶到刘子平脸上了,鼻尖细碎的汗珠在汗毛孔里游走。刘子平看得真真切切,心里一直琢磨,扈菲菲的脸色真白呀,白中透着粉嫩,真是健康。扈菲菲解释说,都是为你好,咱把心收回来,就凭你的聪明劲头,学啥都不难。刘子平很想对扈菲菲说声谢谢,但是始终也没有说出口。很多时候,刘子平是个不善表达的人。
刘子平像变傻了似的,课堂上不再听老师讲课,也不看书,就呆坐着,像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偶尔俯下身,头抵在书桌上,显示出正努力抵御痛苦的样子。即便是这样,数学课上,老师刚写完一大串计算式,他随口就能说出答案,而且准确无误。语文老师有时也不知深浅地提问他,说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品都是啥?刘子平像大病未愈样站起来回答说,一坨狗屎。同学们一阵爆笑。扈菲菲没有笑。扈菲菲不但没笑都要急哭了。扈菲菲说老师他发着高烧呢,烧迷糊了,不是故意的。
此时窗外阳光正好,四月的暖光铺洒进教室里,屋里氤氲着花草成长的芬芳。这种勃发的气息让人无法安稳,有要奔跑撒欢儿的想法。学生们被这种暖阳激励感染着,有要歌唱的冲动。让扈菲菲难受的是刘子平的沉重和萎靡。扈菲菲不止一次问刘子平,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一次刘子平都沉默不语,只是直盯着扈菲菲的俏鼻子看。在阳光播撒的明艳线条里,刘子平发现,扈菲菲鼻尖上的汗毛纤毫毕现,阳光正通过毛孔的缝隙,分解出红紫青蓝。
3
刘子平的萎顿让葛晓辉喜出望外。葛晓辉对扈菲菲说,以后别再招惹子平了,他的事你帮不上忙。扈菲菲耸耸鼻子,给葛晓辉一个蔑视的眼神。葛晓辉觉得扈菲菲很好笑。“扈菲菲不用你参合,子平是我的好哥们,我们的友谊延续了两代,我会尽力帮助他的。”葛晓辉浓重的湖北口音让扈菲菲直倒胃口,有要吐的感觉。
最初刘子平也没明白,葛晓辉如何能帮到自己,所有的麻烦都是葛晓辉惹出来的,刘子平恨死葛晓辉了。直到有一天,刘子平见到了葛晓辉的父亲。葛晓辉的父亲说,那次葛晓辉与他吵架之后,他赌气说要离家出走。说赌气也不算对,葛晓辉说这话时一脸高兴,嘴里还嚎叫着粗野的旋律,看不出一丝生气的样子,应该是深思熟虑蓄谋已久。葛晓辉说自己永远不做俗人,说生活不需要眼前的苟且,他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行。只是他准备得马马虎虎,他除了要饭用的搪瓷缸子外其它的啥也没带。
在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据说葛晓辉走火入魔了。在一个叫南方的大城市,葛晓辉手举着搪瓷缸子要饭,嘴里嚎叫着别人听不懂的诗句,目光则专注于饭店门口的残羹剩饭。
“晓辉是你父亲找到的。”在葛晓辉父亲的出租屋里,刘子平坐在床脚被四块砖高高垫起的木板床上,听葛晓辉父亲说话。“是你父亲看见搪瓷缸子,最终认出了晓辉。我和你父亲是39军的战友,一个班的好兄弟,转业又一起分配到这个集团公司。你父亲有文化,没几年就当领导了,叔叔没混好,干了一辈子电工。”刘子平想说,干电工其实挺好的,至少比父亲被派在那个叫南方的所谓大城市,当什么狗屁办事处主任强一百倍。事实上,刘子平啥也没说出口,嘴闭得严严的,连葛晓辉父亲给倒的茶水都没喝。刘子平有些听不清葛晓辉父亲说话。葛晓辉父亲和葛晓辉一样,话语中都带有浓重的湖北口音。
刘子平本打算问一下有关父亲的流言蜚语,嗫嚅了一会儿,终究没有开口。葛晓辉的父亲好像也失去了说话的兴致,不再理会刘子平。刘子平觉得葛晓辉的父亲好矮呀,都四月天气了还穿着薄棉袄,棉袄左胸处印有白色的集团公司标识,右胸的衣兜处,的的确确插着两支电笔。他脸色灰黑,容颜苍老,头发黏在一起紧贴着头皮,此时正左手拿刀,右手按住一颗土豆,笨拙地犹豫着究竟是切片还是切丝。
刘子平很好奇,眼前这个小老头就是曾经和父亲一起出生入死的解放军战士?看他窝窝囊囊的样子,身体里哪里来的力气,经常没有缘由地往死里打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也许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喜欢打人,尤其喜欢打自己的儿子,不用任何原因,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吧。在刘子平的记忆里,父亲也经常打他,母亲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怒了父亲,因而连累儿子挨打。
4
关于父亲找回葛晓辉的事情,刘子平是知道的,是葛晓辉回来说的,和父亲的传说一起,已经被传得满城风雨。葛晓辉说,他看见刘子平的父亲和办事处的女会计晚上躺一张床,折腾到很晚才睡觉,两个人都露出了白花花的屁股。葛晓辉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挤到一起,眉飞色舞,比挨了他父亲揍还兴奋,他最后还强调说:“子平你就死心吧,你爸是肯定不会回来了,他不要你们娘俩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刘子平的妈妈在电话里哭闹。刘子平的父亲解释说,别听小孩子胡说,葛晓辉那孩子写诗走火入魔了,他的话千万别信。刘子平不知道葛晓辉的话应不应该相信,但父亲的话母亲似乎相信了。刘子平发现母亲不再哭闹了,安安静静坐在床上,早上出门时母亲坐着,晚上放学回来,看见母亲还那样坐着,似乎一整天都没有挪动过,像傻掉了一样。每天放学,刘子平捡近路以最快的速度往家跑。透过门前的一溜丁香花丛,刘子平看见母亲在窗边露出半张脸,挺耐看的半张脸。刘子平就想起了父亲的脸,感觉都快忘记他的脸了,父亲有好久都没回来了。
放学了,刘子平约葛晓辉一起走,去葛晓辉和他父亲租住的地方,他想好好和葛晓辉谈一谈,让葛晓辉承认自己是走火入魔胡说八道。葛晓辉的父亲不在,葛晓辉说是加班呢。刘子平说,你父亲真辛苦,工作不容易。葛晓辉说,辛不辛苦我不知道,我跟他不是一路人,我们之间没话说。刘子平说,葛晓辉你不能这样说话,所有的父亲都是辛苦的,都不容易。葛晓辉说你父亲才不辛苦呢,你父亲在集团公司南方办事处,那里就是他的王国,他天天搂着胸大脸白的女会计,简直过的是神仙日子。
刘子平生气了,觉得这些话不应该是葛晓辉说的。这些话分明就是老娘们的老婆舌,老爷们吃不着葡萄说酸的羡慕嫉妒恨,怎么可能出自一个未来诗人之口呢。“葛晓辉,你不能再胡说八道,我父亲不会的!”刘子平发火了,说话声音有些急促。“我没有胡说,我全看见了,俩人每晚都睡一张床,满床白瓷瓷的大屁股呀。”
此刻葛晓辉靠在门边,手里扒拉着一把破吉他,房间里充斥着混乱刺耳的音律,配合葛晓辉一头凌乱的长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实在是让人生气。刘子平爆发了,一脚踢在葛晓辉腹部。吉他被踢出去两米,落地发出碎裂的声响。葛晓辉还没有反应过来,刘子平的拳头就到了,正砸在葛晓辉脸上。葛晓辉挨了重重一击,身体变得绵软,顺着门框滑坐到地上。
5
第二天葛晓辉左眼乌青,右腮红肿,两颗门牙松动外凸,明显有逃离口腔束缚的冲动。扈菲菲这次没笑,不但没笑,甚至都没有多看葛晓辉一眼。在同学们惊讶或嬉笑的眼神注视下,葛晓辉在黑板上写下了“刘子平是偷钱的贼,刘子平他爸和女会计搞破鞋”一行字,是标准的仿宋体,字的四周加了装饰花边,旁边还配了插图漫画,漫画夸张得有些不堪入目。葛晓辉环顾了一眼教室,表情严肃,丝毫没有玩笑的意思,“谁也不许擦,谁要是动了我和他没完!”
刘子平不干了,分辩说,“葛晓辉我啥时候偷你钱了,昨天因为啥挨打不知道吗,咋还有心思信口胡说呢。”“昨天你离开后,我发现压在枕头下面的两百块钱不见了,又没有别人去过,不是你是谁,就别抵赖了。”“葛晓辉你不要胡编乱造,咱俩之间事归事,我可真没拿你钱,不信来翻呀。”“早被你藏起来了,一个人藏一百个人都找不着,我上哪儿翻去?我也不费劲了,赶紧坦白交代自己拿出来得了。”“拿你个卵,葛晓辉你是不是皮子又痒了!”刘子平要站起来,被扈菲菲使劲摁在座位上,几次挣扎都没有成功。
嵇老师来了。看了几眼黑板上的杰作,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发火,更没有发射粉笔头。嵇老师脸上又起小豆豆了,高跟鞋也不穿了,上课不但不压堂了,而且还经常晚来早走,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像是有啥大病。语文老师解释说,你们嵇老师健康得很,啥病也没有,她未婚先孕,孕期生理反应而已,不必大惊小怪。语文老师三十多岁,因为身材太矮,板书只写下半截黑板,至今也没有女朋友,但他并不气馁,依然乐观向上。同学们都佩服他判断准确,懂得可真多。
嵇老师讲课声音小了很多,刘子平更是一句也没听清楚。他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过于冲动,不该对葛晓辉下那么重的手。但是,葛晓辉一次一次地胡说八道,也实在是让人生气。
刘子平思绪混乱,战战兢兢,啥时候下课人全走光了都没注意。已经中午了,刘子平依然不饿,胃始终安安静静,没有以任何形式和举动提出过抗议,甚至连一个闷屁都没形成,实在是善解人意。想找本书看,却发现扈菲菲对课外书清理得极其彻底干净,竟不存在一条漏网之鱼。在找书的过程中,刘子平发现扈菲菲的书桌里,以扇面的形状排列着五张人民币,五张鲜艳红润的百元大钞。“这个扈菲菲,真是有些意思,傻的好可爱。”刘子平心里涌动着一丝暖意。刘子平突然就有了想吃东西的欲望,可要命的是他已经走不开了。他特别留恋之前不饿的感觉,人要是一直不饿,永远也不吃不喝不用钱该多好呀,人要能那样是不是就是神仙了。刘子平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像一尊守护神般纹丝不动,一直等到扈菲菲再次到来。
6
和葛晓辉发生冲突后没多久,刘子平就不来学校了。他一连好几天都没来上课,扈菲菲心神不宁,不知道刘子平为啥不来。除了扈菲菲,没有人注意刘子平来没来。嵇老师终于坚持不住,为了保护爱情的结晶休长假去了。代理班主任语文老师,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对嵇老师未婚先孕的休假行为十分抵触,进而变得狂躁不安,目视女学生的眼神开始放射绿光,对待男学生则整体忽略,对缺谁少谁一律视而不见。
葛晓辉发现有机可乘,拿了本诗集移坐到前排,屁股毫不犹豫地占领了刘子平空下的位置。扈菲菲对待葛晓辉一点情面不讲,抄起圆规手起刀落,朝葛晓辉大腿连戳两下。在葛晓辉杀猪似的嚎叫声中,扈菲菲逼问葛晓辉刘子平的去向。葛晓辉哀求说,我真不知道刘子平去哪里了。你们关系那么好,你都不知道,我哪里会知道呀。
扈菲菲不依不饶。“你不知道能行吗,要不是你造谣生事,刘子平也不会离开学校,这事你脱不了干系。”“我承认钱的事是我冤枉他了,我爸把钱拿走也没和我说一声,我真以为丢了呢。但是刘子平他爸乱搞男女关系这事,我可没胡说,是我亲眼所见,那个女的长啥样子,姓啥叫啥我都清清楚楚。”
扈菲菲朝葛晓辉笑一笑,没有再次使用圆规,她竟然意识到应该保持淑女形象,不能表现得过于暴力。她改用徒手了。她伸出四指捏在一起,揪住葛晓辉的耳朵。“放学后和我一起去找刘子平,找不回来可有你好看,我拿你耳朵当下酒菜吃!”扈菲菲腾出另一只手,拍了一下葛晓辉的脸颊,摆出了一个妩媚的笑脸。在葛晓辉连声“哎吆、哎吆”的求饶声中,扈菲菲放开了手。
7
寻找刘子平,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去他家了。好在葛晓辉轻车熟路,引导着扈菲菲,超近路七拐八拐,十几分钟就找到刘子平家了。葛晓辉穿过门前丁香花丛。扈菲菲在丁香花丛前停顿了一会儿,她有些胆怯,不敢直接走进刘子平家里。她第一次看见开得如此浓艳的丁香花,雪白的,淡紫的,一簇簇紧挨着,遮蔽了枝干上尖细的叶子,花的香气弥散着整个院子,呼吸一口,口齿间都存有淡淡的幽香。
院子里和屋里都安安静静的,没有人活动的声音,很显然刘子平没在家里。在里间屋子的床上,他们发现了刘子平的母亲。刘子平的母亲平躺在床上,基本看不出衣裤包裹下的躯体,脸灰灰的,头发被压得偏向一侧,发丝凌乱地交织在一起。她目光呆滞,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她两个手腕和脚腕上都绑着布带,布带的另一端被系在床的四角上。刘子平的母亲,就这样被固定在床上。
扈菲菲看不下去了。她解开了刘子平母亲手上和脚上的布带,想扶她靠坐在床头,帮她把头发理顺。刘子平母亲扬手打开扈菲菲的手,不让扈菲菲挨近自己。她自己双手支着床,像木匠用的曲尺一样,一节一节打开把自己支撑起来,扈菲菲仿佛都听到了她身体内骨骼之间摩擦的咔咔声。
扈菲菲问她,刘子平去哪里了?好一会儿刘子平的母亲眼珠转一下,脸上稍显出一些活气儿。她自问自答说,我家子平呢?我得去找子平,让他去医院做检查!扈菲菲双手在刘子平母亲眼前不停地摇晃,又不敢直接挨上她,去阻止她起来。扈菲菲急得脸都红了,嘴里不停地说,您就待在床上别下来,我们这就把刘子平给您找回来。
在刘子平家小区门外,街道南侧的建筑工地,扈菲菲和葛晓辉找到了刘子平。准确地说,是刘子平先看见了他们。刘子平站在一栋浇筑完第三层楼板的建筑物上,肩上拖着水管,正在给混凝土楼板洒水养生。他居高临下,先看见扈菲菲和葛晓辉。扈菲菲!扈菲菲!刘子平扶着楼板边缘的安全护栏,喊扈菲菲,把头上扣着的安全帽掀下来朝扈菲菲晃动。扈菲菲寻着喊声,稍微仰头,左手遮挡在额前,她认出了夕阳照射下的刘子平。刘子平穿着肥大的工作服,阳光把他的身影拉长扯大,从他站立的位置一直铺到扈菲菲眼前。扈菲菲感觉,站在高处的刘子平,已经不是学生的样子了。
沿着运送材料的坡道,扈菲菲和葛晓辉走上了三层楼板。刘子平赶紧跑过来,堵在坡道连接楼板的入口,不让扈菲菲上来。“赶紧下去,没戴安全帽不能上来,老板看见该骂人了。”扈菲菲伸手推开刘子平,一步抢上楼板,还把刘子平手里的安全帽抢过来甩在地上,安全帽在水泥楼板上翻腾着滚出去挺远,发出极其不满的“喀拉、喀拉”声响。扈菲菲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咋地呀刘子平,还真把自己当成农民工了?去把你们老板叫来,我问问他,雇佣童工违法不。”“别闹了菲菲,老板对我挺好的,没给我安排重活儿,专给浇筑完的楼板洒水养生,2小时一次。”“你还挺满足是不?是不是要在这干一辈子呀!”面对扈菲菲的咄咄逼人,刘子平不敢再言语了。
葛晓辉站到刘子平跟前。葛晓辉给刘子平赔礼道歉,说丢钱的事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说子平你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等你挣到钱伯母的病恐怕早耽误了,咱们一起想办法,总能弄到钱的,不行我管我爸借去。葛晓辉这番说词逻辑清楚条理清晰,刘子平认定葛晓辉绝对没有走火入魔,是个对诗歌有狂热喜爱的正经文艺青年。“但是你爸的事我可没撒谎”,葛晓辉强调说,“你爸太不是东西了,抛妻弃子,不行就去找集团公司纪委去,不信没人管。对了,那个女的长得和菲菲有些像,也长个坚挺的鼻子,姓名很特别,我都记住了,她叫车蔓。你爸厚着老脸整天围着人家转,车蔓、车蔓地叫个不停,恶心死了。”
听到葛晓辉说车蔓这个名字,扈菲菲突然就发疯了。她张狂着双手去撕扯葛晓辉。葛晓辉吓得狼狈逃窜,他们俩像玩老鹰捉小鸡游戏似地在楼板上来回折返跑。慌乱中葛晓辉踢到了安全帽,安全帽再一次遭受撞击,这次直接飞楼下去了,发出凄厉的碎裂声。随着声响,扈菲菲像被卸了劲的发条,突然间就瘫软不动了,她蹲在楼板上哭了,说葛晓辉你胡说,葛晓辉你一直在胡说八道,我要杀了你!声音完全没了先前的声势,显得有气无力苍白可怜了。
谁也没注意刘子平母亲是怎样上来的。她嘴里嘟囔着“子平跟我去医院做检查”,在楼板上直往前走,等到刘子平和葛晓辉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她越过安全护栏,伸展开四肢,很像一只巨大的金属圆规造型,飞扑向地面。刘子平懵了,仿佛自己的身体被巨大的圆规洞穿后,钉在了水泥楼板上,再也无法移动半步。未来诗人葛晓辉眼里所看到的,像是一只大鸟飞过,拉扯起巨大的暗影铺到地面,竟遮盖住了如血的残阳。扈菲菲看见什么了呢,她啥也没看见,她被吓傻了,呆坐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一张俊脸竟变了形状略显狰狞,惨白得觅不见一丝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