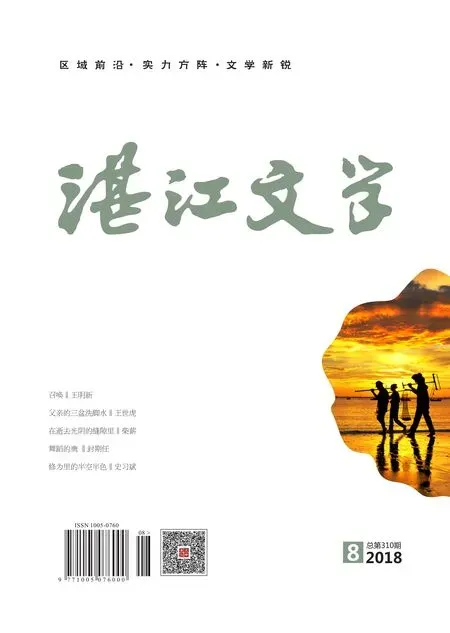距离的背后
◎ 殷鉴
因为永利是老相识老朋友,所以客套恭维的话就不说了,而是直抵诗集的要害与核心。需要预先解释一下题目的含义,所谓“距离”,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诗集里的作品与杰作的“距离”,二是指永利作为诗人与优秀诗人的“距离”。所谓“背后”,是指这些“距离”所隐藏的问题和原因。在我看来,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只有当他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找到了原因(其实这很难,因而才需要朋友的真心帮助),才可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新的攀登,从而登上新的艺术高峰。所以,希望永利把我的发言看作是朋友间的真心帮助。
读完诗集,应该说,诗集所涉及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不可谓不丰富,所使用的意象也不可谓不独到,主题也不可谓不多样,但掩卷回想,除了某些机智的语句能为人称道外,几乎没有让人印象深刻、念念不忘并希望反复咀嚼的篇章。为什么会如此?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便成为我想进一步探究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我以为主要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1、依然缺乏自己专属的艺术符号和意象标识。一般诗人与优秀诗人的“距离”之一,就是后者常常有自己专属的艺术符号和意象标识,并以一些成功的作品作为标志。比如,提到闻一多,读者脑海里立刻就会闪现出“死水”,提到郭沫若,读者脑海里就会即刻闪现出《凤凰涅槃》和《天狗》;同样,提到戴望舒,读者脑海里会闪现出《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提到卞之琳,读者脑海里会闪现出《断章》《元宝盒》,提到徐志摩,读者脑海里也会闪现出《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提到舒婷,读者脑海里就会闪现出《双桅船》《致橡树》……而这些艺术符号、意象标识和作品,也几乎成为他们艺术成就的代名词,成为他们作为优秀诗人的不二标志。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一位诗人无论他写过多少诗,出版过多少诗集,如果他们依然没有自己专属的艺术符号和意象标识,没有自己代表性的诗篇,也就没有辨别度极高的辨别物,这就意味着不仅他的艺术成就很难被读者认可,他也很难成为优秀的诗人。
2、碎片化的意象呈现。具体到诗集里的每首诗,意象不可谓不丰富细腻,但合起来究竟想表现什么,永利似乎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个作品并没有形成严谨的逻辑结构,这既无法让读者准确把握诗欲表现的主题,也无法形成深刻的思想穿透力。这不仅是一般诗人与优秀诗人的“距离”之一,也是我把永利的诗称为多具有想象的张力而缺乏思想的张力之原因。优秀诗人不应该只是展示想象,而是通过展示想象而抵达思想,也就是说,他要让进入诗歌的所有意象和细节,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地呈现他要表现的主题,无论其深刻与否。诗歌意象绝不能是碎片化的“自在”的随意呈现,而必须是合逻辑的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古人所谓的“匠心”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地方。诗里出现什么意象或删去什么意象,先出现什么意象和后出现什么意象,既不是随意的铺排、不经意的点缀,更不是为所欲为的呈现和堆积,而是诗人精心结构和安排的结果。而这个精心结构和安排的出发点就是主题的表现,意象是否是主题所需要的,能否恰如其分地呈现主题,如果意象是主题所需要的,如果能恰如其分地呈现主题,它们就是合逻辑的;如果相反,它们就属于枝蔓,属于多余的赘瘤,属于碎片化的意象呈现。
所以,我个人觉得永利作品的这种碎片化的意象呈现,是其忽略结构的结果,因为碎片化的意象呈现必然带来碎片化的结构,而碎片化的结构必然不足于支撑起一个严谨坚实的深刻主题。而优秀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特别重视诗歌的结构。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以经典加以进一步阐释。卞之琳的《断章》为读者熟知,表面上看,诗的意象“断”而散,但实际上则是卞之琳精心结构的产物,是主题表达之必需的结构。按诗人个人所言,《断章》是要表现一种“相对”的观念。而“相对”,就是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动之中,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一成不变就成了“绝对”。那诗人如何通过意象来表现这一主题呢?诗人运用了“对应手法”,或者叫采用了对应结构。我曾把“对应手法”称之为“诗歌主要的结构原则”,即任何一首诗都离不开“对应”,都或隐或显地使用着各种“对应”。《断章》虽然只有四行、两节,却处处显示着这种“对应”。其实每一首诗都有其最合适的结构,它们或“对应”,或因果,或假定,或转折……,关键是诗人必须找到某个主题最合适的结构,从而把主题有力地凸显出来。当然,我所举的《断章》只是一首四行的短诗,结构安排相对容易,而篇幅越长的诗,结构起来才越困难,而正是其越困难也才越需要精心结构,才能让主题更有力地凸显出来。
3、少余味。这是我读诗集的第三个感受。诗的味道几乎都呈现于文字之内,而绝少诗该有的“言外之意”,这让诗所表现的意义显得过于单一,也不够含蓄丰富,更缺少让读者进行联想破译的空间和机会,从而造成了诗意的单薄与不足,于是才称之为“少余味”。而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优秀诗人的优秀之作,如果说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富余味”。在那些作品中,你总能读到一种“言外之旨”,因为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地展示生活细节和自然意象,而是通过生活细节和自然意象来营造一个更宏大更含蓄的结构,用来隐藏诗人对生活和自然别样的理解。当读者破译了隐藏于诗歌里的诗人对生活和自然别样的理解,就会感觉诗“富有余味”。其实诗是否“富有余味”,是评判一首诗的价值高低及艺术与否的主要指标。诗如果能让读者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价值就高,艺术性就强;诗如果读了之后只感觉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价值就低,艺术性就弱。杰作之所以是杰作,常常就是因为它能让读者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哪怕只有短短的几行,像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总是能让读者联想起超出“春蚕”“蜡炬”之外的一些东西。
那诗集里的诗为什么“少余味”呢?当然是没有采用能产生“余味”的技巧。翻读《自在与拷问》,总的感觉太过写实,或者太拘泥于表现生活和自然的实况实景,几乎没有运用超越的技巧,也就是几乎找不到隐喻和象征的运用,这就是诗“少余味”的原因。“余味”常常是建立在运用隐喻、象征的基础之上的。李商隐的诗之所以“富余味”,是因为他用“春蚕”“蜡炬”来隐喻自己,而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礁石》、舒婷的《双桅船》之所以“富余味”,则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象征,这就超越诗所描写的物象,而具有了形而上的特性,让读者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成为可能,让读者对诗歌进行联想创造成为可能。所以要想让诗歌“富余味”,就一定要运用隐喻象征。只是可能永利缺少对这样的技巧的重视,才更多采用实写的方法。其实隐喻和象征的训练并不困难,我提供的方法就是学会“情景移位”,用自己熟悉的一种“情景”去表现另一种“情景”,常常就变成了隐喻或象征。比如,《雨巷》就是用男女爱情的“情景”去表现诗人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情景”,《双桅船》就是用“船”和“岸”的“情景”去表现男女分别后忠于爱情的“情景”,《礁石》则是用其面对海浪的“情景”来表现诗人个人的人格精神……总之,一旦能够熟练地进行“情景移位”,就非常方便地营造隐喻、象征,这样不仅丰富的“余味”产生了,也让诗歌更具思想的张力。特别是靠着建立一个贯穿全篇的象征,不仅完全避免碎片化的意象呈现,建立起个人专属的艺术符号和意象标识,而且还会使它成为诗人持续不衰的艺术声誉,久久回响在诗坛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