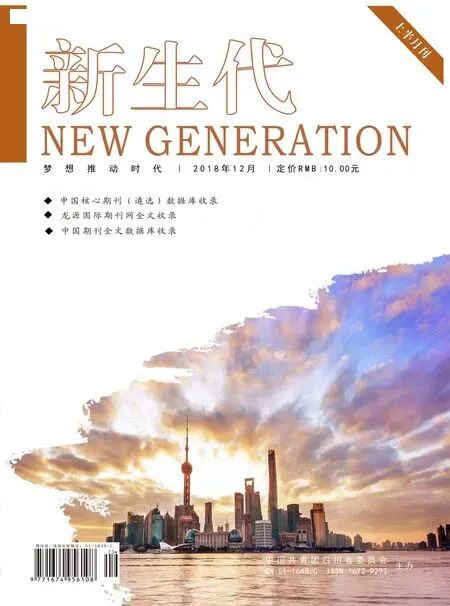中国存托凭证发行人类别股架构问题研究
何政浩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江门
一、中国存托凭证的基本原理
促进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进入A股,是2018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工作之一。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初步确认了发行存托凭证是这批红筹企业回归A股的主要路径之一。同年6月6号证监会又分别发布了《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奠定了存托凭证的各种基本制度框架。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意味着存托凭证即将在中国运用的步伐更近一步。
存托凭证(Depositary Receipts, DR),是指在一国证券市场上流通的代表投资者对境外证券拥有所有权的可转让凭证,是一种在公司融资业务中使用的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存托凭证进行融资的手法起源于美国,JP摩根为了帮助英国企业规避本土企业海外上市的限制,发行了一种可转让流通,代表投资者对境外证券所有权的证书,并将其命名为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ADR)。通过这种工具,美国投资者可以持有代表英国企业证券的证书,英国企业亦变相等于在美国发行了证券融资。此后又出现了如欧洲存托凭证(European Depository Receipt, EDR)、国际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 GDR)等同质的金融工具。中国存托凭证(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CDR)便是参考ADR设计出来的。
中国存托凭证核心架构主要有四个主体,分别是“发行证券企业”、“存托人”、“托管人”与“投资者”。境外发行证券企业同境内存托人订立存托协议,将发行企业的证券交给存托人,存托人同托管人订立保管合同,由托管人对基础证券集中保管,随后,存托人发行代表这些基础证券的凭证,境内投资者可在证券交易所购买该凭证并通过转让获利。
二、中国存托凭证各方法律关系分析
(一)发行基础证券企业与存托人的关系
发行基础证券企业与存托机构之间是信托法律关系,其中发行公司是委托人,存托机构是受托人,基础证券为信托财产。双方通过存托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从实践上看,发行基础证券企业的义务主要包括保证基础证券权利无瑕疵,依发行地国法进行信息披露,通知召开股东大会,向投资者派息分红等;存托人位于凭证流通国境内,其义务为代表境内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负责境内存托凭证的发行、交易、注销,等义务。
(二)存托人与投资者的关系
投资者与存托人之间是信托法律关系,投资者是信托受益人,存托人为受托人。在发行基础证券企业与存托人的存托协议中约定,投资者是信托受益人,而投资者所持有的存托凭证是信托受益权凭证。存托人对投资者的义务主要包括谨慎、忠实地管理、记录和披露信托财产的管作情况,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发行基础证券企业所在地市场及存托凭证发行地市场有关基础证券与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的信息,代投资者向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益等。投资者的权利包括买卖、注销存托凭证,行使表决权等。
三、当前文件未明确类别股架构问题
目前官方已通过一系列文件确立了中国存托凭证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基本框架,在涉及投资者表决权方面的,如是否应当赋予投资者表决权,行使表决权的方式等问题已得到明确,在本文就不再讨论。但对发行证券的境外公司类别股的问题就有待解决。
类别股是指在公司的股权设置中,存在两个以上不同种类、不同权利的股份,这里指因每股表决权大小有别而在流通性、价格、权利及义务上有所区别的表决权类别股。我国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类别股的态度较为保守,目前仅承认了优先股这一形式的类别股,而且公司法对于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范围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不符合普通股或优先股的“第三类”股份,毫无疑问其效力将会被否认。
这种坚决的否定态度在《管理办法》中变得模糊。文件第三条提到对中国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不低于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求,并保障存托凭证持有人实际享有的权益与境外基础证券持有人的权益相当,不得存在跨境歧视。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都不允许除普通股和法定种类优先股外的其他种类股份,目的是防止部分股东设置权利过大的股份类型损害其他权利较小股东的权益。假如认为类别股的存在是对投资者权益的相对减损,那么上述条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否定类别股的合法性的。但是在第三十九条又提到“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具有股东投票权差异等特殊架构的,其持有特别投票权的股东应当按照所适用的法律以及公司章程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特别投票权,不得损害存托凭证持有人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该条文从字面含义可理解为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设立类别股的,只要类别股股东“不滥用”其特别投票权,不损害存托凭证持有人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可以承认类别股的正当性。上下两条文存在相互冲突和表达不明的问题。第三条和第三十九条分别可理解为否认和有条件地承认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类别股架构。第三条中“保护总体上不低于中国法规的要求”的表达过于笼统宽泛,无法定位到具体的权利。第三十九条中“滥用”的形式是什么?若以上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可能阻碍一些存在类别股架构的海外公司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融资。
四、类别股问题的出路
笔者认为,我国对待类别股架构的问题,可以从否定转变为“试点放开”,看实际效果后再决定是否在所有领域放开。
(一)否定类别股的合法性阻碍很多有潜力公司进入市场融资
目前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公司,尤其是新创的科技型互联网公司都采用类别股的架构形式。这类公司采用这种模式是由其公司成长特性决定的。公司创始人及团队具有的专业技能对公司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因此其必须牢牢掌握住公司的运营控制权,确保公司发展始终沿着创始人团队期盼的的路径进行。但同时这类公司前期需要获得大量资金,且多为股权融资,不可避免地面临股权被稀释的风险,类别股架构能很好地解决这个冲突。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长期以来都否定这样的股权架构,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司因股权架构问题无法在境内上市,实为可惜。近期香港已经先于大陆一步,放开“同股同权”的限制,以吸引更多有潜力的公司进入香港市场,避免再发生“阿里巴巴”的憾事。我国也不妨借助中国存托凭证发行的机会,尝试一下新做法,放开对类别股架构的限制。
(二)转变宜采用渐进性的方式进行
虽然笔者赞成放开对类别股架构的限制,但应当注意到的是,该原则一旦放开,将会对目前境内的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造成巨大的影响。为了减少对目前社会经济生活的突然冲击,宜采用渐进性的方式进行改制。首先借助此次在沪伦通发行中国存托凭证的契机,对在沪伦通中进入中国市场发行凭证的企业放开类别股的限制,形成一个试点。同时密切关注投资者的保护状况,考察类别股制度对不同股东权利的影响情况。在考察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后,从得到的反馈信息中评估类别股的架构是否适合在全范围进一步开展。最后待时机成熟之时再对当前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修改。这种“先行先试”的方法能减少法律法规突然变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