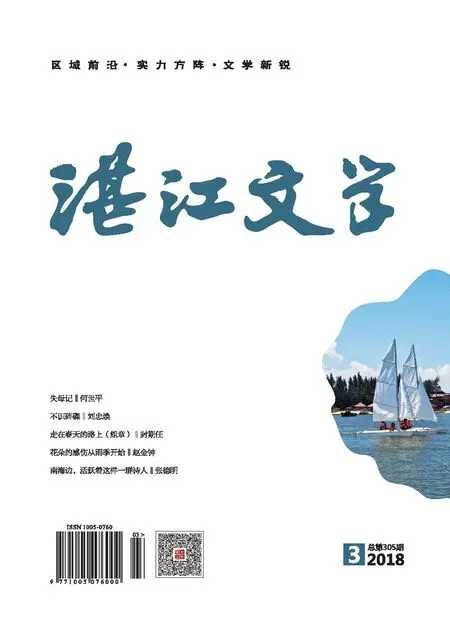潮来的方向
——符昆光小说阅读札记
◎ 周显波
符昆光是以散文登上文坛并获得一定影响力的。近年来,他又一步踏入诗歌创作领域,写作并出版了数量颇丰的诗作,以至于写诗的符昆光甚至渐渐“盖过了”了创作散文的那个符昆光。符昆光自己的身份本身就是跨界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写作领域里诗歌、散文“两手抓”之外,在文学圈外,他又是兼具成功商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本雅明曾经讲过,“远行的人必有故事可讲”,作为跨界者的符昆光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情绪、体验、触感和思考,也的确陆陆续续地通过散文、诗歌的写作一点一滴地剖露出来,但显然,不论是诗歌或散文文体自身的限度,还是写作成就的野心,亦或是作家三十几年来生活历练积累下的一个个庞大的体验块茎,都催促着或驱赶着身为写作者的符昆光尝试着再次跨向另一界。小说创作是符昆光的另一方向,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只发表了两部短篇小说,但这一跨界尝试却之于作家自身来说意义重大,与此同时,阅读他的这两篇作品,也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或启示。
一
毫无疑问,乡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资源和书写对象,几乎每一位现代作家,无论是否出生或成长于农村,那个或荒凉或富饶,或历史厚重或精神贫瘠,或在时代巨轮下奄奄一息或奇幻美妙的中国乡土都是作家们永远绕不开的。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柳青到路遥、高晓声、莫言、阎连科等作家都从自身体验和思考的角度为20世纪文学贡献了乡土书写,而近年来的《望春风》《陌上》等小说也一次次因为书写乡村而引发批评界瞩目或热议。除了“传统”的乡土文学写作之外,微信、微博上一次一次出现的“返乡体”写作或与农村有关的话题都掀起了热议和讨论,由此可见,乡土中国的确是现代中国的重要风景,甚至成了一种认识装置,用以承载乡愁、观察城市、反思现代性、度量历史与人性、探测伦理与文化问题。
深深服膺鲁迅的符昆光,文学启蒙伊始就是阅读和学习鲁迅,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始终深爱着鲁迅。”(1)符昆光自然地从鲁迅小说开创的乡土题材上开始小说写作,他的小说取材的是粤西农村。短篇小说《沉默的酒壶子》(《湛江文学》2015年第7期)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往事。主人公王古过了二十五岁依然还是光棍一条,在用妹妹换媳妇失败后,王古搬到远离村子的茅草寮里。一次偶然中王古救起了一位自杀的女青年叶玫,叶玫因感恩继而爱上王古,两人随后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生儿育女。但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小村依然无法逃脱历史的残忍和暴力,王古夫妇的生活被一只偶尔拾到的收音机打破,收音机被蒙昧的村人当做了特务联络用的电台,身世不明的叶玫被诬陷为“特务”,而百口难辩。最后小说以惨烈的场景结束:五花大绑的叶玫趁着被押送时所乘坐的竹筏行至河中间时,她背上儿子跳水而死。另一部短篇小说《塄坎》(《湛江文学》2015年第11期)题材和写作手法上更接近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小说的中心矛盾围绕着家庭中父与子,儿子想要父亲支持他购买设备成立股份制糖厂,而父亲因为旧观念的束缚一直却阻挠儿子。小说结尾是保守的父亲看着立起来的糖厂烟囱,对儿子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符昆光的两篇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乡土的眷恋与思考,首先,农村在符昆光的笔下表现出诗意的美丽风光与泛着清新泥土味道的民间风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沉默的酒壶子》里“野气浩荡的丘陵大地”和阳光照耀下岭顶的乌托邦一般存在的小房子,会看到王古顶着“干燥”而“凄厉叫声”的西北风,赶着耕牛劳动的场景。也会读到《塄坎》里庭院里生长着葡萄树的景色,还有辛勤劳作后的村人们就着煎猴头菇的香味和大绿竹水烟筒的烟气袅袅,所开的带荤的玩笑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些全部都富有浓郁的烟火气,里面既有化不开的生趣,同时也是作家通过对生活质感的精细观察而用力的描画,此外,在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乡土的熟悉和深爱。虽然符昆光一直强调自己并非来自农村,而是来自林区:“我不是城市的孩子,也不是农村的孩子,我出生于林区,自小浸淫在绿葱葱的山林里。”(2)虽然林区和农村有一定的差异,但林区与自然的亲近,林区经验与土地的天然亲近,所有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构成了符昆光写作的底色,而这层底色促使着他小说写作的初始阶段就自然地走向了乡土文学。在他的笔下,乡土的浑然天成、烟火气息,或雄壮或柔美的风景都有生机地立了起来,动了起来,活了起来。
对乡土的眷恋与热忱是绝大多数作家都具有的,而是否能够与所钟情的乡土拉开距离而反思是要充分考验作家的视域深度和思考力度的,更准确的说,小说创作之中,特别是具有一定容量的小说创作里,对原乡的书写,突破眷恋这一单维角度,而采取更丰富、更复杂的多重视角是一个有追求的作家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塄坎》里,父子所发生的争论和乡土上的现代人与传统的冲突有关,具体而言,是现代观念与传统意识之间的冲撞,在小说里,作家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而对后者持批判或反思的态度。当学会了制糖工艺的年轻人回乡,当制糖厂的烟囱拔地而起时,象征保守的、具有传统观念的父辈获得的是“固执,看来你连那道塄坎都跨不过啦”。符昆光的小说对原乡的书写就不仅仅是一种眷恋之情的投射,而是有意识地对乡土采用了拉开距离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之中放上作家审视天平上的就不仅仅是乡土本身,更有乡土所负载的沉重的历史与精神痼疾。与《塄坎》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不同,《沉默的酒壶子》直接表现的是“文革”。小说不只是书写一个封闭、桃花源式的乡村,也不只是表现了类似于沈从文早期写作阶段里书写的奇情故事,当作家构筑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环境和传奇式的爱情后,这个乌托邦和爱情却被残暴的历史所轻而易举地推倒和碾为齑粉。而这一切的实施者是村里“自作主张”的副队长,更有轻易被谣言煽动起来的那些愚钝的村人,但正是这种“自作主张”和愚钝是“杀死”了王古的女人和孩子的真凶,显然,作家的意图很明确:用这个乌托邦和桃花源的故事来表现政治挂帅特殊历史时期的残暴,以及残暴的背后那些潜伏在人性之中“平庸的恶”,所以,《沉默的酒壶子》后半部分让我们不由得联想起鲁迅的《药》和《风波》。
原乡的故事在符昆光的笔下就显得色彩斑斓,在这色彩斑斓里我们可以辨识出作家远承的是鲁迅的写作传统,近接的则是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脉络——“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寻根小说”等。
二
前文述及,符昆光是散文行家里手,近年又以写诗闻名,读他的小说创作,让人能够清晰地辨认出他“诗人之笔”在叙事性文本中的表现。在他的两篇小说之中,细节的精准、语言的细腻、文体的自觉是非常突出的特征。可以这样说,就他的小说写作而言,虽然在观念与思考力度上存在一定的有待进步之处,但是上述三个特点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忘记了缺憾的存在,我们甚至会为作家对描写细节的重视和语言的讲究而不禁称赞。
符昆光是很注意结构与章法的,《沉默的酒壶子》以一只普通的酒壶贯穿文本始终:酒壶从父亲传到王古手中,这只铜制的酒壶子是父亲逃避生存压力时的麻醉品,也是王古消愁时的伴侣,酒壶更因为王古生活处境的转机成了盛酱油的器皿,王古也与之“疏远”,而妻子被诬陷为“特务”投河自尽后,酒壶再次成了王古苦涩心境的对象物。酒壶在小说中既是主人公生活沉默的见证者,也是人物情感的对象物,更是生长在农村大地的人物的命运写照。从小说的结构角度来看,酒壶子也是小说结构之物。与《沉默的酒壶子》相比,《塄坎》则直接铺设悬念——年青一代与老一辈在创业上和改革理念上的鸿沟,开篇的布局即把读者拉入争执的现场中,继而整部小说都仅仅围绕着这一悬念缓缓有序、不疾不徐地铺陈开来。显然,小说叙事的井然让这篇主题简单的小说增色不少。
余华曾经在访谈之中谈到,“如果细节不真实,那作品中就没一个地方是可信的了,而且细部的真实比情节的真实更重要,情节和结构可以荒诞,但细部一定要非常真实。我认为表明一个作家洞察力的,其实就是对细部的处理。”(3)无独有偶,中外许多小说家都非常注重在作品里细节的勾勒、刻画与雕琢。在符昆光的两篇小说之中,细节的刻画随处可见。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小说机杼》里曾高度评价福楼拜对细节的重视:“福楼拜设法将一切细节都变得重要又无关紧要: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他的注意,被他放在纸上,而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被杂乱地堆砌一处,在眼角之外;它们‘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4)在符昆光小说之中,这种“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正是源自作家对于细节的捕捉。比如:“正月的太阳,像地上的红萝卜,外表红艳艳,里头却透凉气。”(《塄坎》)太阳的热与冷,温度、颜色与质地跃然纸上。再如,写到借酒浇愁时的王古:“当欲火浇上酒精后,他按耐不住自己野性的欲望,然而土墩上之人消失了,他啊的一声杀猪般嚎嚎惨叫,跃起来扑向那块土墩子,用手动请地抚摸着还带余温的坐过的歪斜痕迹,又不时凑近鼻子深吸着气,企盼能嗅出女人特有的气息。”(《沉默的酒壶子》)在这里,酒醉之人欲望燃起却受又备受挫折的场景显然被作家披露得淋漓尽致。
毫无疑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细节的刻画到人物的塑造都离不开小说家的语言手艺。作家如同一名炼金术士一般,需要在那些漫布着生活尘土的、如同顽石一般的事物里提炼出金子和鲜血,然后把这些统统放入自己灵感与技艺的容器里,打造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诗人是作家中的作家,是敏感于语言的高手,因此一旦作家着手写作小说,往往小说,特别是小说语言里别有一番风采。在现代文学史上,冯至的《伍子胥》等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符昆光恰好也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在生活之中是颇为自觉的:“生活有好多细节,但是它们总是随着时光一晃而过,不留一丝痕迹。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一些断句就像河里的鳞片,在我的脑海深处闪烁。”(5)我们的确在他的小说中可以频繁地发现那些闪烁着灵气的句子。如写溺水之人:“有如四根绳头的四肢在空中松软地摆动着”(《沉默的酒壶子》)。再如,“门外的风有牙,啃着手指木木的。”(《沉默的酒壶子》)这些语句都富有神采,与其说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细节捕捉的用心,不如说是作家的语言准确地捕捉到了细节,继而让它们发出微光。而作家在写到乡土中的农民时,并没有对他们的语言予以诗化和书面语话,并没有因为诗意的追求而让乡土之子们被迫操起知识分子的语言,作家符昆光则是选择在符合人物身份的基础之上,采用口语来写出农民的语言来,这些语言也不能视作是对生活的完全复制和照搬,作家有意地选择并使用口语语言,但又是让农民的口语符合身份,节制、传神和富有弹性。比如:老爹玉才的语言:“真是胆生毛,不问半句擅自做主。田都种不好,还想办糖寮。这碗饭容易吃别人早就吃啦,还留下给你路生吃吗,真是死马都敢阉。”(《塄坎》)“胆生毛”、“死马都敢阉”既符合农民的身份设定又有一种来自底层的幽默和泼辣,令人读后忍俊不禁。
三
符昆光在他的文章中透露过自己对于创作的思考:“上乘的散文作品,必须是能够反映时代的心声、突显时代精神。”“散文创作的直接目的是渲染个人情绪,这种个人情绪是用审美的眼光去关照时代,揭开时代丑陋的东西,发现美、表现美和传达美”。“一个大的散文作家,我认为必须坚持以下三点:一、要时刻关注民生;二、要切实促进民主。三、要努力追求正义。”(6)虽然作家在这里谈的是散文的创作追求,但通过对他几篇小说的阅读,也可以看到作家在小说中依然坚持并贯彻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正义精神的强烈追求。从《塄坎》对“改革文学”主题的书写,到《沉默的酒壶子》对创伤历史的呈现与对农村普通人性的思考,以上这些都让人看到了作家对鲁迅以降的现代写实文学传统的有意继承。
今天,当代文学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名”的“小时代”里,这个“小时代”已经耗尽了“共名”及“一体化”的可能,而变得多元、个人化及日常生活化。“无名”的“小时代”中更多的人选择了书写杯水风波,或者在商业下涌动的一波波浪潮中做弄潮儿。但我们看到符昆光的创作,他不仅选择了诗歌写作,而且还尝试着小说的创作,他虽然立足在乡村书写之上,但他绝不仅仅满足于局限在一村、一人来写,而是努力地要在这个“无名”的“小时代”里回身寻找历史的真相,或者写出这个时代的侧影。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符昆光的小说是与热门的写作逆潮流而为,但是通过我们上文的讨论,乡土题材、细节与语言的讲究或诗化、对鲁迅传统的有意学习,作家符昆光以上这些对小说的追求又是不是要奔去潮来的方向呢?
注释:
(1)符昆光:我们永远记住鲁迅,《北部湾那片海》,文汇出版社2015:142。
(2)符昆光:后记,《北部湾那片海》,文汇出版社2015:245。
(3)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4)[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9。
(5)符昆光:序言,《天堂风》,文汇出版社2016。
(6)符昆光:写出贴近老百姓的散文,《北部湾那片海》,文汇出版社2015: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