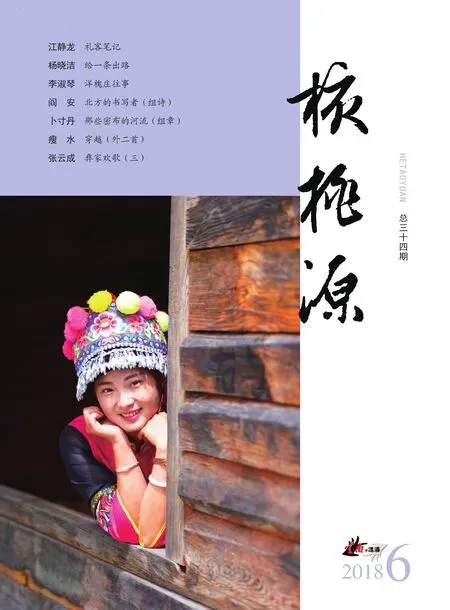礼客笔记
——云南省漾濞县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纪实
江静龙
逢春,岁在2018,农历戊戌年。
这是我记不清第几次深入这片地域,专程就倡导移风易俗规范城乡客事活动作采访。作为一名县级媒体记者,对于这样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总是有着无限的欣喜,我希望通过我的笔端和镜头,让更多的新风文明散播世界,把更多的陈规旧俗解放开来,呼吁更多的干部群众齐心共襄文明。
其实,个中还有着一些私我的小心思,虽然涉世不深,曾经,我也是一个深陷客事烦恼的普通人。而且我深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过一样的苦恼和无奈。
因此,我在本文中一再地通过纵向对比,在历史的维度中,对一些过往细节的叙述,结合自己的一些见闻和感受,一起看乡风文明走过的路程,换一个角度看看我们身处的世界,或者说看一看世界呈现的面貌。这里,我在文中用了很多“当时、以前”之类的词条,那是属于过去的一段,我作此记录,除了记事外,更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改老观念、移旧风俗、扬新风尚,共同守卫我们所处时代和谐的公序良俗,弘扬我们美好新时代的良好风尚。
1.江静龙是一个代号
回想起自己的做客史,内心在不断感叹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反思,反思我们周边的这个世界,热热闹闹、礼尚往来、酬宾客谢亲友的美好传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菜篮子口袋子的不断丰盈,随着一些曲解的新思想新概念不断介入,却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发生了改变,不断地走向了奢靡、铺张、攀比等不健康的另类。
有柬为证!从年头到年末,一些未知的请柬如红花蛇的信子,吐着红光,舔舐着人间。
2010年仲秋,我来到这里,在一所山间小学任教。上班后的第10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乡政府一位素未谋面的干部的请柬,为其儿子办婚;紧接着,又接到了一张隔壁村学校老师的嫁女请柬;然后,中心校老师办搬家客,说是在县城买了房,具体位置不清楚,反正是到如今,我都没到过其家里喝过茶;派出所干警结婚,办在县城,都是单位上的,今后一定会打交道……上班第一个月,我接到了6张各类请柬,当时,我的工资为1670元,我共随了400元的礼。
当时,我连主人家的面都没有记清。当时,他们也没有将我认清楚。当时,客事的场面都极大,人如流水,菜也如重山码在桌上。当时,请客是只认名字的,只需找到财务把当月的工资花名册找来,挨个儿填写即可,甚至于一家两口子会收到两份同一场客事的请柬,我在离开上述几家的时候,主人家基本都没跟我道别。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很多时候,不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只用认识这个名字,大意如此。
就这样,我成了山村的一名教师,过完了山间的第一个月,除去生活、交通、话费等支出外,我的第一笔工资所剩400多元。闲暇时,跟同事聊到这个事情,都说我要入乡随俗,要融入社会,就要交接各类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于是,为了随这个俗,为了路更宽,我频频参加各类客事,随了各种不知名的礼,认识了很多再无交集的朋友,有时人到不了的,礼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带到。
泛滥如疯火,客事完全失控,这样的状态形成根本不需要多长时间。
那时,山间村子不大,学校教师少,学生少,多数村小都是一个老师带一个年级一个班。我所在的小学,四个年级四个班的学校,拢共加起来,基本都从没超过30人。学生还在小灶房里自己烧火做饭吃,每个周都回家背来菜、米,下课后去林子里现捡柴,放学后一窝蜂地涌进灶房,吹火洗锅做饭,锅烟灰尘袅袅升起,然后洗碗洗锅,背书写字,一个学生一周的用度差不多30元,每做一场客相当于两个读书孩子可以在校生活一周。
山野寂寥,地广人稀,总得找点由头,大家聚一聚。
村里有个大事小情,首先想到的是学校的老师们。一来老师辛苦培育孩子,培养一个家庭的未来,最应该感谢,二来还是因为老师能够执笔记账,算得清楚钱文,接人待物不拘泥,三来老师还是一个村中为数不多的吃“皇粮”的人,请他们有体面,这是村人共同达成的最起码的尊重,让人感动。再者,同事几个都是久居此地的老教师,算是本地通,请他们一定不会忘记请上我,落下我的那个在村里是不好做人的。村子不大,于是一个村的所有客事基本都有老师们的身影。犹记得,每次张罗客事的时候,主人家都是亲自来到学校,带上水礼,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的请,先请帮忙写对联,然后请帮忙挂礼记账,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有的孩子在学校读书,都抹不开面儿,都得参加。于是,到了客事当天,几个人便带上对联,骑上摩托,到家里客厅前的台坎上,拉开阵势,你记账,我收礼,他分发瓜子,传烟递水,为前来祝贺的人划上重要的一笔。久而久之,配合得十分默契,各自分管的这摊都井井有条,一场客事随即顺利结束。
有时,同村几场客事一起办的时候,学校老师不够了,村委会人不够了,还会引来一些口角或碎语闲言。
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我接到了一个学生的父亲让我到家里串闲(串门)的电话,一打听,才知是办36岁生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办这么年轻的生日客事的电话,36岁,本命之年要办生日。办就办呗,还要请客——这也是习俗。据说,而立之年后,每一个本命年都是一大关卡,过了此关卡,仿似又可以再来12年(心理层面的自我开解),因此,是人生的大事,值得庆贺。还有一个习俗,若是父母已过世的,那就36岁生日过后,每年都要办下去,每年生日这天,都会有鞭炮响起,有祝福到来,有远近宾朋前来喝酒吃肉。于是,逢甲子,过大寿,大家约定了,生命的短也好长也罢,都是一大喜事。
喜事要办客,是必须的。
2.狭小世界里的无限可能
入乡采访中,在我听闻一些口述后,尽力地结合想象力,断续地勾连了一幕幕客事场景,它们如同旧日的桥段,黑白色的片子里,时光轻轻洒落。
于是,话语滴滴答答中,敲开了一段段旧事。
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36岁后,请先生掐指算过,要将棺材和坟墓提前准备好,名曰做喜材、立生基。做喜材的木材都是最好的,本地没有外地买,请上专业工匠细细心心地做,一层一层地推滑刷细,要有棱有角,有龙或凤,有花有树,有福或寿,每一层油漆都是最精致的,最防腐防虫蛀的;立生基的石材,必须是坚硬的大理石,白色或青色的,大老远拉来,精雕细琢后,请来帮忙人,选定葬址,空下碑刻和棺材位置,待后来填补,然后大吃几天,大肆庆祝。二者的价值少则两三万,多则七八万十几万,都有可能。正所谓,生不平等死平等,每个人出生都没有选择性,生在贫穷百姓家,吃苦受累一辈子,生在大富大贵家,落地就可享清福,这本来就不平等,谁都想生来富贵,但,谁都避免不了一死,既然生无法选择,那就死后一定要公平,你生来富,死后有棺材有碑铭有大理石墓,我虽然生来穷,但这些一样不少,也要跟你一样,活着的时候我可以吃糠咽菜,过世之后一定要风风光光——厚葬是习俗。
如果谁捱不过生命的苛责,不幸走了,这将影响着一个村落三五天的日程安排。本家血亲、旁系外族、亲家老友、朋友小伴……消息不胫而走后,请来毕摩,确定入葬日期,根据粗略估算的办事规模分派任务,采买丧物办伙食,祭祀、鼓吹、迎宾、宴客、送丧、掩土、刻碑、封墓……丧事的流程太繁杂又各有不同,实在难以罗列清楚,只能粗略记之。若是生肖、日程等有冲突,择日显得尤为慎重,这关系着本族的运道和后人的未来,就有在家停丧数日甚至上月的可能,那就更加繁杂了:每天都会有亲朋来吊唁,每天都要准备好饭菜,每天都要有人守灵,每天都要祭祀念经,饮食烟酒香火不断,逢着热天,尸臭熏人,那是一种侵入灵魂的臭,眼泪、鼻涕甚至黄疸水都能将你熏出来,满院都是怪味,还有疫病的危险,尤其是农时过了,农事撂下了,生产荒下了,开支加大了,后人身体熬垮了——一丧荒三年。
女儿多的人家,嫁出去的每人都要请一帮人回来,然后,祭祀的猪羊鸡、鼓吹、大帛、纸扎等一应物事,所有儿女必须一户一套,价值近万元,然后每家都摆一礼簿收礼,这是“姑娘客”,也是习俗。儿女越多,结识的亲家老友越多,场面越大,有时一个院场摆不下,大门外都摆满了,村头摆到后山,礼簿越多,做客的人基本上每个礼簿都要上礼。天热的情况下,人还没送上山,家里祭祀的猪羊鸡全部散发恶臭,无法再食用,只好扔弃,所有纸扎等物全部随火化为灰烬。
这里的丧事是不以请柬请客的,知道讯息的人愿意来的都来。一个村,谁能保证没个事情呢,地宽广人住得散,谁家有个事,这时就全仰仗大家来帮忙了。其实,来多少人,办多大客,都是未知的,一切准备都得按最大限度来办,要不就会冷了来宾,得罪了亲朋。接下来,新坟、七月半、脱孝都要办客,这些客多数都办在坟前,森林安全,防火工作隐患太大。算下来,一个人去世了,亲朋每家至少做3次客,礼金基本不会低于300元的支出。
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参加丧事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血缘的牵扯,但相熟人家的一个人去世后,至少也要做1至3次,要不,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心里不踏实。
实际上,我参加过的不止这些。有一天,我们闲聊时,还理了一下办客的名目,这里,我觉得我有必要还原一些真实的采访画面。采访中,他们说到,大致分类看,“订婚、结婚(头婚、二婚……)、丧事(送丧、新坟、新包、脱孝)、建房(奠基、竖柱、飘梁、立大门、封顶、乔迁)、生孩子(一孩、二孩)、上大学、参军、参加工作、生日、做喜材、立生基、退休、买车、杀猪……”“甚至母猪产仔都想办上几桌”,旁边的人玩笑说,“有什么办法呢,不办客,你做客的钱哪里来?”
于是,朋友越来越多,办客越来越多,请柬越收越多,礼金越随越厚,客越做人越穷,心也越来越空——大家都一样。
3.旁观者对客事风气的思虑
通过频繁做客,村里的人认识了我,周边的人听说了我,我认识了村庄的大多数,包括山、水、人、路、狗叫以及风俗和菜肴。这个村庄接纳了我,这方山水接纳了我,这个狭小世界接纳了我,于是,我接到了更多见证幸福、哀愁和无关的邀请。
我在想,这样的一些习俗,除了一直秉承着古辈传承下来的礼俗以外,很多都出现了演变,还“与时俱进”地添加了诸多原本没有的东西,诸如恶俗闹婚,艳俗祭祀,听说过很多,也见过一些,网络上一查比比皆是。其实,像祝寿过生日,原本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共同祝愿寿星健康快乐、长庚平安的家事,是家庭内部的一种孝道、家风以及感恩赐予后人生命的表现,与外人无重大关联的,却以此为借口,收礼、敛财、大聚、豪办,乱哄哄一天下来,真正的寿星还可能忙出忙进地招呼来宾、烧水泡茶,寿辰变成了忙碌日,传统之孝却不见笑,何乐之有?再者,生日每年都以客事的形式来办理,他人的生日客事也要做,随礼、还礼都必然在一年内完成,礼金的流动成了内部循环,来的人、去做的客基本不变,于是乎,生日演变成了每年必须的一项开支,小气地算下来,无非是每年请那么一些客人来家里吃一顿,毫无利润可言,只剩下无端的开支、无尽的操劳和无谓的耽搁,也许,亲情没有得到加固,相反,来人甚至连对寿星的祝福都没送出一句,即使是亲人,跟寿星表达了什么,说了句谢谢吗?不得而知。
转念想,真正的寿,应该不是36岁吧!活过36岁,应该是很多人都能实现的,不该算为人生的重大事件的。古训云:“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子,七十古来稀,八十为耄耋之年。”而36岁,按生物学分龄而言,仅只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壮年,正该奋斗,正值英年,如何就到了“寿”的地步,还得大肆宴客庆祝,其中的因由除了借机办客的解释之外,实在难以窥探清楚。
我还在想,在听他们谈说之后,对于丧事后面的一系列铺陈,新坟也好、新包也好、脱孝也好,都是缅怀逝者的一种合理方式,缅怀是追忆一个已故人的情思,有着其相对的狭窄性和私人性,是属于某个家族、某个群体内部特有的一种静谧流淌的忧伤情绪,牵涉了太多的人员嘻嘻哈哈地搅扰一番,就显得不够庄重和诚恳,况且这样的事情要持续三年。一个亡者三年后再难被他人记忆,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曾听过这样的说法,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理学上的死亡,躯体在社会中消失,人在社会交际中不再发挥作用;二是坟墓在山间削减,碑铭磨蚀消失,直至成为泥土一部分,实际意义上的消弭于无形;三是认识亡者、记忆亡者的最后一个人死亡,世间再无此人的任何消息和记录,所有关于亡者的东西全部殒灭。
如臧克家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抑或者,永生的多为精神,不朽的多是灵魂,他物定是尘归尘土归土的。
我在想,想当然地想着。其实,在丧事上,一系列的仪式都离不开一位核心人物——毕摩,如果可以,是不是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将这几位核心人物进行集中探讨和培训,在充分尊重民族习惯、祭祀文化、丧葬习俗等基础上进行引导,对相关习俗进行一定的改革,传承中有所保留,也有所摒弃,逐渐形成文明节俭的礼俗,并进行推广和运用,达成普遍共识。
其实,这样的一些细节,太细腻之后,必然会衍生为一个现象的缩影,显微的世界也是一个世界,跟小鸡一样,五脏俱全,都是芜杂凌乱却又有着内在调节的合理秩序。我无法阻止一种庞大又无形的风气形成,我在我蜗居的世界里,我内心烦乱,我抵触,我愤怒,我甚至恨,我的这些情绪多无力,但,我无法不将我内心的这种不爽换个角度来思索,这是我身处的世界教给我的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必备技能,我必定要伪装起、武装好,将自己的悲喜哀怨全部用亮丽的皮毛遮蔽,从容地走进世界之海。
4.聆听后,我感到恐惧
在渐次泛滥、愈演愈烈的客事风气背后,还隐藏着无数的悲情可能。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坦然地参与其中,成为了这种风气的推动者。
一些因客事引发的不幸,不断地在身边发生,我一再地聆听着关于对事件的回顾和反思,某些后悔和想当初的言辞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我倾听着,并将其内化为我灵魂的一种记忆,这是属于恐惧领域的一个因子,我无法说话,我所说的偶尔言语同样苍白无力。
陌生人的故事,在小城悄悄地发生。正所谓幸福的不是故事,不幸才是——他们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
话说,一辆红色轿车在山间带状路上奔跑着,这是从小城出发赶往乡间客场的一辆红色轿车,行程还不足一万,专程为着一份红色请柬的盛意。车辆在山间婉转,四个人一路欢声笑语惊醒了沿途的百花,这是最为诚挚的恭贺,饭毕,按照老搭档,返程回小城,那时,山间的阳光还烈,谷底的库区漾出阵阵凉意,极为惬意,停车休息片刻,再次启程时,女司机一脚油门,车如同受惊的奔马,更像点燃引线的钻天鼠,原地蹿起腾空飞进静谧的水库,溅起巨大的白浪并发出极大的声响,哀绝之声被淹没在水下,谁也不知道她们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她们惊恐挣扎后的彻底绝望……唯独司机活了下来,默默承受着“双开”的处分和偿还巨额赔偿的“债”以及一定量刑的“罪”,被认为“命硬”的背后还有更为沉重的是一生难以弥补的心灵之痛、回忆之伤。
这个事件在他们的描述中太过惨烈,以至于我在听闻后一直怀疑着事件的真实性,而它却又是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确切地说,它的发生,像区域性的气候,真实地影响了我们周边很多人、很多家庭以至于整个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这是一种如同车辆落水般的声浪打乱了宁静的生活水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下乡的人都有意识地避开了那片水域,怕因为“三缺一”而被抓去。
实际上,透过事件,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非,意外之事谁也无法预料,但冷静地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对于当事司机也好,对于喜事家庭也好,对于亡者家庭也罢,都是永久的伤痛,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形中,这样的“债”“罪”和悔,每一笔都是巨额的、终身的、令人窒息的。
喜与悲,忧与乐,往往都在转念间,是相对的,这是世界原本的秩序。悔是最无用且无力的。
仍听说,在客场上,两口子忙于打牌,家里孩子发烧没人管,最终不治身亡;女人背着孩子打牌,等打牌结束,孩子勒死在了娘背上;娶亲队伍闹婚,把新郎脱光扔进水里,被水底的石头磕伤身亡,喜事成了丧事;因为客场上赌博,被公安机关处罚;因为做客喝酒,路上骑摩托出事,喝醉了后闹事,引起纠纷;因为请客吃饭,造成食物中毒;因为上坟祭祀,火烧了森林……不胜枚举的伤情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山间,成为一部惨痛的客事史。
通过倾听,我感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如我一样,恐惧客场背后隐匿的诸多未知危险,实际上,乱做客、滥办客的各种无形支出同样让村人们害怕不已,它是一种可怕的病菌,吞噬着向前发展进步的每一分力气,更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黑色地带,轻巧地就把你拖进贫困的深渊。
5.换算为数字背后的凄寒
在山间,农人迎接一场雨的方式,与实现小康是一样的方式,除了奋斗再奋斗外,就是虔诚地期待,然后大山便以一山葱翠报答雨的恩泽。
遍访,我们一次又一次深入这片地域,不断地深入一户户农户家中,一遍一遍地将他们从活计现场拉回来,把他们的话换算成数字的表述,这个过程具有的意义我们无从言说,然而贫困是有目共睹的,贫穷是一种缺乏某方面的外显,直观的是房屋、衣食和人,一种贫瘠且“愁”的状态,一种毫无安全感保障感的空寂,更是一种内在的痛,无法言说的痛。在若干次的访谈中,他们与我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契合,也不会再为某个数据过多地纠结。
在一年的支出中,他们多数用于生产生活,家有病人的,很有可能就陷入无边的困境之中,“穷得病不得”,这个无法抗拒的支出项目如同地震,一旦发生,必然引起恐惧。然而,还有一样同样让人恐惧,基本上在那些年不受控制的客事时间段里,一户人家一年都要做各种各样的客事,要帮忙很多天,这笔账算出来还是相当惊人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组调研统计数据:
顺濞镇哈腊左村于2014年开始在全村范围内开展移风易俗俭办客事工作,2015年全村客事减少了七成,每户农户的做客礼钱支出下降了三分之二,少支出3000元左右。富恒乡党委、政府于2015年初开展俭办客事工作后,一年里,全乡农户仅客事生活消费支出累计节约了600多万元,随礼花销累计减少了400多万元,两项合计平均每户少支出6000元左右。2016年,富恒乡农村经济总收入1.2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共计8286万元,这个数据中,光做客节省的就有2000多万元。2015年,全乡42户、154人退出贫困行列,2016年退出77户266人。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县农户随礼花销每户平均减少2700多元,全县客事帮忙或应酬节约下来的劳动力30万个左右。
这组数据是粗略的数据,也是基本的数据,真实的数字还在此数据之上,可想而知,从小家到村到乡镇到县,10万多人口的小城光一项支出,足以让人震惊,这对脱贫而言,成了真正的拖累。
出身于农村的我,从农村渐渐融入了城市,这个过程我父母经历了22年的抚养,如今双亲鬓角染了霜。这些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的生活不是想象中的简单,他们有时可能会为了三五十元的用度绞尽脑汁,他们很可能从月初就盘算着我上学的生活费该怎么得来,有时为了去做客,要随礼,可能跑上几家亲戚去借钱,然后过了想办法还,他们为了建房,搭上了一生的努力,为了给我娶妻,不惜借了高利,为了让我顺利买房,他们省吃俭用也要凑我几万……“五角钱难倒英雄汉”,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而普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为了儿女,甘愿献出一切,为了在村中生活坦然,他们借债都要做客。
而其中,随礼从二三十到一百元以下基本随不了的这种态势,让原本拮据的家庭更加吃紧。在乡村中帮忙挂礼时我发现,有的人马上要办客,便在先办的这家高价随礼,为主人家长面子的同时,也为自己储蓄,到自家办的时候,至少保本,歪曲的思想,让重礼成为面子工程。而一旦乡村这样的日子成为常态,一旦这样的客事成为乡村敛财聚财的一种盈利方式的时候,扶贫表格上填上的数据就十分凄凉,谁都无法阻止乡村在某种面子思想作祟时的虚荣,这种攀比与摆阔的不良风气一度成为了近些年甚至现如今很多中国乡村的常态,让人不寒而栗。
做客次数增加,办客名目太多,带来的无形开支难以算清楚,只好厚着脸皮办,硬着头皮做,把脸左右开弓打肿了,依然充个胖子——做客者、办客者的普遍心理,每年都需近万元的随礼花销,这占了收入的大半甚至三分之二,余下的部分如何度日?乡村的开支多数在“吃请”和“请吃”之上,吃穷的乡村,让干群谈“客”色变。
试想之,一个开盘300户的小区,多数是熟人购买,随礼的开支都足以付足首付了,谁不想办客,哪个小区会不被疯抢?
6.疼痛中闪烁着耀眼的忠诚
疯狂的请吃和吃请后,半夜醒来,大家都在反思,经济、精力、时间、劳力、亲情、风气、发展……都去了哪里?一笔笔吃亏的账目从深夜走进了黎明,从黎明走向了阳光,逐渐明晰起来。
这里,我框架性理了一下漾濞县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的发展脉络:
2012年起,在全县各重大会议上,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干部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就移风易俗客事从简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建议,同年年初,漾江镇双涧片区率先成立了彝族支系罗武族“红白理事会”,并挂牌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和执行;2013年开始,漾濞县部分村组有益探索开始规范客事从简活动,减排场减菜数,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相关理事会章程和职责等内容;2014年,富恒乡罗里密村、顺濞镇哈腊左村、漾江镇荨麻箐村等村作为试点先行推行,并将其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做法进行总结和提炼,取得良好反响;2014年,漾濞县针对国家公职人员办理客事情况,出台了国家公职人员客事办理规定,从“关键少数”上作规范和约束;2014年4月,富恒乡6个村全面推行,上述几个村的做法不断成熟,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不断巩固和提升,影响不断扩大,在推行中再系统地进行了总结和提炼;2016年3月31日,漾濞县委、县政府在总结上述村庄乡镇探索经验后,在2016年县委第37号文件中,发文推行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方案,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组,并成立了办公室,全面推行此项工作,成功总结出推进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五同五一”的“漾濞样本”;2016年5月,大理州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推进会在漾濞召开,漾濞成功经验被各级重要媒体大量刊播,并被部分领导专供材料刊载后呈送至中央领导,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2016年9月23日,县文明办就整治不文明闹婚行为发文,整治不文明闹婚,倡导文明新风;2017年6月19日,漾濞县“两办”再次发文,成立了由县委宣传部、县委政府督查室、纪委监委、文明办、民政局等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县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督查组,为推进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和组织保障;2018年3月,云南省纪委、监察委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对农村婚丧喜庆事宜进行了“订标”,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走出区域性困境,迎来了全省齐头并进的大好明天。
政策推行中,痛感遍地,先行的“被开刀者”是痛苦的,也是骄傲的。这是在采访中,我所受感动极深的场景和话语。
“我是党员,这个事情上,何消村上来做工作。”这是富恒乡罗里密村洒高密村民小组李勇面对我们的镜头说的原话。李勇今年58岁,有着33年的党龄,原计划前年为自己“立生基(喜坟)”时大办一场,风光一回,恰逢全县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客事从简工作,本来卫生筷、油盐作料、干菜都提前买好了,客也请好了,“想着自己是一名党员,村里有很多人看着自己,不办也许他们会觉得我没面子,很倒霉,其实我是这块工作的带头人,面子大得很呢。”后来,他把办客物品退的退,周围的亲朋好友买的买,留下了一部分,请帮忙人把生基也立好了,更没有耽搁了生产生活,成了此项工作的模范带头人。
私下,我跟李勇聊到,他自己成为一项工作的先行者,心里苦不苦?他红着眼,哽咽了。富恒乡一直都盛行立生基,且办得都大,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去年儿子结婚就有过相关考虑,因为过一年要立生基,连着办事亲戚朋友受不了,就打算大办立生基,婚事就免了,这已经是最朴实、最本真、最换位的谋划了,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现在风光不了了,客也办不了,这些年做出去的客钱也收不回来了,能不伤心吗?他的委屈,他的苦楚尽在不言中,尽管有太多的委屈和苦楚,他将其吞咽下去,忍着内心的痛,支持党的事业,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忠诚、担当和伟大。
在富恒乡,在漾濞,像李勇这样的党员,每人都挂包着几户人家,不仅自己不办,还专门宣传政策,劝阻想违规办客的人家。一年多,李勇成功劝阻了一家想办二胎客事的邻居,并说服兄妹,在自己母亲的丧事上,按照理事会章程和村规民约要求,主动减少了纸扎、祭品的数量和规模,“纸扎这些再多,也就是烂在山上,一把火烧了可惜了,不如把这些钱用来给80多岁呢父亲养老。”厚养薄葬、尽孝在生前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漾濞县卫计局局长罗欣荣谈起来也是深有感触,罗局长两兄弟在漾濞都是实职正科级干部,一年多前,瓦厂乡老家奶奶去世了,后家人、亲朋好友纷纷准备鼓吹、纸扎、祭品等一系列治丧物品,按老规矩,够忙活好几天。在他们的坚决制止下,一应丧物基本简化为一套,丧事办得节俭、轻松,既传承了民族风俗习惯,也简化了办客的程序,及时送亡人入了土。后来,其父亲提前已准备好两头肥猪、三只壮羊,在生日上也准备风光一回,后来,两弟兄分别多次做老父亲工作,终于做通了,生日当天,一家人带父亲出门旅游,并在外包了席,其乐融融的一家人过了个难忘的生日,据了解,自他们家这样办理之后,当地群众纷纷效仿,很多老人都有了“旅行祝寿”的待遇,当地生日大办客的习俗逐渐变为传统的家宴。
正如当地人所说,像他们这种不是办不起客,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党员,是领导干部,是一面旗帜。
在平坡镇向阳村,熊大爷不无感慨地跟我闲聊到,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抵触,“老规矩”“老脑筋”一下转不过来,想不明白,做客、办客是无可厚非的,这些都要管,管宽了吧。后来,村里的党员、村干部带了头,苦苦做工作,大家都这样做,慢慢地他们也接受了,现在真的感觉这个政策好,钱也节约了,时间也省下来了,是个老百姓得实惠的好事。
脉地村委会的一位大叔跟我谈到,他结婚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婚事不请客、不待客、不办客,至亲好友帮忙,只是吃一碗米线,嫁妆基本都没有,接媳妇要么是新郎去背,要么用骡马接,一律不准用机动车辆,一切以节约为基准。
——这样的娶妻场面在我辈看来,貌似想象不出来,而这却在妻子的爷爷口中得到了证实,他说确实存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地的婚事都极为轻简,彩礼、嫁妆等基本不需要,没有更多的客套和礼节,娶妻真的只是娶回这个人,仅此而已。
因此,至于一二十年中为何演变为前文所述现象,我仍不明白!
7.新风踏歌扑面来
客事名目减少、规模缩小、开支节俭、人情债缩减……这并不意味着彼此间情分的减淡,相反,大家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在发展各种生产“广开源”的同时,减少了一些不必要客事的支出,“节流”后的劲头,是轻装前行的如释重负,更多的人力、财力、精力都集中致力于脱贫致富上,少了纠纷、少了烦恼、少了奔波,多了和谐,多了温情,多了满足,大家都富了,社会风气就正了。
大山深处,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每一个硬币都用在了能够使劲的地方,每一丝好钢,都用在了紧要的刃口上,这种风气转变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推动和表率,是更多人的无私付出和奉献,也是很多人的无限期冀和祝福。然而,节俭办客,不能偏见为不能办客,传统的婚丧事宜,是人生极为重大的事件,在倡导不大肆排场浪费、节俭文明的背景下,客场上,一些习俗便如春风般铺洒开来,让一些久远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气息成为日常,成为了客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鸡街乡的吉用伟,被人称为“刀王”,刀王舞的是大刀,大刀舞是彝族“腊罗”支系的一种民间舞蹈,这是一种兵器舞,源于古时彝族祭祀活动,据说能够辟邪驱魔、永保安康,这种舞蹈融兵器的冷与人情的暖于一身,集舞蹈的柔与兵器的刚为一体,将民间的淳朴与艺术的精美结合起来,从祭祀活动中一步步演进到艺术舞台上,搬到了节庆活动、民间喜事之上,成为了漾濞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刀王18岁开始学艺,历经10年的努力,他出师了,一出道登台便成了打歌场的中心,“刀王”之誉名号渐响,大刀舞双龙出海、雪花盖点等36路、108种刀法,在他手中不断精进提升,如今的他,成为了鸡街乡中心学校的一名大刀舞兼职教师,将大刀舞艺术通过孩童,通过走村入寨进行了传承和发扬,他成为了一名名气颇大的大刀舞“教头”。
采访中的他,话语不多,更多的言语就是肢体,舞动的刀光和脚步,他一再地说,他耍大刀舞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会耍,学会的人越多,他心里就越高兴。看得出来,这种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面对镜头,他将言语以舞蹈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吉用伟和鸡街乡38个村民小组的43支“大刀舞”打歌队,用他们的努力,把民间的舞步、文明的阐释、民族的精萃幻化为灵动的艺术,并数次搬上了县庆、核桃节、三月街民族节、昆明、上海、深圳、北京等活动的大型舞台之上,甚至于将其演进了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2013年,刀王吉用伟也被评为了大理州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大刀舞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彝族民间艺术的一次次重要升华。
事实上,光鲜沉寂之后,艺术更重要的仍是归于生活。在农活忙结束,夕阳沉落山背后时,漾濞山间的很多院场里,一堆堆篝火吐出火光,映照着一方天地。一个个民间打歌队,围着火,拉起手,跺起脚,吼出声,将一天的疲乏通过一通大汗淋漓的舞蹈,消解了,文明的种子通过舞蹈和着汗水播种了,发芽了。刀映衬着火,火点燃了夜,这样的山间,又热闹到了半夜,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个队伍,老中青少不分,男女不辨,欢乐之势烧败了很多盆火。要是遇到喜庆事宜,这样的打歌能够将夜跳通,把月跳落,芦笙之声,笛箫之韵,舞步之劲,全部揉为最诚挚的祝福,最浓郁的欢乐,渐渐地,在影像中成了永恒。
在富恒乡,彝族的另一个支系——“聂苏”支系,人口占到九成以上,同样有着这样的一种彝族民间艺术,名曰“路噜则”,这是彝族“聂苏”支系歌舞的主要表现形式,集对歌、打歌、乐器、舞蹈等艺术形式于其中,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表情达意生动诙谐,切实将情感流露在一场场歌舞之中,成为最酣畅最直白的民间叙述。
廊檐水呀滴滴淌,一代做给一代看。艺术也好,民俗也好,文明也罢,中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正是因为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无悔奉献才得以传承,它蕴含着无数的渊源和过往,是一笔难以估量的无形财富,礼客之道,也如此。而这些民间文艺队的存在,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极为重要的笔触,是干部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践,是需要精心呵护和传承的。
一幕幕采访图景不断涌现,更多感动的情节仍在乡间,在深受感动的同时,我更加憧憬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美好前景,乡风文明作为其灵魂之笔,定然在移风易俗推进中饱蘸灵墨,图染出锦绣山河,届时,大地遍布葱郁繁荣,人间满是安乐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