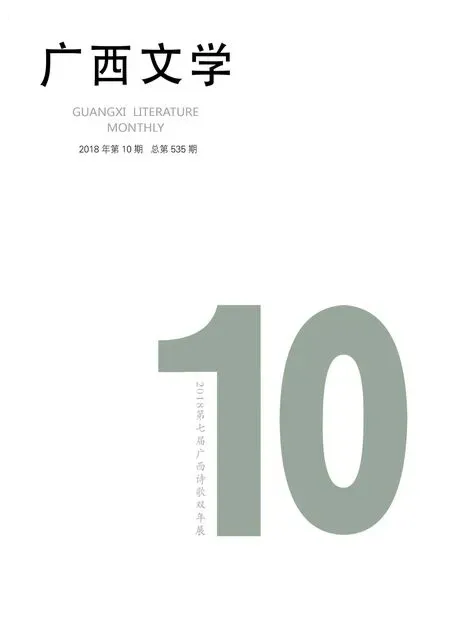乌丫的诗
好啊,浔江
好啊,浔江,它就是东流去啊——这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它流过贵港在你的亲戚老友老去偏瘫了的爸爸眼前流过了好多年,
它流到广东在被冲压机压烂手指的黄忠格打工的那间空调厂下面流过了好多年,
它流过平南在江边绿草我们眼前几栋黄鹤楼一样的房子脚下默默奔流东去,
它那么大,那么宽阔悠长,我们乘坐大巴在夕阳下穿过浔江二桥,
它给我们带来海那边的风。好啊,浔江,
风多好啊,夕阳也那么好——它
在你额前刘海隐现的几根白发上闪耀着辉煌金光,
我想说,我好爱你啊——这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贵 港
贵港和那些热闹乏味的小城市差不多,
我知道,你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它,
但我们还得回来啊,看看家人
兄弟朋友,爸爸和妈妈。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当小孩,
爸爸走不动了,整天就坐在轮椅上看电视
聚焦“三农”,或者海峡两岸。
他脑袋里长了颗血瘤,“有花生米那么大……”
你给我看C T片,我才知道,红色的血
流动在脑子里,原来
是一棵树的形状。
爸爸经常对妈妈发脾气,妈妈不玩Q Q农场了
改玩Q Q抢车位。二舅妈有动脉硬化,
二舅父疑似脑梗死,递烟给我
跟我讲桂柳话的大舅父也有三高和痛风
躲在岁月暗处的病痛,和
病痛的名词,突然
在这个家族里一下子涌了出来。
兄弟们过得挺好,阿孟的父亲去世了,
阿保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有一天
我们在盛世汇景大路边说话,漫天尘土,
眼前是一片工地和耸立的高楼。
贵港变得越来越大,县东街正等着拆迁,
唐人街的玛丽莲·梦露被搬走了,
大东码头卖绿豆沙的铺子还在,
每次回来,你总要带我逛一下,吃一碗
带黄皮焦煳味的绿豆糊。你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永明街,南江村,灯笼桥,东湖公园……
东湖种满了荷花,但我们
很少能看到。贵糖沿江路总是落叶纷飞,
大树在江岸边胶贴缠绕在一起,
那里适合走走路,说说话,我很希望
它能制造一些事情,一些偷欢的情爱,暗夜里
被精心谋划的谋杀,隐藏至深的毁尸灭迹
但贵港一直很平静,那么多年了,
也没什么可以一说的大事。
旧居老房子还没拆,“县东街52号,”
你记得很清楚。你老是说,
小时候房子很大,有地方种花,种菜
有一口井,一棵番石榴树,
你爱在一个沙堆上玩耍,喜欢
偷偷从外婆养的母鸡屁股下面
摸鸡蛋——现在你还是一样啊,亲爱的,
那夜我们搭乘的士回家
我捏一下你的脸,玩弄你的鼻尖,
窗外灯火明亮,一些L E D霓虹灯镶在高楼上,
像一个个悬挂在夜幕苍穹下的巨大门框——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对小孩儿,
在看着世界急速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