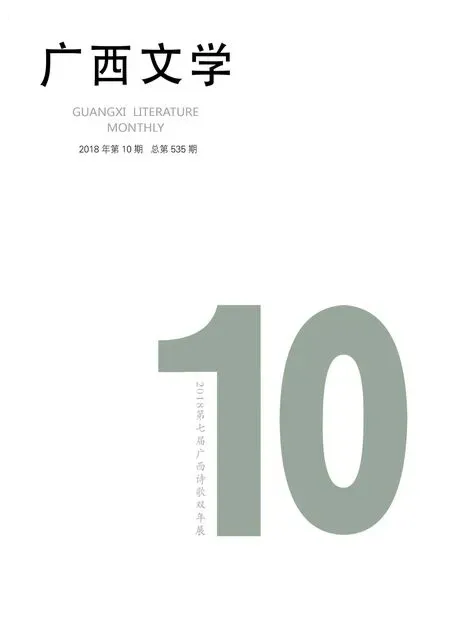刘巨文的诗
2018-11-13 14:29:18
广西文学 2018年10期
湖
水,一直未涨。荒草沿堤岸
向下,步步壮大,几乎抵达湖心,
环绕那一汪浅水的,
嚣张至俯身窥视自我。
也许这茂密的荒草
就是湖的自我,
一个隐秘的信号:它渴望一场猛烈的暴雨
被急速地注满。
自然法则(二)
利比亚,苏尔特,更干爽十月的
街角:阿尔戈斯的水泥墙在见证
革命者猛烈的开火——一个前腿屈膝,
紧抱重机枪;一个蹲着,端起A K-47。
他们都绷紧了屁股。
而裹白头巾的士兵在弹吉他,
小夜曲,还是战歌?你听不到。
但棕红色的弹壳在崩落,乳白的烟尘在升腾,
正午的阳光在闪烁。
另一个正午,同样强烈的阳光,
我,五岁或六岁,蹲在小学操场边,
见证了另一场战争:成群的蚂蚁,
一对一,一对二,二对三……上颚碰撞上颚,
细小的腿蹬开细小的腿。
而蚁流穿梭于被撕裂的身体
传递着战场的消息。它们也在歌唱?
你一样听不到。但我明白,某种黑暗本性
确实无法摆脱。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场……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场,
我想睡着。
躺在球门后,身体
贴住光的湖底——
多么清晰的天空,
不像上一个冬天。
高高的白杨树
几乎落尽,
黄绿的树叶随着季节
滚动,包围我。
哦,忍不住的睡意啊!
向着天空坠落。
我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吗?白杨树在夜风中
高高摆动;雪来了,扫过干枯的树枝,
落满无人的小径。
而梦中,雨水擦亮寂静的天空,
流入深深的谷底;鸟儿
无所畏惧地叫。
我们朝着死亡挺进。
猜你喜欢
农业工程学报(2022年12期)2022-09-09 03:00:50
文苑(2020年8期)2020-09-09 09:31:06
科教新报(2019年34期)2019-09-10 02:43:27
课堂内外(小学版)(2019年4期)2019-05-17 10:11:04
科学Fans(2019年2期)2019-04-11 01:49:38
扬子江(2018年1期)2018-01-26 13:00:59
法语学习(2016年5期)2016-12-18 15:16:23
法语学习(2016年4期)2016-11-27 07:31:26
法语学习(2016年2期)2016-04-16 15:50:09
男生女生(金版)(2015年12期)2016-03-21 10: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