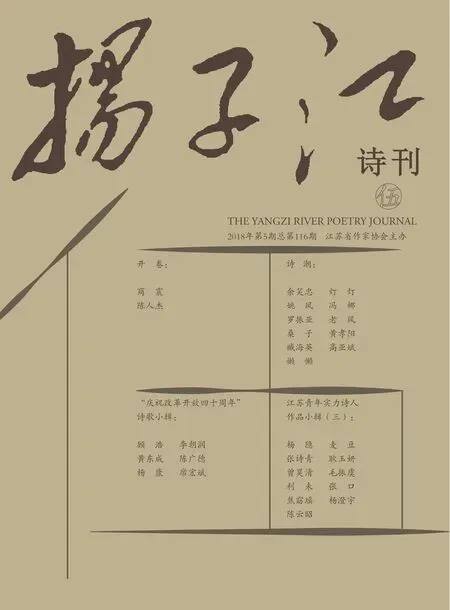偶 遇(组诗)
王江平
王江平,1991年生于湖南衡阳,现居浙江丽水。
途 中
蝉声变细的时候,你去课堂。太阳辣辣的
只有遗弃的道路,承受这场静谧的独走
走过一处,就失去一处。体育馆
小商铺,人们不止一次背过身去
对于树的体验,从未提起
(因不关乎巧合,更不关乎一阵风的善恶)
它们只是顺着街道延伸
在必要的时候,撒下几片影子
遮住你的那片,踩起来,湿湿的、粘粘的
仿佛受热的糖果,融化且流向低处
偶 遇
忽然,我们相遇在枝头
天色未黑,几叶小舟还停在湖面上
我们是在许久之后才搭话的
(偶尔也会踮起脚尖,望望远,并小心地
领受一些来自水底的风,像领受一些事实:
我们互赠的山色拐杖,已散发出苦味)
真是有意思啊,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变瘦
你摸摸胸口,露水一样哈哈大笑
关于你的消失,我是在
一堆雨后的青苔上得知的
我们小心地聊起过许多事情,那些
未说出的部分,也许恰恰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对 弈
风加紧吹,怎么吹,也吹不散这阴云
星期天,出行失去必要。窗口,坐——
初夏时候,雨说来就来。雷
像暴躁的人在云层里,启动一辆货车
是的,连我们的眉毛都在震动
但我们不出声,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在下棋
下,只是一种策略,而非结局
在那宽阔的楚河汉界里,我们不出声
不出声的时刻,雨水飞快翻新。我们
小心地完成每一步,每一步中,我们完成了婚姻
晴朗的下午
现在,他住乡下来了
每天晌午,蝉就凶凶地叫起来
直到睡眠反复于凹陷的枕头(他胸口肿胀
局部开始发乌,这——他是知道的),
午饭后,他趴上窗口
瞥见一具壳子,透明的、精致的壳子
在背部,在光的边缘,一道长长的裂口
锋 利,干脆,仿佛还能听见裂开时,一声小小的——“嘣”
噢,这就是蝉吗?他心头一动
又 仿佛有什么被压住。后来,他是这样描述那个下午的
一切都好,树木也长得飞快,树皮上的壳
金灿灿的,只有数样事情消失了很久
秋 日
一直以来,此诗游离在神秘的某处
会是什么,令我猛然捕获它
哦,今晨,多桥多浩渺的今晨,我漫步在
森林的水边,想想一日又将荒度的必然
浑身便游动着一丝丝偷窃得逞的快意。游啊……
游啊……直到某一刻变成一种可知的存在
(没什么比这更糟心也更令人向往的了)
是雨,忽至且曾敲打一夜的,清凉的平仄雨
原 野
阴云越积越厚
失效的事物,越积越多
几处房屋在辽阔的冬日里
显示出它的小
一位陌生男子的走动
使它们彼此相顾
雨前综合征
守住整个中午,就是守住
这枚正在融化的钉子
现在它是一滩粘稠的液体
现在,它是一块干透的印渍
这就是一枚钉子不可避免的命运
陪同守候的,还有漫长漫长的天气
身体低矮,发霉。而眉毛上空吊住的是
十台发动机,猛烈空转的云层。转啊,转啊……
雨还不落下。雨眼看就要落下
如果落下,那会不会都是曾经的钉子
闷 居
哪儿也没去,小小的屋里,空气围拢我坐着。
冷光照进来时,我摸到自己的双手,
像衰老的丝瓜,吊在空中。青筋
一条条凸起,摩挲着四壁的微风
我尝试抬起它们,但不行。之后
便看了一会儿书,似乎也没看
再往后,外面下起小雨
淅淅沥沥,从云中降下这座小城,
我多少次默数着城中,那些被打湿的
地名,像树叶,一片片飘落地面
曾经我因成功地把它们关在屋外,
而暗自庆幸。现在——雨和雨声
再次降落的时刻,我推开窗子,并确认它们
是否在某个时候,真的触及过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