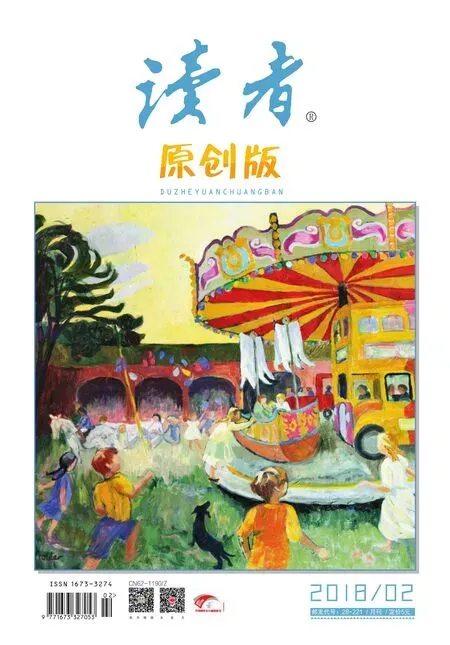丢丢:关于陪伴
文|张悦芊
一
我是在和母亲通电话时得知猫死去的消息的。猫似乎已成为我和家人无话可说时屡试不爽的自然盾牌—“我的猫怎么样了?”我随口问道。
通往学校的路需要穿过一片树林,那里信号很差。我断断续续地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串语气小心的话语:“啊,你的猫昨天晚上死掉了。我们把它埋在了黄河对岸的小树林里。”
我是12岁那年有猫的。从小我养过大大小小各种动物:校门口卖的盛在纸盒子里挤挤挨挨的小鸡,玻璃缸里的鱼,会在阳台上留下粪便的鸟,亚光表皮、多足而蠕动的蚕,背上长出青苔的乌龟……但它们都比不上一只毛茸茸的猫或狗来的真切。
在年幼的我的概念里,唯有这样生动的、体形较大的、与人互动频繁的生物才可以算作宠物,其他的小动物都是父母因不胜其烦而买来敷衍我的。但对于一个刚刚走过千禧年—这意味着在下岗大潮中我的父母双双失去工作—的家庭,并不会因为女儿的吵闹做出收养宠物的决定,而我似乎也习惯了渴望变成遥远的、模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令12岁那年放学回家的我,在看到客厅一角的纸箱里忽然探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时,无法控制地尖叫起来。母亲在厨房里说:“你小声点儿,别吓到猫了。”于是,我又打开房门跑到楼道里高声呼喊了好几分钟。
十几年前的那只猫那样小,蜷缩在纸箱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很多年后,我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看过无数只异瞳的、毛色雪白的、姿态懵懂可亲的猫,以至于初看时激动心软,看多了便也没什么感觉了。
但我的猫不是那样的。它是那么真切,头顶的绒毛因为紧张或寒冷微微抖动着。我们三个人讨论了许多名字,后来因猫总是躲在暖气片或是电视机后面,故命名为“丢丢”。那些年还不太流行给宠物取洋气的(比如Juliet)或是文艺的名字(比如七月),“丢丢”二字朗朗上口、不落俗套,一直是我多年来引以为豪的灵感杰作。
二
2007年竟然已经是10年前了,10年是一段多么沉重的光阴啊,如今我竟也能信手拈来。
我和父母之间变得疏离大约始于2007年,也就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那时我第一次喜欢一个男生,他学习很好,白白净净的,如今想来乏善可陈,但彼时多为他疯狂,写了一本本重复着他名字的日记。
我第一次向母亲提起他时,母亲在洗衣服。当时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开口,但羡慕班里同学说起自己和母亲分享关于心上人的事情时透着的那种亲密感,于是也跃跃欲试地说起了他。母亲奇怪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不要影响学习。”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洗那盆衣服。
我对母亲的亲密情感大约是自此开始垮掉的,这件她或许早已忘记的事,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再后来,我的亲密关系甚至人生中的很多事,都不再与她讲。
而和父亲的关系在那两年更是紧张到随时要爆炸,我们会因为各种琐事争吵。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去书房学习要先经过卧室,于是我会先打开卧室的灯再走去书房,而父亲每次都会大声斥责我的“浪费”行径。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了两三分钱吵,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似乎自己怕黑的心情根本比不上那一点儿电费。
如今回想起来,当初觉得父亲不可理喻苛责我的事情,大约也是贫穷背景下迫不得已的举动,但在本就敏感的那几年里,每次争吵后我都在认真考虑从阳台的窗户上跳下去。2010年的时候,我家小区南面的高层住宅楼还未建起来,那里的旧厂房坍塌成一片废墟,我因为久在窗口俯瞰,甚至连废墟上每一块砖瓦的位置和纹路都记得清楚。
而回过头来时,我的猫永远在那里看着我。
后来我在很多心理问卷里都见到过“你有考虑过自杀吗”的问题,而那片废墟,是我每次答题时脑海中都会迅速浮现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画面。真正站在窗口时其实不会想什么疼不疼的问题,也并非是猫的注视让我对这个世界心生留恋,因为促使我想要跳下去的原因,是我受了委屈,且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被爱过。但盯着那些瓦砾的时候我意识到,即使跳下去这两个问题也并不会得到解决,而我对未来的所有期待则更不可能实现。
这样的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不断重演。当我在恋爱关系和友情中遭受委屈,觉得被忽视、被轻视、无法获得同等的情感反馈时,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想着如何通过伤害自己来使对方愧疚,进而达到对对方的“报复”。这种蠢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淡了许多,在我人生后来的10年里,我再也没有考虑过自杀这件事,大约是越长大越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不再像那个无助的12岁少女那样,手中只有一柄指向自己的尖刀,只能控制力量,无法改变方向。
三
我去所有的地方生活时都带着一只熊,机票行李的限额永远优先留给它。
这只熊其实没什么特殊意义,是舅舅某一年送给我的,但它抱起来手感很好,我一抱就是许多年。
新认识的朋友每每知道我千里迢迢带熊而来都会表示讶异,一是看不惯我强行跨越阶级靠拢小布尔乔亚做派的行为,二是听闻这只熊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有的人性格温和,会问诸如“你的熊叫什么名字呀”“是他还是她”之类的问题,这下便轮到我接不上话了—我从来没想过。
但我跟这只熊讲过的话,可能比和许多时常相见的人一辈子讲的都要多。我每天睡前都会和它说很多话,那时它不再是一只填充了棉花的玩偶,而是有误会没来得及说清的友人、需要坐下来认真谈谈的恋人、无数我白天没机会说出口的话的倾诉对象。
它已经陪了我整整12年,似乎最亲密的友人也没有相识这么久。它像是永远都不会被提起的深夜私语,默默消解掉一天入睡前最后的不甘和留恋,白昼黑夜,四季轮回,渐渐积攒成一段不可割舍的情结。
丢丢,你和这只熊一样,在我的生命里陪我走过这样一段路。我翻遍自己10多年来在所有社交平台留下的只言片语,不出所料,你出现的次数最多。
我和别人提起你时,总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你不像“网红猫”般乖巧黏人,向来受不了热烈地拥抱和亲吻。
自大学始,每年在家的日子超不过两个月,后来又折腾着做义工、实习,有时甚至一整年都不回家。故乡像是远方一个熟悉又朦胧的梦,越来越少地出现在生活中。
我拍下的猫的照片越来越多,有时候在家待短短一周就能拍几百张。但这样的对瞬间流离不舍的堆砌,往往只是因为对未来感到恐惧罢了—我知道我在这里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而生活在这屋檐下的猫,更像是“家”这一概念的具象:你在身边的时候,我就回家了。
但家,又在哪里呢?
那间位于河畔的公寓,我已经离开太久了。18岁,入住6人间的宿舍;21岁,远赴欧洲大陆;22岁,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23岁,住在伊萨卡居住率最高的小区,每日披星戴月地乘公交车回去时,车上常有讲中文的同伴,恍惚间会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故乡。
那么,究竟哪里是家呢?究竟是要在异域用200%的努力加300%的运气挣扎着生存;还是回到孤独的都市,自由而忙碌地快速生活;还是再次回到逃不开的12岁的梦魇里,抓不住任何生活的方向,唯有凭窗随波逐流?
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来不及准备就得知了丢丢连续两周未进食的消息,这令我措手不及却又无计可施。我知道猫的平均年龄也就十几岁,但有心理准备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去的,但就像我知道猫或许并不喜欢家中的新成员(家中新添了一条狗)一样,我知道父亲吸烟多年一定落下了严重的肺病,母亲的腰伤和心脏也早已有了不好的迹象。我当然总是热切地劝说他们常去体检、少抽烟、多休息,但这种隔靴搔痒的客套话谁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用处。就像默默期待我的猫能撑到我回国,再陪它玩耍一次一样,我只能默默期待父母再健康几年,但这样的期待脆弱得好像童话故事。
我刚上大学的那几年,以及刚去法国和北京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些新鲜事—起初是去餐厅吃了一顿饭,后来是感受了异域风情、文化碰撞,或者是花一些钱换来了很多方便。每逢此时,我都会想起他们,心想要是能和他们一起来看这个世界就好了,这样我们之间的隔阂可能就会少一些,而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对抗,可能也会柔和一点儿。
但这只是美好的期待罢了。人生于世,无时无刻都有强加在身上的桎梏—12岁那年是因经济困窘无法离家出走,22岁依然是,如今举家全力支持我来美国读书,他们自然放弃了许多浪漫的念头和眼下的体验。而我并不知道这种父母健康、其乐融融的表面和平什么时候会崩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有心理准备又有什么用呢?
20岁出头的时候,我常和母亲吵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受不了她绵绵不绝的抱怨,鼓励她找寻自己的生活。之后因她并不能突破自己走出家庭而感到失望,不再听她讲述新的烦恼。我和父亲的矛盾似乎止于成年,大约没有了去书房是否要开灯此种小事,经济上又少有纠葛,便也少了很多争吵的理由。
我和他们的和解似乎并不是由于“自己开始工作,遂知道了生活的不易”,而是在接触了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讨论后,才渐渐意识到人的所见、所知、所感都受限于很多因素,一味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要求他人,不但不道德,更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四
丢丢,听到你离开的消息时我并未停下脚步,仍然在路上。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两周,我没有为你掉过眼泪。我觉得自己绝情,又因此感到沮丧,但你离我太远了,你的离开就像是书上一行不动声色的文字,我试图感同身受,却发现早已读丢了情节。
伊萨卡下起第二场雪的时候,我正好在和父母通电话,走着走着,路边忽然跑出一只黑猫来。我从未见过这样主动亲昵的猫,它朝我跑过来,蹭了蹭我的裤脚,然后慵懒地躺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毫不设防地露出肚皮。
它一点儿都不像你,长相、性格都不像。父亲在电话那头评价道:“这就是美国的猫呀。”母亲说:“不要碰,小心有细菌。”而我看着它在冷风中微微发抖的毛茸茸的样子,忽然真真切切地想到你。
世间所有的陪伴大抵如此,有瑕疵、有失落,且最终有无可避免的离别。但这些陪伴让人生变得充实、鲜活、热泪盈眶,即使你不在,仅仅想起你也让我觉得温暖。
谢谢你,我的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