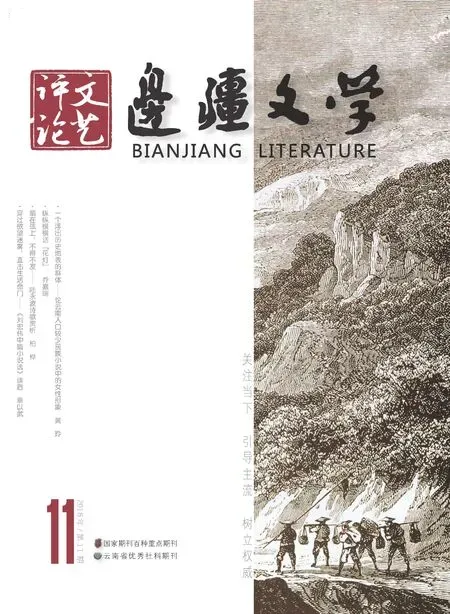本期摘录
黄 玲 一个浮出历史地表的群体——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文学在中国已经形成独立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系统并取得丰硕成果。所以请不要再说什么“文学不分性别”之类的话,以免贻笑大方。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虽然起步较晚,女作家的影响也比较稀薄,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那就是各民族能从事小说写作的女性,都是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在各行各业从事着创造工作的一批文化人。她们在受教育的程度和思想观念上应该与传统的民族妇女有很大区别。性别意识的觉醒在她们身上不应该是个难题。虽然她们的民族意识可能远远大于性别意识,她们的小说也并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但是写作者自身的性别因素对小说写作的潜在影响一定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假装看不到。
乔嘉瑞 纵纵横横话“花灯”
明清时传入云南的灯会,社火以及越调吴歌等江南时曲,与云南本地的民情风俗民间歌舞相结合,便逐步形成了歌舞形态的花灯艺术。当然,它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从其它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借鉴创造,但它的主要来源,是民间的祭祀歌舞和非祭祀歌舞,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戏剧形态的云南花灯艺术的形成,应是在清王朝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的乾隆时期到道光年间。
柏 桦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陆永波诗歌赏析
是的,陆永波写诗,既不为晋升职务、评职称、拿大奖,也不为加入省作协、中国作协,甚至也不为发表、赚取稿费,所以,他常常是率性而为:“点点滴滴,随意流淌,就像山地里的泉水”。笔者感觉,像这样原生状态的写作,确实是没有压力,轻松自在,出产的诗歌真真切切,质朴无华,但如果只是一昧简单地“如果觉得有触动就应该表达出来”,也会有负面效应,那就是下笔随意,打磨不够。笔者以为,一气呵成固然能够保留诗歌原始的精气神,但诗歌毕竟不是微博或日记,除了真情实感和独到见解,语言的锤炼同样非常重要。
章以武 穿过欲望迷雾,直击生活命门——《刘宏伟中篇小说选》读后
从细碎的寻常日子里,洞悉浮华表层下细敏的社会神经和人们内心的焦渴,摆脱对故事情节本身和文本的过度依赖而又要引人入胜,尤其是要令早已被物欲生活催逼得心神难安的读者,越过“似曾相识”的故事本身,停住脚步“扪心自问”,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如何在滚滚红尘中固守“人之初”的本心,寻一清幽之所,安放早已被俗世的洪流裹挟得跟无头苍蝇一般,瞎飞乱撞焦躁不安的灵魂,才是文学作品对当下社会直戳命门的拷问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