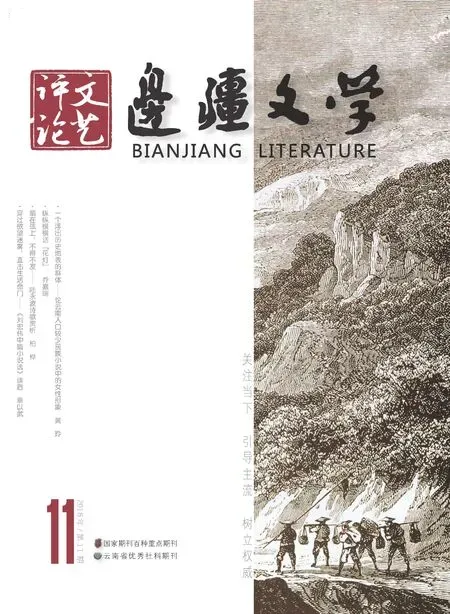泥土的奢华
张 淼
杨友泉是一位植根于农村泥土的小说家。他出于祥云石壁村。石壁世代走老银厂(缅甸),家家如此。进不了老银厂,就进滇东、滇西、滇南、滇北,进西藏、青海、宁夏,卖土锅。穿草鞋,一担担挑着卖,大土锅套小土锅,小土锅里套茶罐。“我的几乎所有的小伙伴都是补锅匠,铁匠,锑匠,银匠,金匠。”(杨友泉创作谈)
杨友泉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就写一个叫农民的人。……这个人,有时是个父亲、农民工,有时是个寡妇、妓女,有时是个上门女婿,有时是个族长、补锅匠,有时是个知天命的糟老头……他们在各种艰险的环境里,拼命发展着,拼命向上着……他们的生命如同大地上的庄稼,一旦收割后,田野立即变得死寂,而在下一波生命来临之前,我借着这稍纵即逝的寂静,尽可能长地回顾一下他的音容笑貌,让他卑微的生命尽可能长地在田野上空逗留、徘徊。”
植根于这片贫瘠的土地,他却用自己的小说,彰显了只属于每一片卑微得让人漠视的土地的奢华!
一、杨友泉先生的小说,是一种奢华的荒诞,这种荒诞来源于小说题旨的多重解构
在《松竹兰梅图》中,族长甘云松的女儿雪兰遇害,引出棋盘村人的恐慌和对汉奸的甄别引发的种种离奇故事,而最终的结尾,却是监视人甘红梅家的所谓探子王国栋和族长在竹刑中“肠壁上的血水光华灼灼……让它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主角。人们举头望时,就看到一颗拖着白尾巴的流星,从地上、从棋盘村村口、从竹丛里,划过竹林,划过满天彩霞,箭一样射向天穹。”这是一个民族封闭、愚昧的展现,也是那个时代人性善、丑的深刻揭示。
在《出师》中,补锅匠杨培金忍受了饥荒年代的种种煎熬,终于出师了。可由于在喊到的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中,有着双方善意的作弊——一方求补锅够数,一方求女儿衣食——可是师道的规则又使他在出师后不得不违背双方的盟约。他只能在一种极苦痛的自责中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把他从师门里逐出来的,现在,只有榛子……榛子会把砸锅的事情说出去的……”所以,“只是一瞬,他就止了步。他不能带她走了”。这既是补锅匠的行业潜规则,更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人遵从的信条;可这又不得不使他违背自己的承诺,辜负了一个善良的妇人弥留之际的托付和一个年幼的弱女子以生命为代价的期盼,使他不得安心!
《弹簧床》可能是谢庄那一代人永远的记忆。“我”和谢龙为试坐龙城的弹簧床,开始引出了我们和谢支书、大双二双在那个青涩年代的情感纠葛。爱情是美好的,可年轻的冲动,却使得一切美好都脆弱得不堪一击。最终,我们不是屈从于命运中那贫瘠生活的物欲压迫,就是被自己那所谓的高贵的骄傲所折杀。青春逝去,我们之间,我们和那个年代之间,“我的掌心已经感觉不到他的热度,冷飕飕的……因为我们中间,隔着厚厚的玻璃。”这里,流逝的,不仅仅是青春,感情,还有更深的失落。
在《疤痕》中,陈大胜额头的刀疤,使他处处碰壁,无可奈何,就用砖刀修理了包工头毕老板,却得到了所有工友的支持。他等来了警察,却是因为同住的小个子工友的盗窃而被关押。在与自己无关的事件中,却因疤痕被重视;阴差阳错地被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英雄,却又在公安局长的“我看着这个疤痕就觉得邪乎,险些把一个好人弄漏了,以后工作要细心”的批示下入狱。他“只想过没有疤痕的日子”,可是,这个疤痕,就只是额头的疤痕吗?
在《跟踪》中,吴书凤用大网把朱虎勒死,却只有一个啼笑皆非的警告:“吴书凤你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鼓弄渔网铁锚,一鼓弄渔网铁锚,捕鱼逮兽的陷阱说下就下。这次你网了个歹人算你为乡人除害,如果你网着良民你不也得搭上?”——意思就是,你弄死了人,警告你不许喝酒!——天大的笑话啊!
在《你得赔我田》中,杨德旺的拖拉机油倒成了茭瓜田的上好的肥料,不知道科学家会怎么解释?
无论族长甘云松还是刀疤陈大胜,无论是剁了小姐手脚的谢龙还是为自家的猪“花白”不遗余力的吴书凤,故事都是荒诞的,不仅荒诞得真实,而且真实得超乎想象。对卑微地活着的“农民”,事情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看到的表象。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似乎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必然的结局,而这一切,都不是卑微的个体所能左右的。荒诞的不是故事,而是我们当下的存在。看似超越了现实的荒诞,却是一种奢华的艺术。就是这种奢华,展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没有悲悯情怀是成其不了真正的作家的。我们永远要关注百姓的疾苦,只要还有人生活在不幸中,作家就有责任关注这种不幸。(杨友泉创作谈)”我想,正是这种悲悯,使他植根于泥土,和近旁的芜杂的生命同呼吸共成长,以超拔的大爱,隐忍人间!
二、杨友泉先生的小说,是一种奢华的色彩,这种色彩来源于天地众生在自己灵性的眼眸里的投影
在《恶之花》中,恶之“花”,不是小孩子的游戏,不是娇艳的花朵,而是“翅膀上有两只红彤彤的大眼睛”的蝴蝶,“在阳光照射下,那红彤彤的眼珠鲜艳得很,就像两洞血。”与之关联的,即是人性之花。“我”,保安,警察和残疾的偷窃者及其妻子花儿、女儿翠和红,就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展现了恶之“花”!是非对错,人性的善恶,没有输赢,似乎谁都是残缺的!
在《松竹兰梅图》中,雪兰是高贵而纯洁的:“她嫩生生地自豪,还很纯真地箍在她刚刚发育的、腼腆的、紧绷着的笋一样凸起的乳房上。她的背景还在不断强化着这一切。她的背景是魂一样细和轻的炊烟,炊烟后面是发呆的青山。青山高处……都是化不开的黏糊糊的黛,它们合力烘托、出卖着雪兰。”就这样的色彩,凸显出一个美妙高贵的女子的圣洁,后来,“只看见雪兰背后青得似乎要遁去的十九座山峰,以及雪兰头顶、左边、右边的酽得化不开的黛。黛,在一点点泯灭,凋敝。”悲剧的由此诞生。
在《弹簧床》中,谢龙令人羡慕的朦胧爱情结束,我阴差阳错地成为大双夜尿的守护者。“微风徐徐,月光把天地万物绣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附近高矮不一的松树,却像一把把柳叶刀,把半空中的月光齐刷刷割下,落在地上,形成了形状不一的阴影。”这样的光影里,“我们的青春就在这样的混沌中挣扎着,困顿着,窃喜着,不声不响地溜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疤痕》中,陈大胜相亲去了,“小路途经油菜花地,油菜花黄灿灿地把小路埋住了。走一段,小路被扯出一段;走一段,又被扯出一段。……过了一溜菜花地就见一个村庄隐隐约约伏在菜花间,绳子一样的小路被脚步一截截逮出来。小路的一头好像系在那个村庄的腰背上,就这么三逮两不逮,村庄就在渺远处拽了过来,而且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瞩目。”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行走,要去天堂一样美丽的村庄跟一个叫玉兰的姑娘相亲,陈大胜一家人的心情像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又像细绳一样的小路。这样精美的景色,和精美的心境,难道不是一种奢华的赐予?
环境描写,场景交代,细节处理,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神来之笔。不仅仅是技艺的精湛,而是作者在呕心沥血地打磨着这个名叫“农民”的人啊!
三、杨友泉先生的小说,是一种奢华的唯美,这种唯美是对人们内心最细腻的雕琢
就在杨天健(《烟垄边上的人家》)浇烟水的早晨,“那雾长得毛茸茸的,鼻孔里马上鼓胀了。”它“收集了沟里的青苔味、墒上的泥土味、田埂上的草青味、烟苗味、机耕路上的苦蒿味、水桶里的泥水味、湖面上的草腥味、男人的汗味——这天地间的味道,被太阳一口吸了进去,然后再慢慢吐出来,依旧把它放回这个坝子,这个坝子就平白多了一种醇厚。”这是一个唯美的早晨,也是一个唯美的季节,即将到来的耕耘后的丰收、生活的丰盈、恋爱嫁娶的期盼,就在这样一个早晨展开。虽然后来有着保护神鸟白鹤的风波、有着浇水烤烟等现实的困挫,可生的希望,依然唯美。一个卑微的农民,“他觉得有一股力在脚底下运行着,他每挖下去一锄,他就会被一种力推送进下一个波谷……”对,是波谷。可是,有白鹤的护佑,有爱情的祈愿,波谷之后,一定是重生的高峰!
寡妇水嫂(《寡妇磨》)和石磨之间,有着不可言传的默契。诸多的石匠中,她只看中了银生。“银生是披着夕阳来的,像镀了层金,从箐口一晃一晃,由一个金龟子那么大,变成了鸟那么大……水嫂就能认出来了。”“银生在屋里晃荡,安静里还隐隐含着一点温情。覆盖在各种物体上的面灰,也慢慢退却了那种漂白,增了种火焰蓝。”在这里,高贵的景,似虚无的幻象,再自然而然滋长一丝恰到好处的风情,那种纯粹的欲望,就至臻至美!所以,“银生和水嫂都把对方当作填充物了……他们才觉得绝望不会再继续苏醒。”自然,美的极致中,灵与肉,混沌不堪而又激情飞扬!“天啊!水嫂在心里呐喊,这到底是最后一道防线,还是最初一道防线……”
当内心之美有如天地之纯正,我们,即可远离龌龊和污秽,无论是人,还是神!
四、杨友泉先生的小说,是一种奢华的静谧,这种静谧既来源于内心静观万象的超脱,又来源于对从红土地中成长的民众的谙熟
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大是大非,没有大奸大恶,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刀光剑影。他只是侃侃而谈,把我们周围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牛七马八的平凡遭际深情地缕析。“白豆烀腊猪脚”“草帘子”“雷楔子”“提箩”等等词语,滇西北民众不会陌生。这种从泥土中侵染而来的亲切感,是他对这土地的深情回报。而每一个张弛有度的故事中,人们的每一句话的音言,每一个举手投足的仪态,无一不是自然天成的本性。有时我不禁质疑,是不是那个凤凰古城的大师突然言说起了滇西北往事与新传?
我们都没有故事,故事在民间。杨友泉先生的内心,充满了最本真的悲悯。所以,他以一种民间的态势,叙述着没有故事的故事,而农民,就是我们这个即将蜕化的农耕国度中化石般的故事中的主角。
世事皆为美。唯能承天地之气者,方为高尚。杨友泉先生是质朴的,隐藏于众生的羽翼之中,用心灵之高洁与文字之拙朴,与夏夜的虫唱蛙鸣一起弹奏属于泥土的圣歌。
最卑微的心灵,才足以让世人仰望。当浮华沉寂,杨友泉先生的小说,足以照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