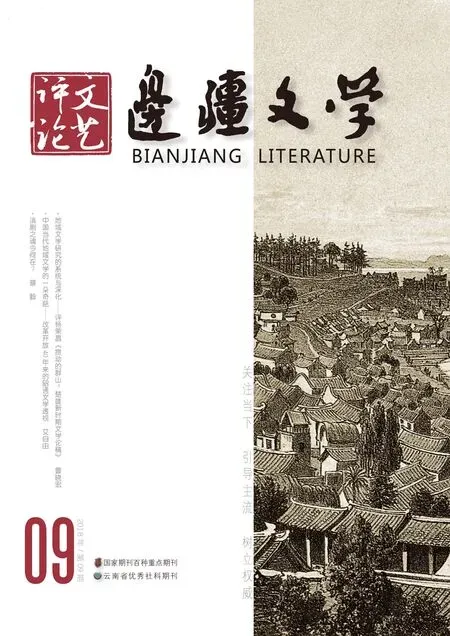直面乡土的困境与出路
——读罗家柱小说
杨荣昌
晋宁作家罗家柱是一名乡土守望者,多年来,他执着地书写着滇池岸边这片火热的土地,用文字精心营构艺术之塔,以小说形式探寻社会变迁带来的人性嬗变。其作品无论是故事取材还是内在的艺术精神,都与云南高原的气质相契合,传递出一种独特悠远的乡土气息。他的小说有着扎根基层的作家们普遍具有的优势与特色,共同体现的困境与不足,是分析乡土文学创作的有效范本。
罗家柱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多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主人公多生活于社会的底层,通过对一方水土剧变史和民众喜怒哀乐的呈现,展示乡土中国的现实境遇。短篇小说《河祭》把故事放在了一个落后的乡村里,叙述村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历程,为乡土中国的历史发展塑造出一个缩影。这个乡村是高度寓言化的存在,人们思想落后,不思进取,在通过正常劳动无法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村民想到了靠捕河鱼为生。主人公鲁树生由此竟荒废了农民世代为主的农业生产,整日沉迷于捕鱼之中,最后因捕鱼器漏电而被击身亡。从故事表面来看,杀鸡取卵的掠夺方式导致河鱼减少,切合了环保主题,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相呼应。但从内里来探究,鲁树生的死在乡民们看来是遭遇了水鬼,因为他做了对不起水下灵魂的事,遭到了生死报应。可见民间自有一套完整的善恶分明的伦理观,诸多正统理念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民间法则来规范。
《做仙姑那些日子》发表于《民族文学》,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叙述者是一名初中毕业女生,为生活所迫跟随姨妈去做仙姑,以装神弄鬼忽悠人来赚取生活费用。她的视角其实也是剧透的过程,隐秘的内幕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逐一展现,揭开了“仙姑”这类人物的真实面纱,她们以心理揣测干预现实世界,注重对诊断对象心理世界的探析。一名初中女生都能清晰看透的剧情,却屡屡哄骗了一大批位高权重或腰缠万贯者,可见当代人的心理痼疾已达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耻辱,需要进行灵魂救赎以摆脱困境,才导致神秘的巫文化有着丰厚的滋生土壤。从价值的建构来看,主人公对“仙姑”这一职业的反感和厌恶,到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开,标志了年轻一代可喜的价值追求。
著名学者陈思和曾提出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即民间文化形态,它产生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态,能够较为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自由自在是它的最基本审美风格,它的民主精神和封建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以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论视角来看罗家柱小说,可发现诸多游离于主流意识规范的鲜活的民间文化因子。作为彝族作家,他对本民族情感的把握极为深刻,这种民族意识又通过最具特点的民族文化形态来体现。在《山寨秘事》中,彝族的民俗文化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它集中于一部彝族古歌《聂苏歌诀》上,写出了这部象征民族文化之根的歌诀“萌发——失落——重新绽放光彩”的过程,通过当代人对歌诀的寻找,深度呈现了彝族人的精神活力。众所周知,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彝族民歌内容丰富、结构朴素、讲究押韵、旋律优美、感情粗犷,男声调雄浑高亢,女声调柔和细腻,从《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等四大创世史诗到《阿诗玛》《赛玻嫫》等民间叙事抒情长诗,都不难见出自古相沿的歌诗传统。彝族民间的传统曲调有的有固定的词,有的是临时即兴填词,男女青年在山歌的传唱应对中传递情愫,消解忧愁。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关于民族文化的继承、消化与呈现,是其表现的重点,这是一种心理意识的自觉反映,也往往构成与其他民族作家的鲜明区别所在。这篇小说中,《聂苏歌诀》就是彝族人审美情感的承载物,亦是一种深层心灵璞玉般的存在,居于小说的核心位置,牵动读者阅读的关注点。通过对它的寻找,串联起一条清晰的线索,勾勒了少数民族社会在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发展历程,背后是中国历史充满犹疑、挫折和奋进的巨大转型,内在精神却是彝族人对民歌独特的感情。民族文学的最高标准应是作家用娴熟的汉语表达本民族的思维、意识和情感,最终呈示作家的深层心理,这篇小说显示了民俗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作用。
《母亲溪》是作家的一篇新作,与当下社会发展的主潮紧密相连。久居山里的人们安土重迁,习惯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情愿配合政府组织的搬迁,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这喻示着当下乡村融入现代文明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整个时代的快速前行,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观念随之改变,物质环境的提升只有与精神思想的发展相匹配,才能实现乡村精神的质的飞跃。罗家柱是一名有责任担当和前瞻意识的作家,他深入扎根进人民中,捕捉来自民间的细节,有生活的质感,构成对当下乡土社会变迁的文学书写。尤其在脱贫攻坚等成为国家头号工程的当下,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已成为全民共识和当务之急。乡村振兴计划,又让占据中国极大比重的生活群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心,他们的前途与命运何去何从,关乎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质量。小说的可喜之处在于写出了青年的力量,传统乡村要走向现代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他们比老一辈更容易接触新思想,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打工的青年,都有责任改变故乡的面貌。
然而,作为一名长年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学写作者,罗家柱在倾情书写故乡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缺憾。这些艺术性的不足,能够引起我们对于小说艺术的必要反思。首先是逻辑不能失信。小说的艺术魅力靠细节彰显,细节的可信与精彩极其重要,要经得起时间和逻辑的推敲,细节失真会瓦解小说的可信度。《河祭》中的年代表述不合理,主人公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十八岁左右结婚(70年代中期),连续生了八个孩子,“隔年一胎”至少需要十五年,“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应该到90年代中期了,其时已经改革开放,甚至已经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不可能还有“村民不能养猪养鸡,不能种自留地”的情况,也不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其次是语言不能失趣。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容有丝毫矫饰,优秀的小说要贴着人物的性格书写,重塑一种鲜活的生命力。段落与情节的承接要自然,流畅,忌讳用大词、成语等,越是生活化的语言越有新鲜感。《河祭》中,村委会干部面对泼皮荞弟的耍赖用“理屈词穷”,并用一连串的“说服、教育、改变他”等表述,这些都不算好的小说语言。再次是价值不能失真。优秀的作品要给人以温暖和力量,需要树立正面的价值,在罗家柱的小说中,绝大多数写出人性的善意与温情,写出一种可以尊崇的价值观,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语言和情节都甚为精彩的《鸟为媒》,发表于重要刊物《民族文学》,尽管讽刺了官僚主义,可主人公终日以养鸟、遛鸟、斗鸟为生,把玩乐当作了生活的追求,并非可取的正面价值。指出这些缺憾,可以促使作者不断锤炼语言,在保持对乡土世界人物性格命运变迁的深度呈现与悲悯的同时,建立一种经得起推敲的情理逻辑,重塑一种可信的价值理念,使小说的艺术性建构达到一个更高的维度。
一名优秀的作家是这片土地的代言人和文化标杆,他以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书写,构成这片土地的精神。罗家柱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与时代发展的主潮紧密相连,深入掘进与建构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彰显出民族文化之根的现代活力。对乡土变迁的把脉和乡村困境的揭示,使他深度触摸到了社会的敏感神经,写出了一个年轻群体的价值追寻,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小说预示了一种可以信赖的生活方式,有效发挥了文学参与社会事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