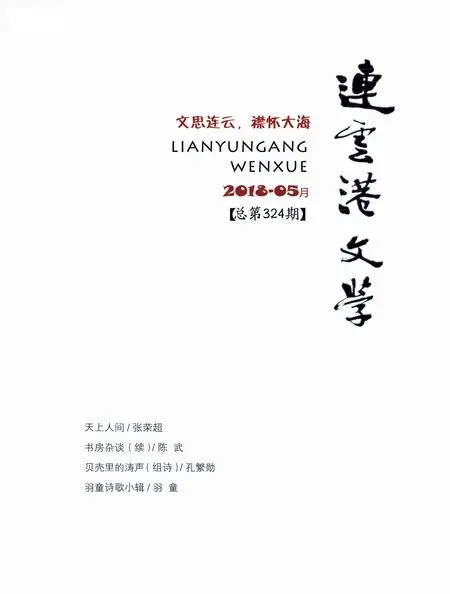书房杂谈(续)
陈武
签名本
近日收到一套珍贵的签名书,由王干、汪朗共同签名,还钤一枚汪曾祺的印章。汪曾祺先生的赠书印章我见过,不止一种,有大有小,有朱文有白文,“汪曾祺印”四字大都规规矩矩,另外还有一枚“人书俱老”的朱文篆字闲章。有时候只钤一枚,有时名章闲章同时钤印。汪先生已经逝世多年,在新出版的书上钤有一枚汪曾祺印章,这是怎么回事呢?待我慢慢说来。
2017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许多出版社都争相出版老人家的作品集。我朋友林苑中先生是个有经验的出版人,也策划了一套三卷本的“珍藏汪曾祺:情不知所起,一汪而深”的纪念文丛,分为三卷,分别是:《散落的珍珠——民间书画拾遗》(壹)《月夜赏汪文——妙文采撷赏析》(贰)《影像与足迹——照片里的年轮》(叁)。在第二卷《月夜赏汪文——妙文采撷赏析》里,还收我两篇拙文,《重读〈受戒〉》和《读〈八月骄阳〉》。丛书出版后,林苑中制作了少量毛边本,请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汪朗先生和丛书编者王干先生分别签名,并征得汪家同意,把汪曾祺先生生前用过的印章钤在书扉上,分赠给部分作者和书友。我的这套书,就是这样得来的。
关于签名本的源流和意义,爱书人都知道,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这里只简单介绍我珍藏的几种签名本,描述一下得书经过。
2007年深秋,我在北京大学听了一段时间的课,有一天上午,在教室隔壁的小会议里,看到有一个《日藏汉籍善本书目》的新书首发式,出席首发式者都是北大的名教授和文化界名人,从座席卡上,能看到任继愈、徐俊、白化文等文化名人。我觉得有机可乘,便逃课,在北大校园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任继愈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随笔集《竹影集》,利用会议间隙请他签了名。后来又后悔没有买白化文先生的书,虽然他也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墨迹,总归是遗憾。大约一周后,我便利用一个周六的上午,跑到北大南门外不远的一家中国书店的门市部里,一口气买了六七本白化文的著作,乘公交车来到颐和山庄白化老的家里,请他在我的书上签名。白化老的签名不拘形式,在《三生石上旧精魂》和《汉化佛教与佛寺》《人海栖迟》等书签上“陈武同志正讹”,落款是“白化文借花献佛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在《稽神录·括异志》《楹联丛话》等书上签“陈武同志惠存”和落款日期。这次登门拜访,还有一个重大收获便是,经白化老介绍,认识了他的师母、我国著名佛学家周绍良先生的夫人、海州大乡贤沈云沛的小女儿沈右兰女士,近百岁的沈右兰女士送我一本《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并在上面签了名。白化老在《人海栖迟》一书里,收有一篇《恭祝秋浦周先生并沈夫人米寿暨结缡七十载寿序》,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秋浦周先生暨德配东海沈夫人”,赞沈夫人的句子一段曰:“沈夫人画阃含章,名闺蕴采。内外同称圣善,子女仰望温慈。”文末曰:“时维乙酉桃月,修禊吉日良辰,受业白化文顶礼九拜谨叙。”1999年,老作家冯德英先生来连云港,我得知后,特地带着他的代表作“三花”,即《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等书,请他签名。苏州才子王稼句的签名有特色,有一次我带着他新出的《吴门烟花》《夜杭船上》《坊间艺影》请他签名,他分别称我为“先生”“兄”“方家”等。天津藏书家、学者罗文华先生的题签内容里,含有勉励的意思:“掬云捧月润笔淘书”,“掬云”是我的书斋名。著名评论家阎晶明先生很客气,所签都是“陈武吾兄指正”,着强调“吾”字,表明和受赠者的亲密关系。另一位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潇洒,一略的“陈武兄批评”,整齐划一。著名作家苏童的签名是“陈武兄指正”。这些文学大咖真是客气,其实我既不敢指正,也不敢批评。这是他们的谦虚,是美德。我所做的,只能是认真学习、领会。叶弥的签名别有情趣,在《红粉手册》和《去吧,变成紫色》二本书上,签“陈武先生看看”。毕飞宇先生在台湾版的《玉米》上签“送陈武兄”也挺朴素亲和的。二十多年前,刘元举先生曾签名送我一本《西部生命》,颇值得一说,记得是在他家的书房里喝茶闲谈,聊起最近的创作,他忽然想起来,要送我一本书,在书架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本《西部生命》,这是他一部重要的散文集,199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把书拿在手里翻翻,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这本原是送给别人的。我说没事,重签。他也哈哈一乐,在环衬上签了字:
真正有缘的人才最应该得到赠书。
陈武友留念
一九九七年夏天
于沈阳
刘元举
在签名的前方,还盖有一方印章。而这本书的扉页上,原有的“请大中先生教正”和签名时间“一九九六年春”的字样还保留。这种特别的签名本,图书收藏界据说有新名词儿,叫“改签本”。
以上是说作者赠送的签名本。在坊间,我还收有不少作者签给别人的签名本,这大多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书,个别是从网上竞价买来的。比如我在竞价购得一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叶圣陶年谱》,就是编著者、叶圣陶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先生赠给“启华”的,所签为:“启华尊兄指正商金林寄呈1987.5.15”。启华者,不知谁也,也不知道这本书怎么会流到旧书市场的。有一本1979年出版的《连云港文艺》第四期上,有丁义珍的签名,内容为“赠‘东海文艺’编辑部苗运勤同志存阅连云港博物馆丁义珍”,日期是1980年3月9日。苗运勤的“勤”,应为“琴”。这本杂志的头条,是丁义珍的一篇民间故事,题目叫《吴承恩上云台》。我在购买这本旧杂志时,已经知道苗、丁二位先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
签名本而外,还有一种“签章本”,其实是签名本的一种外延。签章本大多没有上款,也没有日期,是事先钤好数本,参加某种活动时拿出来随手赠送朋友的。我就藏有白化文老先生的一册签章本《敦煌学与佛教杂稿》,中国华局出版,蓝面精装,程毅中提签。所钤印章有特色,为阴阳混合,“白化文”三字为隶变阴字,敦厚稳重;“持赠”二字为小篆阳字,线条古拙,潇洒飘逸。另外还有秋禾赠送的《中国藏书大辞典》《书评概论》等书,也是有特色的签章本,只盖一枚“徐雁持赚”的篆书大印。与签章本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没有上款的签名本,只签一个作者姓名,现在也受到爱书人的喜爱了。还有一种签名不是作者所签的,而是赠书者作为礼品赠送给朋友的,这种书大多是中国古典名著或世界名著,也有字典辞书什么的。比较珍贵的签名本是限量毛边书,每本带有序号,一般序号排到五十,多了就意义不大了。
近年来,网上卖旧书风行,有专门拍卖签名本的,有的是个人,有的是机构。各种形式的签名本、签章本都有,同一种书,同一个品相,有签名、签章和无签名、签章的价格大相径庭,特别是名家签名,又特别是名家签给名家的,更是价格翻倍。比如一册普通简装本的《山湖处处》,1985年出版的小32开,因为有毛笔签名,夏木书房的起拍价是三百六十元。不是签名本的,在旧书市场十几二十几块钱就能淘到。文友李建新先生喜欢淘书,似乎尤爱签名本,又尤其喜欢汪曾祺、孙犁等文学前辈,他在网上就淘得多部汪曾祺的签名本,价格不菲。签名本成了增值的一大由头,也是签名者和获赠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我的淘书,多半是为了读和用。读书的功能就不用多说了,目的不一样,读的书也不一样,比如我是写小说的,兼写文化类的随笔、杂感,遇到我喜欢的小说和文史方面的书籍就多买点,签名本也不去刻意求之。但因为这个圈子不大,许多同行都成了熟人朋友,有的还尊为前辈师长,他们每每出版著作,我会买一本请其签名,他们也会签名送我。记得我到大学者程毅中家请老先生为《白化文文集》题写书名,为了便于拉近关系(当然也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特地在网上淘了几本程老的著作,又跑到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他的近作五六种。待到他家四面都是书的客厅里坐下后,便先拿出他的大著,老先生大为惊讶,谈话气氛遂宽松了起来,他不仅在我携带的书上题了签,还愉快地答应写序。不久之后,我就收到程老写来的序言了。
毛边本
我虽没有刻意搜集毛边书,但坊间也有所收藏。早期只从鲁迅、周作人、唐弢、黄裳等人的文章中略知一二,也在姜德民的书中见过其尊容。真正收到毛边书,是得秋禾(徐雁)先生所赠,时间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了,这便是由秋禾编辑整理的《雍庐书话》,书的作者梁永,本名钟明,是古城西安的一位爱书家,他的本职工作是建筑工程学的教授,喜欢新文学收藏和版本研究,常有这方面的书话文章发表,梁先生生前将书稿托交一家出版社,因种种原因,该书未曾面世便溘然长逝了。秋禾在编辑《读书大辞典》时,得知这一讯息后,便倾力促成该书在他供职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写了长文《编辑手记》附后。首印只1500册,还留有少量毛边书赠送同好。我这本的编号是“011”,书扉上有“陈武先生雅存”的题签,并钤有一枚“秋禾持赠”的篆印。但是按照毛边书的制作要点,即“地齐天毛”的标准,这本《雍庐书话》属于毛边书中的错本,“天齐地毛”了。如此说来,按收藏的惯例,这册“错边”毛边书,更是珍贵了。
沈文冲先生送我的《毛边书情调》也是一册毛边书,还另赠一把刀,刀是红木的,专门用来裁书。该书是一本关于毛边书的文章汇编,收有鲁迅的《毛边装订及其他》、周作人的《〈毛边装订的理由〉按语》、唐弢的《“毛边本”与“社会贤达”》《“拙之美”——漫谈毛边书之类》、舒芜的《也说毛边书》等。后来,我又陆续收到罗文华、王稼句、赵玫、自枚等人赠送的毛边书,罗文华所赠的《与时光同醉》的毛边编号是“之陆拾捌”。徐雁和自枚还把杂志做成毛边本,如徐雁实际负责的《今日阅读》试刊号就是毛边本,书内首页钤有“徐雁赠书”的印章。自枚也把自己担任主编的《日记杂志》第四十七卷做成了毛边书。
关于毛边书的把玩和阅读,各人体会不同,王稼句在《夜航船·毛边书谈琐》里说:“在我想来,只在耐读的小书,最适宜毛边,特别是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又要用刀裁一帖,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好像说书人卖的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将你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还有裁约纸,最好用竹子或红木做的刀,一刀裁下去,纸边并不光洁,略有一点毛茸茸的,仿佛素面朝天的女子,比起画眉抹粉后的样子,更有一种自然朴素之美。尤其裁纸的过程,眼里看着,手里动着,还有那咝咝的声音,你仿佛就与书融合在一起了,似乎只有在你的劳作下,这本书才有了它的意义。”我的阅读,没有王稼句这么用心,使用的刀也是一枚废弃的银行卡,有时随手拿一张名片充刀,总之能把书页裁开就行。
白化文先生有一篇短文,曰《侍坐话“毛边”》,讲述他年轻的时候,听他母亲和一位图书馆老馆员关于毛边书的议论,还讲了一个段子:
丘吉尔送一部自己的著作给一位贵夫人,这位夫人在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的开罗有一幢别墅,欧战时,夫人搬到别处,别墅空着,丘吉尔到开罗开会,就住在那幢别墅里。一天,丘吉尔在那位夫人的书房里看到自己送她的那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看,还没裁开呢!丘吉尔动了真气,在扉页上写了一段批评那位夫人的话,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意,也不读书。言外之意,此书“明珠暗投”矣!……战后夫人归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留言,大喜,立即送伦敦拍卖行,以高出书价许多倍的价格拍出去了。丘吉尔闻之,更加恼怒,想写信与那位夫人绝交。有人提醒,若写信,可能接着还得拍卖。于是截止。
这个故事说明,送书,也是要看对象的,即便是普通开本的书,也不能随便乱送,又何况特制的毛边书呢。
我后来接触并从事图书出版行业,屡次想把自己策划出版的书籍做少量毛边本,用以赠送同好,可每次都因各种因素未能如愿,真是心有不甘。
碑 帖
并不是因为要练书法才收藏碑帖。碑帖也可当作闲书来消遣,比如一册《曹娥碑》,无事时翻翻,看看帖子,领会一下字体结构和用笔,再想想关于曹娥和《曹娥碑》的诸多轶事,心情会大不一样,仿佛读了一本大著。一册《宣示表》,一册《洛神赋十三行》,一册《虞恭公温彦博碑》,都能让人产生许多怪异且有趣的联想。就说书写《虞恭公温彦博碑》的欧阳询吧,这位书家钻研书法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传说有一次外出,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特别好,细看,原来是大书法家索靖所写,便索性在石碑旁边打了地铺,睡了下来,足足看了三天,才起程赶路。朋友陈立新,在多年前,曾经跑遍云台山,拓了不少山上历朝的石刻,唐、宋、明、清的都有,承他送我几贴,我也是经常拿出来把玩欣赏。帖子看多了,便也想写点小文,有一天买到一本《王羲之小楷字帖》,制作颇下一番功夫,我便写成一篇小文,曰《黄松涛和〈王羲之小楷字帖〉》,原文抄录如下:
市面上关于王羲之的法帖多如牛毛,毫不稀奇,翻印水平也有精有劣,概不一一说之。我手头的这本只有二十四页的《王羲之小楷字帖》(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是2003年春,在华联边的冷摊上购得的。喜欢这一本小幅书贴,倒不是喜欢书法,相反,我对所谓书艺,一向的不以为然,古人写字,不过是用来作文用的,是必备的一种技能,就算中国文联成立之初,也没有这样的协会。成为一种专门艺术,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是这本小书值得雅玩的地方,是和我喜欢的一个文士有点关联,这就是“凤栖村民”黄松涛先生。黄氏出生于1900年,活了一百多岁,直到2002年才驾鹤西去。他原名华,曾用名颂陶、木夫,笔名柝翁,别署凤栖村民,湖北汉阳县人,绘画、书法、音乐、文史典故皆精。生前曾为武汉文史馆馆员。这本小书的封面画、题签和封底篆刻均出自黄松老之手。
黄松涛先生世代耕读,诗书传家,沈必晟有他的小传,称他“幼从伯父雨亭公学诗文书画及古琴演奏,及长从上海熊松泉先生习画,又从南昌涂尧学篆刻,壮岁在武汉执教鬻艺。常与杭州钱越荪、临川黄鸿图、太平盛了庵、长沙唐醉石相友善,与邓少峰先生居闾里,探讨三代两汉六朝金石文字及历代名画,获益良多。”他画山水、花鸟、走兽等,“用笔古拙朴厚,章法深秀典雅,设色奇丽秀润,有朴茂浑融、温润古健之意趣。”他亦作瓜蔬果鱼,也是水墨淋漓、清气可掬。《王羲之小楷字帖》的封面画就是他八十四岁那年创作的,是他为这本小书专门的量身定做之作,取意晋人王羲之的《黄庭经》的典故——这画里的故事是我们熟悉的——晋代大文士王羲之因为爱鹅,被山阴道士敲了竹杠子,写了一部《黄庭经》,换了一对大白鹅。因为这个典故,《黄庭经》又称《换鹅帖》。写字的人都知道,《换鹅帖》可是历代楷书的范本啊。李白在某年到绍兴,游了古镜湖,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专门提到了这个典故,诗曰:“镜湖流水映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本书帖就收了《黄庭经》(另外还收了《乐毅论》,并附了王献之的《洛神赋》)。画面是池塘边草地上的三只小憩的大肥鹅,有卧息,有引颈抖翅,特别是边上的那只,可能是听到草丛里有蛐蛐声吧,正转首窥探,虽然它们都是闲散状,神态竟是如此的各不相同,真是到了化境啊。
这本书帖的题签也出自黄松涛之手。黄氏书法,“初从颜楷《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入手,后遵伯父雨亭先生命,临习王羲之《怀仁圣教》及孙过庭《书谱》,在和清道人弟子黄鸿图先生的交往中,又对碑学极为用功,曾对《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崔敬邕》、《孟敬训》等临习殆遍。”他的题签字体用的是隶变,用方笔、铺毫,转折处喜翻笔挫锋,看他的字,端直快厚,奇古凝重,深秀雄浑,味醇意隽,颇富金石之神韵。
封底的“武汉市古籍书店”的篆印也是黄松涛的手治,该印于平实中见气势,于精细处见生动,平实而不呆滞,生动没有怪妄之陋。
另据沈必晟先生所撰黄氏小传,说他对音乐亦是精通,“雅擅古琴演奏,曾师从方眉、谢耘僧、徐瑞芝诸先生,在1956年中央民研所全国琴人调查及录音汇编时,曾录制有平沙、醉渔、渔樵、梧叶诸曲,先生亦精通梅花、阳关、高山、忆故人、欧鹭、孤猿词、普安、石上流泉、樵歌、捣衣、风雷引等诸曲目,为世人称赏。”
一本薄薄只有二十来页的小书,没有一字前言后记,却又如此的富有情趣,确是难得。
这篇短文作为《读艺小札》的一节,收在《尚书有味》(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里。有一次我在朋友王干先生的办公室谈事,看到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书法条幅挂在墙上,有的字体很眼熟,一想便想到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觉得他一定练过此帖。后来请他为《中国好小说》题签,闲聊起了书法,果然如此。他还说到苏老夫子的字虽然“迅疾而稳健”,但气度不足,而他更注重“疏密有度”、“转换多变”、“顺手断联”,且能“隔行通气”。待我读到他的散文集《隔行通气》时,我知道了,王先生是把书法当成文章来经营打造的。
书法家平时临帖固然是毕生功课,但我倒是觉得,把碑帖当闲书来读,该更为重要。君不见,哪位书法家箧中没有数本法帖呢?他们不一定完全是用来临写的,书到一定的境界,读帖也是一件要功力的事,有时比临摹更为重要。有一次我翻看《翁同龢归籍清单》,在老先生整理的数箱带回原籍的物品中,大多是书籍、画册、书札、长卷、册页、碑帖和书房用品,我粗率统计一下,仅各种拓本、书谱,就有百余种,如《宋拓娄寿碑》《宋拓劝进表》《宋拓群玉堂帖》《宋拓茅山碑》《宋拓大观残本》《宋拓晋唐小楷》《宋拓道因碑》《宋拓玉枕兰亭卷》《董香光十三行小楷册》《宋拓宝晋斋米帖》《宋拓修类司帖》《乙瑛碑》《国山碑》《明拓宋广平碑》等等,这些都是老先生倾大半生心血搜罗的,也浸透在他的学问中。
而读碑、抄碑,进而对碑帖产生兴味,做起了学问,这又便是鲁迅当年的路径。鲁迅抄碑的事,除了他在《呐喊》的序言里已约略说到而外,较详细的是周作人的回忆文章,仅《鲁迅的故家》里就有三篇,《抄碑的房屋》《抄碑的目的》《抄碑的方法》。抄碑的房屋是S会馆,即绍兴会馆,目的呢?《抄碑的目的》有详细说明,是为了“逃避耳目”,因为“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到处活动,“由他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也就多少可以放心”。鲁迅“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得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袁世凯死后,鲁迅原本不用再抄了。可他还是继续抄,前后有四五年时间,竟然抄出了兴趣来,周作人在《抄碑的方法》里说,抄着抄着,想着要校勘这些碑文了。因为“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作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存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鲁迅的“标准的著作”没有写成,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也许并不可惜,因为在钱玄同的游说下,他还是操笔写出了此后影响中国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
鲁迅由读碑、抄碑,到当成学问来研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我的读碑帖,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更没有要拿它做成学问,如前所述,只是当闲书来读的。有一段时间我读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的小说《人生拼图版》,莫名其妙会想中国的汉唐碑拓,把汉唐碑拓拼接起来,不就是一部中国史吗,如果任意拼贴,更是包罗万象的中国史了。
花草·清供
周瘦鹃先生在《花前琐记》里有一篇《插花》,开头便说:“好花生在树上,只可远赏,而供之案头,便可近玩。”一个“玩”字,道出了心境和情趣。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喜欢在书房里弄些花儿草儿,一方面作为摆设,可以丰富书房气氛,增加书房色彩,净化书房空气,让书房像花草一样生长;另一方面,服侍这些花儿草儿,在工作疲倦的时候,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施施肥,可以打打岔,所谓放松情绪、缓冲神经是也。
吊兰最适合书房,浇水施肥都不用讲究,随便给它点水,就能洋洋洒洒地展示青葱和翠绿。旱伞草也喜水,株形美观,叶形别致,和兰草一样不在乎环境。比较而言,棕竹、文竹就要娇气一些了,特别是文竹,你就是精心去服侍,也会不小心把它给得罪而耍点小脾气。在我的书房里,我喜欢的,要数紫色的落新妇花,其根茎粗壮,习性强健而耐寒,姿态直立而婆娑,小花繁密雅致,特别耐看。但是,这些花草都不及我对牵牛花的喜爱。
牵牛花在乡间是常见的野花,小树、芦苇、笆帐上常常缥满了喇叭形的花朵,早上开得花喷喷的,过了中午,它就蔫了。它的花只开半天,我们都是知道的。女孩子们喜欢把喇叭花一朵一朵揪下来,红的蓝的白的紫的,串在一根细长的柳条上,做一个花环,套在脖子上,可以一直“臭美”地走到学校。
牵牛花是蔓生草本,茎缠绕,可达三四米长。叶互生,三裂,有长柄,两面有倒生短毛。花腋生,开一朵,或者两朵三朵。有趣的是,开白色和淡红色的花,种子多为淡黄色,叫白丑;开蓝色和紫色花的,种子多为黑色,叫黑丑。这就是牵牛花的别名又叫黑白丑的原因吧。
我书房阳台上的这盆牵牛花,是我从山上采来的种子自己种的。极普通的品种,开淡蓝色花朵,秧子极其茂盛,岔了许多条细藤,我插的两根细竹竿上,都被密密的爬满了,开花也一点不偷懒,一连两三个月,基本上天天都有新花。
说起来,种牵牛花,还是受叶圣陶老先生的影响。
叶圣老写过一篇《牵牛花》,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北斗》杂志的创刊号上,开头就说:“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叶老是在瓦盆里种牵牛花的,而且种十来盆。叶老很有深情地说:“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四十多年后,在叶圣陶和俞平伯通信里(见《暮年上娱》),有关于牵牛花的内容涉及数十通,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叶圣陶至俞平伯信中说:“今日往访伯祥,知近日又到彼处晤叙。谈及种花草,忽忆前程告知,某友处可得出自梅氏牵牛花种子。未识能为致两三颗否?如可致,希纳于信封中惠我。”从这封信开始,至十一月七日,两位老人关于牵牛花种子及栽、种等事宜共通信达十五次之多。
叶老信中所说的“梅氏”,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
梅先生也喜欢牵牛花,还和朋友们组成一个小团体,见面时,三句话离不开牵牛花,互相间还交流种植经验,互换花种。据说,梅先生养牵牛花,是因为牵牛花在大清早开花,他常常拿起床和牵牛花比赛看谁更早。有一次他在俯身闻花时被朋友看见,说他像是在做“卧鱼”的身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梅氏从中受到启发,便仔细揣摩实践,终于在《贵妃醉酒》中使贵妃赏花的“卧鱼”身段更加完美、生动、传神。
不仅是今人喜欢牵牛花,古人也多有诗咏,宋人秦少游就有一首《牵牛花》,可以说极为生动,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演绎得朦胧缠绵,情韵无限。诗云:“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栏杆。仙衣染得天边绿,乞与人间向晓看。”
关于牵牛花的诗文,可以举出一大堆来,但是都不及我书房阳台上的牵牛花开得真实,在花期期间,我每天晨起,都要看看它开了几朵。有一次,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因为赶写一篇文章,在书灯明亮的光影里面对电脑沉思,心里突然想起牵牛花,跑过去看看夜里是不是也在开花,我看到,那几个花骨朵,紧紧地闭合着,它还没开。回到书桌前继续工作,心里便多了牵挂,到了凌晨四点半,天色已经微亮,我再到阳台上看时,惊喜地看到,那几个骨朵,居然全开了!
正如周瘦鹃先生所说,花草也可做瓶供。瓶供的瓶子不一定要多么的好,普通的杯子也可以。我就曾在书房的桌子上,用一个稍微有点造型的罐头瓶,瓶里灌一半清水,剪几枝盆栽里的枝叶,蓝花菜、绿萝、薄荷、吊兰等,稍作整理,插于一瓶,青青绿绿的,倒也还好看。有趣的是,这几种枝叶,都能在水里生根,自行生长,这瓶生机勃勃的绿,便可四季长供了。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里,有这样一段话:“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鲁迅书房里的“水横枝”(以栀子为好),就可看作是清供了。有一盆清供盆景陪伴,鲁迅先生“编编旧稿”才不至于寂寞,并可以“驱除炎热的”。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先生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他制的清供盆景,有的清雅可人,有的调皮可爱,别有特色。受他的影响,我在我的掬云居里也做了一盆,造型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配以相宜的几枝竹叶和桃枝,竹枝青绿,桃花艳丽,虽然太过简陋,居然也不俗。后来又换成几枝茉莉和两三朵白牡丹,高低错落,清香沁人。瓶供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更换,枯萎了可以换,看腻了也可以换。冬天,我的瓶供里供过蜡梅;早春,供过迎春花;初夏,供过海棠;盛夏,供过荷花,初秋、深秋、残秋,直至寒冬,都可以有做清供的花枝,虽然有些花花草草,都有象征意义的,但也不可太强求,以舒心好看为上。
最可记一笔的,是我在今年冬制作的一束干花。在我供职的办公室楼外,有一个花圃,栽种好几个品种的月季,从四月开始,每月都开,花朵大,花色艳,特别养眼。但是,开到十一月中旬里,突然而至的寒流,一夜间冻死了。那些正开的花,或花骨朵儿,还有绿叶,便保持前一日的姿态静止在那儿了,再被太阳晒了几天,成了干花,如烘焙一般,依然不减原先的美丽。我便拿了剪刀,剪了几枝,长长短短插在一个白釉带蓝色碎花的广口小瓷杯里,放在书桌上,比鲜切花更有味儿,而且一个多月保持她的色彩,花光鲜艳,如在枝头一样。
书 灯
唔呀声里漏声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
这是元人谢宗可的《书灯》诗,诗中的精髓,早已经成为读书人清贫自持、荣辱不惊的典范,并为读书人所乐诵,书灯也成为读书人常相厮守不可或缺的用具。
老实讲,书灯的实用价值,远没有它的名称让人容易浮想联翩。书和灯,真是有着不可分离的情感,传递了多少莘莘学子求学问道的艰辛历程。还有什么灯比书灯更明更亮的呢?它照耀的,不仅仅是读书人普通的读书生活,同时也照耀着读书人前边的路,并牵引着读书人一直顺着书灯的光芒走下去,直到走进知识的圣殿。
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我初中毕业的一九七九年还没有通电,在故家的老屋里,我就是靠着一盏煤油灯来完成最初的文学阅读,萌芽了对文学的迷恋,获取了走进知识殿堂的钥匙。想想当年,冷屋秋寒,孤灯黄卷,一个少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贪婪地阅读一本本文学名著,并被作品里的人物深深地感动。灯,成了我的“伴侣”,那是我自制的灯,一个蓝墨水瓶,一枚铜钱,一根灯芯,半瓶煤油,就在我的鼻子底下。灯火很小,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煤油味儿,说来奇怪,我喜欢这种气味,它是煤油经过燃烧而发出的,刺激,怪异,让鼻孔有些痒,心灵反而更加安静,很适合阅读。那一本本卷边掉页的书,一行行熟悉的方块字,在昏黄的光影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样的苦读中,完成了我人生最初的启蒙。每当凌晨来临,我的鼻孔里都会被煤油灯熏黑,用手一抹,手指头都变得黑油油的了。其实在此之前,我有一盏很“高级”的灯,叫罩灯,有漂亮的玻璃灯罩,灯芯还可以根据需要由一个小齿轮调大调小,灯光也便忽明忽暗。隔一两天,我就会把灯罩擦擦,让它始终保持洁净。但是,好景不长,被一只调皮的猫碰到地上,连同灯罩一起,全摔坏了,煤油还淌了一地。为了防止猫再搞“破坏”,我用泥巴,给我自制的煤油灯做了个底座,从此就很稳了。我这盏灯虽然丑陋些,却很实用。缺点是,灯芯直接从铜钱眼里穿出来,容易结灯屎(灯花),影响发光,豆大点的灯火还因此而易歪到一边。每天晚上,我在点亮它的时候,想起我本家的一个年老的长辈,他手巧,会柳编,也会扎纸,还会木雕,他家有一盏自制的煤油灯,灯芯的构造挺“洋气”,也是铜钱做盖子,不同的是,它是三四枚铜钱,厚厚的,叠在一起,关键是,在铜钱的眼子上,装一个自行车的气门芯,铜的,棉绳的煤芯从气门芯中穿过,灯头就不结灯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眼红他家这盏灯。想着这盏灯会省油,亮度会更大,就由不得心向往之,就会想起我曾在父亲工作的废品收购站里看到过的一盏铜灯。那盏灯太漂亮了。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件工艺品,全身都是铜的,造型别致,灯肚子上还刻着花纹,只要穿上灯绳就可以用了。我把它玩了好几天,真是爱不释手。可我父亲早早就关照我说,这是公家的,玩玩就要放回去。直到很多年后,我在济南的山东博物馆里,欣赏到多盏馆藏的古灯,计有北朝的瓷灯,还有汉代的青铜舟形灯和青铜雁足灯等,它们都特别贵重,可以说一盏灯,能敌得过一座城。但感觉还是没有我小时候在父亲的废品收购站看到的灯漂亮、珍贵,雕花的铜灯可能年代没有博物馆里的古灯那么久远,但造型和工艺却是古灯不能相比的。
“三朝元老谁伴我,一盏书灯六十年。”我的煤油书灯没有这么长久,大约两年后吧(约在1981年春),村里就通上了电,我有了有别于古人和土造的书灯。这是一盏长檠可以随意弯曲的台灯,灯头是螺口的,二十瓦,亮度是煤油灯的数倍。不消说现代化的书灯给我带来的兴奋,也不消说在这盏书灯下我读书用功的无数个漫漫长夜。非常幸运的是,1987年入进新浦以后,这盏书灯也被我带在身边,跟着我搬了多次家,直到1997年,我搬进新居后才有新的书灯取代了它,那是一盏造型别致而新颖的书灯,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有足够的亮度,灯光舒适,不会使眼睛感觉不适应。但是,不久之后,我又换了新的书灯,新书灯的好处是,灯头可以调节,方便将灯光照向需要的地方,由于是由多块透明板组合在同一根轴上,使得这盏书灯类似于书本的形状,而且各块透明板可以转动,位置可以互换,使得书灯可以变化不同的造型,在获得灯光最佳效果的同时,也可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装饰作用。2017年年末,再次搬家。这次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更好的改善,新居的书灯,又换了花样,是一盏纯白的台灯,造型特别简洁,方便自由移动,像手机一样可以充电,也可以接电源,开关是触摸式的,亮度可以自由控制,像个魔方一样,触摸亮了以后,如果长按,亮度会逐渐变强,离手后再长按,又逐渐减弱,特别神奇,我有时读书或写作累了的时候,会玩玩它,让它更亮些,或更暗些。不过这盏灯不是我一人独享了,因为我经常在外,加上书灯移动方便,巴乔常会拿到他的房间使用。
也许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是有些怀旧吧,无论书灯如何出新,如何换代,最不能忘记的,还是故家老屋的那盏煤油灯。那是我自制的书灯。想起它的时候,书灯便在我心中点亮,在它的照耀下,许多陈年的往事会涌上心头,我的煤油灯,我在乡间看过的别家的煤油灯,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小时候在舅奶家看到的那盏怪异的灯,它在舅老太太(我母亲的祖母)的房屋里,那是一间泥墙的东屋,墙很矮,门也矮,大人进屋都要弓身曲背才可。可能是为了增加屋里的高度吧,屋里比屋外要矮一尺多。舅老太太的屋里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我一般不去。有一次,舅老太太喊我去吃东西,我便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盏灯,材料仿佛是瓦当(也可能是土陶),一个碗状的容器,碗盏边有个长臂,长臂上有个眼,可挂在墙上的橛丁上。碗盏壁靠长臂处,有个洞孔,灯芯就是从这个洞孔穿上去的。碗盏里有半盏液体,不知是什么油,在那时,我就仿佛觉得不是煤油。后来读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有一篇《灯火》,说到的一盏灯,似乎有些相像:“祖母房间里在辛丑年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这灯有好几种,顶普通的是用黄铜所制,主要部分是椅子背似的东西,头部宽阔,镂空凿花,稍下突出一个铜圈,上搁灯盏,底部是圆的铜盘,高可寸许,中置陶碗,承接灯盏下的滴油,以及灯花余烬等。”余生已晚,这种老式的灯盏自然是没有见过的。而我舅老太太屋里的灯也不完全是周作人所描述的样子。只能说,过去的灯,就仿佛如今的台灯一样,有着各种变化的。
我不知道以后的书灯还会造出什么样的花样来,但我知道书灯将会一直陪伴着我,我不奢求写出日臻其皇的华章,只要书灯不灭,我依然倾心相陪。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处何方,它都是我心中的明灯,它的亮度将超过任何现代化的灯盏,一直照亮并指引我奔走在问学的山道上。
笔 筒
笔筒的功能无须赘言了。这里只谈谈我书房里的几个笔筒。
一个是竹木结构的。这个笔筒有了一些年代,据我粗浅的知识,断定它是晚清或民初的东西,上沿口是鸡翅木镶嵌。可喜的是,这是一块整体的鸡翅木镂空制成的,四角没有接口。下底也是整体的鸡翅木,且有四个连体足。四个方面上,雕有春夏天秋冬的图案,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四条屏。该笔筒无款识,但从“笔墨即人”这一不变的理论推测,雕刻师非庸人所为,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也不难发现,该雕工手法娴熟,布局清细,胸有大气象,使笔筒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和教化意义。“春”面上,可称“郊外踏青图”,主体画面是一座拱形石桥,一老者立于桥中央欣赏河景和两岸桃花,他双手背后,目眺远方,全神贯注,或许远处的河面上,正有舟楫赶来,也或许被远处的河柳春燕所吸引。在他身边,两个顽童正跑步过桥,动感十足。在河对岸,辽阔的原野上,桃花草亭,假山草青。有两组人物,一是祖孙二人,沿着花丛小径,向远方漫步;一是一学者和两个书童在煮茶,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煮茶图”,在他们身边,是只露出一根柱子和一角草顶的草亭,草亭里很可能有人在抚琴,抑或有人在吟诗。整体画面,有轻有缓,有疾有徐,让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夏”面更是繁杂,应该撷取的是园林的一角,主体画面是一片湖泊的近景和远景,近景是假山、斜伸出来的绿树、湖岸假山上的绿草和湖中的荷,有的荷花已经盛开,有的呈花骨朵状。远景也是以人物为主,一条长廊前的假山前、古树下,有二人在对弈,有一个茶童正在侍茶。在假山上下,有几个孩子在玩耍。“秋”面到了远郊山野,远景是层峦叠嶂的高山,主打近景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寺庙前的河埠头,正驶来一条香船,有人在撑住船,有人走到了船梢头,有人已经行走在了码头的石阶上。山门近在眼前,山门前的石桥静静地横跨河面,是夜畔钟声到客船了吗?“冬”面也是安静的,江岸上山体陡峭,有一条蜿蜒的石阶隐藏在山石岩体间,直通建筑在云端的房舍,那是寺庙呢,还是书院?一片祥云环绕在建筑四周。有数株寒梅,开放在江亭和山崖上。近景的江面上,一条孤舟,一个老者,独坐船梢,正在放竿垂钓。画面取“独钓寒江”之意。这工笔“四条屏”,每幅上都有人物,且主题鲜明,造型考究,将画意和与雕刻技艺融会贯通,把城里的园林和城外的风光尽情描绘,用粗放写意和工笔精描之法,体现了灵秀多姿的园林风景和田园风貌,把“云水空蒙”、“剩山残水”的意境和情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真是非大家莫办。
另一个笔筒的材质是红瓷。和笔筒配套的,还有一个烟灰缸和一个茶杯。这套红瓷,是爱人的朋友送我们家的,她老家在湖南醴陵,十多年前,她回娘家探亲,回来时给我们送来了这套瓷器。百度一下,知道“中国红瓷是湖南醴陵特产,醴陵红瓷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在四大发明出现以前,它就已经传遍世界。”又说中国红瓷一时成为爱好者的雅玩,“成了各国收藏家刻意追求的宝贝。一直以来,中华瓷器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却单单缺了大红瓷器,这是因为大红釉料烧制艰难,成本极高,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历来为皇家贵族所珍藏。”看来,我要好好珍惜这套红瓷了。单说这个笔筒,直径约十五厘米,绘“五虎献福”的图案。朋友选此图案,可能是因为和我的属相有关。
我曾在山东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笔筒,展出名叫“竹雕竹林七贤笔筒”,说明文字是“画面设计独到,有静有动,相互呼应,是明末清初竹雕笔筒中的精品”。正是在这次参观后,我开始留意各种笔筒。南京博物院藏有“朱松邻松鹤纹竹笔筒”。据考证,朱氏为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记载笔筒较多的文献大多在明代。如《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贪官严嵩(1480—1567)的家产清单上,就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都是好东西。文震亨的《长物志》,记有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中,也有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震亨和屠隆都是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写文章时,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翻看明代中晚期的绘画(还有小说中的插图),笔筒也多有表现,如仇英的《桐荫昼静图》,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万历年间的刻本《状元图考》“胡广”的插图等,笔筒成了文房四宝之外的重要辅助用品。晚清时,常熟两代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回乡,在“回乡清单”上,多次记有笔筒,如“小笔筒(一个)”、“瓷笔筒(一)(蓝)”、“竹笔筒(一个)”、“大圆木笔筒(一个)”,老人家的这些笔筒,也许并无特殊之处,因是自己行用的物品,也打包装箱运回家了。
如果不事收藏,笔筒也没必要讲究,凡能插笔的容器都可做笔筒。我有一个做土陶的朋友,送一个自己用土窑烧制的笔筒给我,另有一个写诗的朋友去井冈山旅行,回来时给我带了一个简易竹制笔筒,也用了十几年了。这两件东西至今还在我的书房里。更值得一说的是,我把云雾茶的茶叶罐当成了笔筒,概因为这个茶叶罐形制特别——干脆就是仿笔筒制作的,材质是青花瓷,造型也不差,青花釉色彩纯正,图案精细,底部有“顺佳”款。如果去掉“云雾茶”和关于云雾茶的文字简介,说是一个笔筒也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