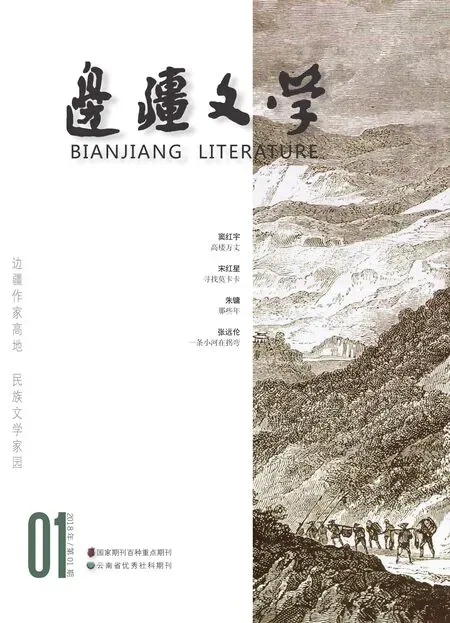城市的迷茫(外一篇)
夜暮降临,我习惯驻足观望五华山脚下熙熙攘攘行人。有些行色匆匆,有些漫无目的,有些叼着烟卷或剔着牙,遛狗的、蹲在路边刷微信的,也有戴着红袖套的志愿者。走在流水般涌来的人群中,我试图寻找熟悉的影子。其实,对我而言,路边上刷着石灰的法桐树,也是我的熟人,在黄昏,它们总像一些孤独的眺望者。谁能说清它们种植于哪个年代,如果街道和街道上的车人是流水,它们才是岸边观水的人。或许它们也已苍老到了记不起陈年的旧事,苍老到了树根已不能独自站立,而需要用铁架子支撑着的地步,苍老到了患了失忆症——它们落地生根时记忆中的这座城市与现在这个样子已天壤之别。只有昏黄的路灯射出怜悯的光,打在它们皲裂的树皮上,柔弱的光线映射出斑驳陆离的影子,让过往的行人也感到迷离。或许,只有用锋利的锯齿才能清数它们的年纪。
事实上,它们被锋利的锯齿撕裂过、啃噬过。仅剩下浑圆半截的下身杵在街边的人行道上。锯齿是手术刀,石灰是消毒液,手术是环卫工做的。前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让它们的头部及枝杆全部枯死。如今,刚愈合的伤疤上已长出了新的幼芽,枯木而逢春这句话里,在这里显出了不一样的悲剧性。
那些与它们一起落地生根南屏街、金碧路、宝善街、书林街、拓东路上的许多法桐已难觅踪影。有诗人说,这座城市的梧桐树多到我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或许是多年前的事了。它们现在的存在仅表现在那些老到懒得装假牙,拄着拐杖的耄耋之人唠叨记忆中,这座城市的夏天被宽大如巨伞遮蔽着夏日暴晒的,处处都是它们亲戚的,黄金季节已一去不复返。或许仅存的他们还在倾听秋雨,打在叶面上的嘀嗒声来追逝那些童年的影子,但古旧的木箱底已成为了日渐腐朽的坟墓,年轻的人们已经被潮流带得走远了。
然而,还来不及改变的是正义牌坊上镂刻着五华山向南延伸的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成堆成片的高楼大厦已覆盖了天际线。这根中轴线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牵引,宛如一根风筝线,还在紧紧地拽着这座美名为春城的风筝。问题是,风筝也有收不回来的时候啊!因为,线绷得太紧了。
事实如此,五华广场上空盘旋着的风筝已断线飘逝,东南方向的呈贡新区已经崛起,且被那座正看成塔侧看成帆的巨大高楼挡住了视线。而清晨高楼倾斜的影子,正好覆盖了那片建于民国年间临街的竖式商铺楼及文庙西巷。
巷子口报刊亭的老张正在清点着他手中紧握着角票,这应该是他一整天卖报刊的收入。此刻,天空是阴沉的,蜿蜒于北边的长虫山并不能阻止入侵的寒流,反而与东面碧鸡山的寒风交汇一起,从呈贡新城、滇池湖畔、碧鸡关、黑龙潭的高楼林立的夹缝间肆意横行,直逼马市口的文庙西巷。
寒风凛冽。报刊亭旁加气补胎的摊主补胎刘拢起了一盆柴火,火势很旺,或许是寒风助火或许他泼了柴油,四周弥漫着乌黑的浓烟和刺鼻的异味。补胎刘蜷缩在火盆旁。事实上,在这寒冷的季节里谁还会骑车出行呢?况且自行车如织的时代早已过去,补胎加气行业早已进入词典大全的页面,仅供后人查阅而已,一个时代已经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体现了它的凋零。
报刊张并没有伸手去烤火,他穿着一件黄色的旧军大衣,戴着毛茸茸的护耳及手套,只是杵在一旁不停地跺脚,并从口中呼出一团团白雾在手中搓揉,搓揉过的白雾又从报刊张的指缝间溜出贴在了报刊亭的玻璃窗上,白花花的一大片。
若不是我们院旁的围墙上盛开着一串串粉红色的炮仗花,谁也想不到所谓春城的冬天会是这样子的冰冷。
报刊亭置于我们院子门口马路对面的巷子口,它背靠那片竖式商铺楼的山墙面。无论晴天下雨,我都会出门买晚报或到报刊亭对面的小杂货店买香烟,天气晴朗时,杂货店的老头会支一盘象棋在门口,遇到厮杀热闹,我也会驻足观望。时间长了,自然与开杂货店的老两口及报刊张、补胎刘、钥匙寇熟识。
钥匙寇姓寇,名单。他配钥匙的摊子就摆在报刊亭旁,和补胎刘形成报刊亭的两翼。五华山周围没有配钥匙的,他的生意自然要好一些。此时,他刚配好一位中年妇女的钥匙,起身与补胎刘一起烤火。开杂货店的老头姓尚,至于他婆娘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年庚几何谁也不知道,所以熟识的人都跟着他喊她:喂。
杂货店位于报刊亭对面,小,小得几乎盛不下老两口。事实上,它仅是一家单位的值班室改造而已,在巷子口围墙的拐角处用空心砖头垒砌而成,临街开一窗户,窗户上伸出一块绿色的雨棚,雨棚积满了灰色的尘埃,失去了它原本的色彩,窗台上摆放着一部红色的公用电话显得异常的醒目。屋内置一货架,货架堆满了香烟、白酒、酱油、酸醋、饮料,以及一些电池、小孩子玩具等日杂用品。货架旁是夏天放于窗外的大冰柜,它几乎占领了店里残留的空间。而店里还要洗衣、洗菜、做饭。杂货店的老尚说,他就住在货架后面搭起的楼面上,他老婆喂,住哪儿就不得而知了。
夏天炎热的时候,我时常看到老尚在店里的货架前擦洗赤裸的上身。他是一个六十年代当兵出身的人,身上有伤疤为证。
报刊张对我说他一直在等我拿报纸,不然他早收摊回家了。他老婆晚上要坐火车回四川老家做胆囊切除手术。我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他说医保报销不了。后来他又说,翻年后报刊亭不准摆了,昆明要创文明城市,区里来过好几伙人,手里都拿着红头文件。
春节过后,我再也没见过报刊张和他的报刊亭。报刊亭的位置空荡荡的,仅有一块保护古建筑的石碑杵在那儿,后面的山墙显然已用乳黄色的漆粉刷一新,而墙头上的蒿草好似又长高了许多。
报刊亭清除后,补胎刘仍在,钥匙寇还在。开春后,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补胎刘的生意依然没有起色,反而在春光中显得更为清淡。他时常蜷缩在人行道旁的墙角边,依着墙角打着瞌睡儿。是的,他是用头上的帽子遮着半边的脸,脚下杵着两个打气筒及装着杂七杂八材料的手提木匣子。这就是他讨生活的全部家伙什儿。
再后来,创建文明城市结束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补胎刘,一如没有见过报刊张一样,连同那些创建文明城市期间,随处可见的戴着红袖套的志愿者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我的眼前。
钥匙寇和他的钥匙摊还在。只是他把钥匙摊挪到离巷子口更远一点儿的巷子里,摊位的旁边,竖着几个装满垃圾,溢出黑水的垃圾桶。我看到了两只流浪狗在泼洒的垃圾上搜寻食物,及一只走失的猫,站在垃圾桶上翘着尾巴龇着胡须。
于是,我捣腾我的记忆,相册里这座城市并没有色彩,仅是一张简洁的黑白的老照片。老照片里没有遛狗的人和怀抱养猫的人,也找不到一只流浪的狗和一只走失的猫;老照片里没有气势磅礴的高楼大厦,但有梧桐树叶,显出风吹的模样;老照片里没有如蚁如蛇般蠕动的汽车流,但有自行车,以及仿佛飘动在耳边的叮叮当当的铃声;老照片里没有灯火辉煌的夜色,但有稀稀落落的灯光与夜空中皎洁的月光相对。
是的,不远处马市口车水马龙的喧嚣,淹没了滇池湖水拍打堤岸的击节音。我无法定位其声音的方向,缘于仰望夜空看不到星月的恍惚。我散乱的眼神飘过正义牌坊但找不到定格的画面。往来的人群摩肩接踵,靠得那么近,但彼此那么陌生。交通协管员尖锐的哨音让你木然地抬腿急行。在这纷繁芜杂的空间里,我始终寻不到报刊张及补胎刘的影子,我不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哪儿?在干什么?我便觉着这座城市比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荒凉,还要孤寂。这种孤寂,比两百多年前孙髯翁的感喟:“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更加猛烈,更加没有原由。
我已找不到报刊张和补胎刘的影子了。那间小杂货店俨然已改头换面,装饰一新,易主他人。而老尚及他的老婆喂,也已不知去向。只是中间一门面房仍旧悬挂着胡志明故居的铜牌——那个让老尚路过总要瞅一眼的金黄色铜牌——这个老尚在失忆的时候,一片茫然的漆黑的记忆大海中,唯一的灯塔。
老尚在文庙巷子口开杂货店有些年头了。我十多年前搬到五华山时他就开着这家小杂货店,那时他五十多岁。我时常去买烟,他卖的烟皆为正品,在假烟盛行的年代,实在难得。但我从未见过他店里应该悬挂着的烟草许可证。问之,他说卖真家伙用不着那玩意儿。我觉着老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他身材魁梧,腰板挺直,寡言少语,逐渐秃顶的脑壳上残留着一道凸起的伤疤;他喜欢下棋,但臭棋篓子一个,且嗜酒。
记得那是一个干旱的夏天。从开春后一直到了六月没有下过一滴雨。天气死热。晚饭后信步到了杂货店,见老尚裸着上身仅穿一条半截短裤独自坐在杂货店门口,呼呼地扇着葵扇,满脸通红,显然喝过酒了。趁着酒兴,问起了他头上的伤疤。六十年代中期,老尚在参军一年后便随部队开拔到了越南北部。那年美越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老尚说,他们连在一次执行特殊任务中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袭击,伤亡惨重。头上的伤疤就是那次战斗中落下来的。这段历史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唯有伤疤,对映着沉默。
回国后,弹片是取出来了,但留下了后遗症,时常感觉头晕眼花,脑袋发胀。部队呆不下去了,便转业到家乡,在商业局保卫科干过,给食品公司看过大门。后便辞职办养猪场。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又办起了酒厂,扩大到人们改称了他尚百万。在一次省里乡镇企业家表彰会上,老尚见到了他的老连长。老连长已是某银行的行长,老战友老首长见面,酒至微醺后老连长告诉他养猪烤酒只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老尚带着首长的指示回到家,毫不犹豫地变卖了酒厂、养猪厂及所有家当,带着他的老婆、娃儿及上百万的士兵杀向省城。九十年代初,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野蛮生长起来。老尚也在老首长的指示下,花掉了所有资金并筹资、贷款搞起了房地产。那一年,老尚说是他最激情的一年,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在盘算着如果赚到几千万元,要怎样子才能花出去?他说有一次,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自己在一个山清水秀太阳高的地方植了一片果园,挖了一池鱼塘,栽了一块秧田,种了一畦菜园,养了一条狗,两头牛,三只羊,四头猪,一群鸡鸭,盖了一间很大的茅草房。房是木头架的,土坯砌的,茅草盖的,冬暖夏凉。房下挖了一个大地道,几千万就埋在地道里,地道的口就在床下,安全又踏实。
事实上,老尚想得太美了,以至于还来不及细细回味,首长就出事了。
首长因嫖娼被停职反省,并接受组织调查。一月后,银行通知老尚,他的贷款属于违规贷款,老尚前期投入的三百万元血本无归。其中有一百多万是集资而来的。
首长回到原籍山西老家去了。临行前含泪相别,老首长说,对不起了,兄弟,你还是跑路吧。自此老尚走上了流亡之路,一去七年,直到知道儿子出事:儿子杀人了。老尚几乎跑遍了半个国土。讨过饭,露宿过街头,他和这个家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每月一号他打一次电话回去。电话在母子二人租赁的房子必须就近的公用电话。
儿子是他尚家三代单传的血脉。儿子为一个女孩争风吃醋杀人被判死刑,儿子死了,但他还活着;那年儿子二十岁。老尚五十岁,老尚说到这儿的时候,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
事实上我搬到五华山认识他和他的喂时,已是几年后的事,他缓过劲来了。直到几年过后,我突然感觉老尚变得陌生起来了。
一日饭后,我去杂货店买烟,他和喂正在吃饭。他突然对我说上个星期我买烟给了他一百元假钱,要我还他,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出差一个月,上星期他怎能见到我呢?在我愣住的时候,他老婆喂在一旁拉着他的衣袖反复对他解释说: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更胖的人。他这才嘟嘟囔囔地坐下吃杂酱面。
老尚的头脑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时常认错人,记不清回家的路。有一次,他的老战友拉他去吃午饭,回来时他不晓得要怎样子坐公交车回家,高楼大厦恍若越南的丛林,他踯躅徘徊在北京路直到黄昏。直到好心人问他要去哪儿,他说:我要回胡志明故居。
最后一次去杂货店买烟时,老尚正和巷子里的一老头在下棋。报刊张和补胎刘说,老尚现在的棋路总是一套,不会变换了。我在一旁喊他卖烟,他抬头瞅了我一眼,回我一句:就不卖给你,你的钱是假的!
去年冬天,一场寒流袭击了昆明,法国梧桐树和小叶榕冻死了许多。
现在我总是想到报刊张、补胎刘、老尚及他的喂,还有正在用锉刀的钥匙寇。
有时,在这茫茫的水泥丛林间,我感到生命的脆弱、苍白、孤寂、渺小,如尘埃,如花絮,如蜉蝣,如蝼蚁。站在西山上俯瞰这座巨大的水泥之城。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我在马市口,在川流不息的车河、人流嘈杂的声音里,我有一种冲动:嘶吼我的名字。但我知道我的声音会被这个钢筋丛林吞噬殆尽,我注定不会听到我的回音。
海菜花
海菜花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一般称海菜。可食用,极富营养,也可药用,养肝明目。
西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偶尔有卖。我和雨君爬山回来,但凡遇到总会点上一钵芋头煮海菜。饭馆里的海菜大都用水桶或木盆浸泡,色翠绿,粗如筷,茎呈藤状,手触滑腻,闻之如鱼腥味。起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雨君时常外出,博闻强识。她说是海菜,与芋头同煮,是滇西大理的一道风味菜。
大理风味菜海菜芋头汤做法极其简单。将芋头蒸熟或煮熟去皮,再切以块状或坨状,后将洗净的海菜切断与芋头下锅同煮,加少量食用油及精盐,至熟。起锅前佐以鸡精及黑胡椒即可。汤色明亮、稍稠、白绿相间;清爽可口,鲜美致极。可作饭前开胃汤。若用骨头汤或鸡汤烹制,更佳。后来,雨君说,海菜还可素炒或凉拌。果然不诬,海菜素炒及凉拌,色泽翠绿,入口鲜香,可下饭或佐酒。
饭毕,雨君说海菜有一雅名,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就是猜不到,问店家,店家竟然不知。雨君脸上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我又问店家海菜是滇池里长的么?店家嗤之以鼻,答:哼,就滇池那水长得了吗!是洱海。
今年初秋,我去大理,特意到海边看海菜花。初秋的洱海,碧海蓝天,水天共色。天蓝如洗,白云朵朵;海子上飘洒着星星点点雪白的花,微风拂过,水动花颤。
那星星点点随波而颤的花就是海菜花,远目而视,风起时,随波飘荡,仿佛无根;走近而视,白花黄瓣,一片片看似浮萍又似莲花漂浮在清澈见底的水面,一株株、一束束、一片片随柳而动,随波而起,水起扬花,婀娜妩媚,摇曳生姿。宛若一片晶莹剔透的水上舞台正在举行一场以风为乐、水为衣、花为人的盛大舞会。美极了。
后来,友人告诉我,海菜花又名水性杨花。原来如此。我想起了雨君那一丝狡黠的笑。大理的白族食馆,每家都卖海菜。那段时间,我几乎顿顿都要吃海菜芋头汤和海菜炒腊肉。上午海菜芋头汤,下午芋头海菜汤;上午海菜炒腊肉,下午腊肉炒海菜。友人打趣说:你想水性杨花呀。
事实上,海菜花对水质特别敏感,只生长在清澈的毫无污染的河流及湖泊里,若水质稍有污染便会门殚户尽。故而又称富贵菜。早年间,昆明滇池满湖满岸皆是,不稀奇,但后来绝迹了。大理白族有一段歌谣:“大理海子无根菜,不飘不落不生根。”这段歌谣听起来觉着漂泊无根,不免使人黯然神伤。
在昆明我家后院。那日午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棵老槐树,一张石桌,一副象棋,一盒烟,一壶茶,一条懒狗;两个杯子,两条石凳,两个人,坐在石凳上对弈。
老刘是我的邻居,平日无事,喜欢邀我下棋喝茶聊天。开棋便是千篇一律的当头炮,马脚蹩断了他都不知道。他喜欢聊天,聊老昆明,聊他家官渡区六甲乡。起初,认识老刘时,听不懂他讲的官渡口音,甜白酒他说“甜伯酒”;没意思他说“某得心昌”;恶心他说“槽逼十奈”;没有他说“某得”;什么他说“喃”;做什么他说“整喃”。后来,他却说我说话快,他听不懂。
说慢点就慢点。我给他一支烟,对他说:“老刘,讲讲海菜花吧,滇池里的海菜花。”
老刘家是官渡区渔民,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他说起海菜花便扯上了他爹,扯得兴起又扯到他爷爷,扯到他爷又扯到滇池,扯到滇池又扯到西山。他声音浑厚、鼻音重、满满的官渡腔:
“喃?海菜花,早就某得咯。”
他燃起烟,深吸一口,随即鼻孔如两座烟囱。
“你们六甲乡,有吗?”我问。
“有呢嘛。我挨你说,小时候跟老爹(爷爷)出克(去)打鱼,那个时候的湖水么清汪汪呢,照得清人照得清船,瞧得着撑船的竹杆戳到底,瞧得着湖底的小鱼小虾么在海菜花根窜来窜去。七八月份,阿么么,一眼望出克(去)一湖尽是白生生呢海菜花,打鱼回来么顺带捞上一提咯(一筐)海菜回家。”
老刘拿起茶杯一饮而尽,狗伸着舌头看着他。他放下茶杯接着说:“那个时候的湖水么板扎(好)得很,渴了么手一捧,凉瑟瑟(丝丝)呢甜蜜蜜呢,现在的瓶装水某得比;煮锅鱼整点盐巴就得咯,某得(没有)那么多讲究,拉个兴(哪个兴)放佐料呢。”
院子起风了,午后的阳光从老槐树上散落下来,和阳光一起落下的还有纷纷扬扬的槐花。老刘家的狗从石凳上跳下,用它的前蹄扒拉着树影下的槐花。槐花和它身上的毛一样白。
事实上,几千年来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滇池的水是干净的。一条天然的海埂把滇池切割成内海和外海。海,有草海和深海之分。草海里纷繁芜杂的水生植物滋养着、净化着滇池无边无际的湖水。鱼虾成群,小草摇曳。堤柳、白鹭、渔舟、碧波荡漾的湖水。徐霞客在他的《游太华山记》中对滇池有着详细的记载:“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十里田尽,萑苇满泽,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
清乾隆年间,孙髯翁挥毫落纸大观楼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史书记载,滇池从唐宋时期的510平方公里到了清朝已缩减至320平方公里。这是自然的萎缩。
历史上的滇池北起松花坝,南至晋宁,东至呈贡,西到马街。
明清时期,昆明八景曾醉倒了多少文人墨客:滇池月夜,云津夜市,螺峰叠翠,商山樵唱,龙泉古梅,官渡渔灯,灞桥烟柳,蛇山倒映。我曾看过法国人方苏雅在1899年拍摄的“蛇山倒映”图。蛇山倒映图是清朝昆明最迷人的八景之一。历史上的蛇山又名长虫山,位于昆明城北。如今,蛇山倒映、坝桥柳烟、海菜花湖、金线鱼已消失殆尽,灰飞烟灭了。
老刘的狗汪汪地叫了起来。他起身指着他的狗骂道:“小砍头,嚷拉样嚷(嚷什么嚷)!整天嚷逼麻麻呢(乱麻麻),回来!”他的小砍头还真听话,回到他的脚下摇着尾巴。他的狗是听到对面楼里的狗吠声。
“将军!”老刘把他的马挂角到我的帅旁。我一看,他的马又蹩脚了!我拿起他的马放回原位对他说:“又是蹩脚马,还是说说你们村边的海菜花是怎么死绝的吧。”
1969年的12月,各行各业的10多万人扛着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跟着一位将军拉开了围海造田,向滇池要粮,移山填海的大幕。发起了筑堤、排水、填土的三大战役。结果是山被炸了五座,平了八座,滇池缩水3万亩,草海消失2万亩。老刘说他家爷孙三代都参加了那场向滇池要粮的战役。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学生。
老刘正说着,他的小砍头对他哼哼唧唧,他用脚踹了它一下。
事实证明,那是一场惨烈的伤害——人对自然资源的极端开发,带来了的灾难性的伤害。老刘说,其实围海造田的土地最高亩产仅为五十多斤,大多数土地,颗粒无收。
下午的阳光从西面穿过老槐树稍,洒在老刘和他的狗上。人,一头白发;狗,一身白毛。他拿起桌上的香烟说道:
“来,兄弟,咂起(抽烟)。”
我问他海菜花在他们六甲是怎么吃的。
老刘从我手里生扯活拉地抢过刚被我的象飞掉的马,接着说:“你放我一马,我才挨你说。”老刘不仅会使蹩脚马,且喜欢悔棋。
“我教你一道我老爹传的海菜花吃法:把腊猪骨头熬成汤,然后呢再把蚕豆米放进去煮化,最后呢再煮洗净了的不要刀切而用手扭成段的海菜。这是海菜豆米汤。”老刘一口气说完这段话竟然没有夹杂他的方言。
“就这么简单?!”我问。老刘说就这么简单。
“好吃么?”
“好吃,小时候吃的,老爹做的,老爹死后就某吃过了(没有吃过)!”老刘咂着嘴巴说。说完低头抚摸躺在脚下的小砍头。
雨君有一次跟我说,和我下棋的那个老刘,说的话,她很难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