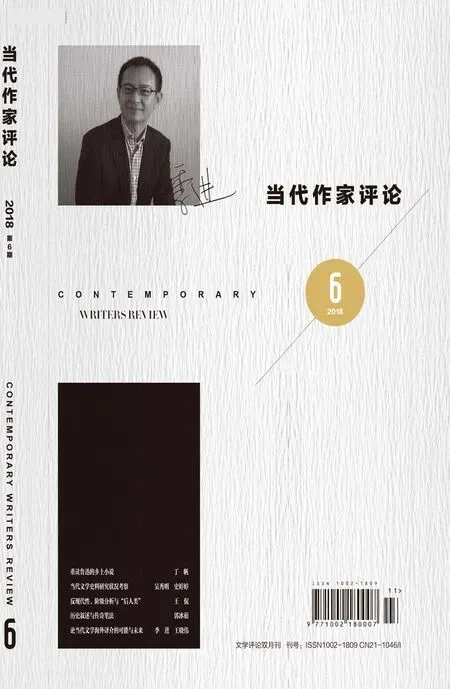从《牛鬼蛇神》到《唐·宫》:马原标签时代的终结
杜婧一 程 革
开启中国 “先锋小说”创作风潮的领军人物马原,在20世纪80年代可说是文坛的一面旗帜,其独特的叙事形式和标志性的“叙述圈套”成为评论界争相探讨的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短暂的“黄金时代”里,马原的藏地文化背景、新鲜的叙事特征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观念的吸收与借鉴,使他的小说充盈着中国文学不曾有过的新颖感和惊异感,当时的读者对如此“另类”的写作方式毫无招架之力。评论家吴亮在那篇知名的《马原的叙述圈套》中评价其说:“马原是属于最好的小说家之列的, 他是一流的小说家。”吴亮提出的“叙事圈套”很快成为对马原先锋叙事的标志性概括,后来的评论者都难以避开这一特性。此外吴亮还用“叙述崇拜、神秘关注、无目的、现象无意识、非因果观、不可知性、泛神论与泛通神论”八个词来概括马原的创作,“叙事圈套”和“元小说”写作成为马原先锋小说的特征标签。
只不过,来势汹汹的事物往往难以持久,随着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变迁,先锋派也随之萎靡、沉寂,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先锋文学浪潮的整体回落,马原明显流露出后劲乏力,激流勇退,最先选择了息笔,留给守望者们大片空白的猜想空间。
令人意外的是,2012年,蛰伏20载的马原带着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杀回了文学界,这在圈内引起不小的震动,接下来的几年里,《纠缠》《黄棠一家》等多部长篇相继问世,不由得引发众人对先锋往事的种种回想。2017年12月,马原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唐·宫》出版,再一次颠覆了读者对他的认识,一时间引发评论界和读者的猜想——马原的小说创作要彻底转型吗?回顾马原近40年在创作上的起落折转,尤其是回归后几经更替的创作抉择,这位不再年轻的先锋小说家在争议声中已悄然转身。近年来马原专注于长篇小说写作,曾经那些尖锐鲜明的先锋叙事特色在回归后的作品中渐渐隐去了身影,在告别标签化的时代里我们仍能依稀辨认出其先锋精神的存续与蜕变。
一、搁笔与复归:转向写实之路的“前小说家”
1991年以后马原的忽然封笔是引起轰动的一件事,毕竟在外界看来马原还处于写作的“全盛时期”,因此大大小小对马原的访谈中都会问及“中断写作”的原因,马原的回答也很坦然,就是“写不出了”。他将自己江郎才尽的原因归结为“离开西藏”。马原的创作是那种极具经验式的、感悟性的、体验式的写作,他需要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放精神力去驱动,而这种精神力需要内在感觉和外在遭遇相共鸣产生一种强大的共振反应,西藏生活曾是保持他旺盛想象力的精神之源,失去了这种强大文化氛围的庇护,无异于遗失了灵感源泉。
直至2012年,马原带着新长篇《牛鬼蛇神》杀回大众的视野之中,再度点燃人们的热情。这次回归可以说与他在2008年患上的那场严重的肺病不无关系,在与疾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马原意外地重新发掘到与生命直接对话的空间,也放下了从前对小说的焦虑与执念。小说《牛鬼蛇神》实际上可以算作马原的一本自传,是隐居20年的马原对读者的一种交代,但这部被奉为“王者归来”的“汉语写作典范”并没有承担起“当代文学巅峰”这样的重责。尽管有格非、韩少功、桑格格、叶开等人的高度评价和极力推荐,但是读者与评论家似乎并不买账。2013年他的《纠缠》出版,这一次在“大元”回来之后,熟悉的“姚亮”也重回读者的视野了。《纠缠》是马原力图折射现实的一部荒诞剧,是卡夫卡精神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重现。自《纠缠》开始关注现实题材后,马原计划完成由《纠缠》《荒唐》《搞笑》构成的三部曲。2017年出版的《黄棠一家》,原名《荒唐》,同样也是一部表现中产阶级荒唐生活的现实题材小说。“他叫马原,他是个小说家。他也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曾经标志性的语句再度出现在《黄棠一家》当中,让关注他的老读者们会心一笑,也显示了他重拾写作的决心。严肃文学之外,马原还尝试了童话写作,从《湾格花原》起已完成了自己的童话三部曲。
归来后的马原有了很大改变,他不再是那个完全处于自我经验世界中心的掌控一切的叙述权力者,而开始更为考虑到阅读者的接受情况。《牛鬼蛇神》《纠缠》《黄棠一家》这三部作品中每一部的走向都可以视为一种过渡性尝试。《牛鬼蛇神》其实是离开西藏这些年马原心路历程的一次深度展示,是一部承上启下之作。对于熟悉马原过去写作模式的读者而言,《牛鬼蛇神》虽然没有刻意地重复叙事游戏,但是整部长篇中呈现了太多的怀旧元素,是马原对以往做出的一份有突破意味的总结。如果说《牛鬼蛇神》停留在一个泛神论者在新世纪异变环境中对人、鬼、神存在问题的自问自答,《纠缠》与《黄棠一家》则直接表现了马原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不满情绪。这两部书的叙事方式基本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处理方法,只是对于生活化内容的情节处理上有着强烈的荒诞主义倾向,骨子里仍保留了现代主义气质。《纠缠》以繁复细节展现姚亮姐弟俩无端陷入的一场因捐赠引发的遗产官司,文本显而易见地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审判》。但《纠缠》并不是一部崭新的现代主义作品,姚亮也不是另一个K。《审判》中K遭遇的其实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是关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象征隐喻。而姚亮面对无休无止的纠缠却是社会现实问题的集中堆砌,是马原对中产阶级生活的简单化想象和以偏概全的形式批判。《黄棠一家》开篇就交代了黄棠及其一家人的优越身份:黄棠是一家大公司总经理,她的丈夫刚任了开发新区主任,两个女儿一个是摩纳哥籍富商、另一个是大型节目策划人,都嫁到了条件优越的丈夫,唯一的儿子在美国读高中,交往的女友也是一个美国籍的富家女。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接踵而至的一切冲突正符合主人公名字的隐喻——“荒唐”,有了明确的荒诞意味。马原在侧重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仍表现出一种矛盾:现代主义倾向和向传统复归之间的矛盾。
从《拉萨河女神》《虚构》起,作为形式典范的“叙事圈套”就成为贴在马原身上的一张标签。尽管马原对此也颇为受用,但先锋的价值在于不断的破坏与重建,持续开拓新的想象空间。顶着形式主义的名头久了难免会滋生焦虑,曾经的骄傲也渐渐成为新的束缚,不能持续地突破,就意味着某种死亡,这大概也是当年马原毅然搁笔的重要原因。重新写作的马原并没有完全抛弃形式技巧,但能够明显感到他为有所改变而进行的反思与努力。再度回归文坛,马原专注于长篇小说写作,这不同于过去的中短篇创作,技巧和形式开始退居幕后,长篇小说更加依赖作家的生活阅历和思想深度,这与马原这些年来频繁变换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更为契合。不论是自传小说、荒诞社会小说还是迎合时代口味的历史小说,马原都把注意力从纯粹的叙事形式拉回到对外在经验世界的关注,收敛起张扬的先锋姿态,将晦涩的形式表达向一种较为平滑、现实的维度转向。“在对经验的娓娓道来中,马原的叙述方式变得内敛、平实,虽然这种叙述姿态失去了早期马原小说中新颖与神秘的魅力,但在传达经验及意义的过程中,叙述却重新散发出了一种新的张力与力度。”
二、突破与革新: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题材
实际在写作《唐·宫》之前,马原就已经在向现实题材靠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但有距离的“和解”。《唐·宫》无疑是马原“转型”力度最大的一部。但是,马原的“转型”似乎又不是一种简单的转型,而是一种体验的“差别形态”。或者说,马原的转型依然渗透着他一贯的文学精神。
《唐·宫》整个故事选取在中晚唐唐文宗在位这段时期,以什么样的创作观念切入将近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历史,如何拿捏把握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原创作《唐·宫》面临的最大问题和考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谈及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时曾提出“历史小说创作大略说来有两条路子,一是可称为‘教授小说’,即在创作中需要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马原在创作《唐·宫》的过程中显然选择的是第二条路,即尽可能在注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他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才情,细致刻画了11岁的女主人公“小丫”从籍籍无名的扬州大和教坊里的丫头,以扬州府府尉女儿“玉央”名义入宫,在历史机缘和命运巧合推动下,与晚唐文豪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太子李永、太子好友兼马球师傅杭龙等人产生的交集和情感纠葛。同时,还把这一时期发生在庙堂之上的牛李党争、甘露之变、宦官专权、夺嫡之争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以及波斯、回鹘等域外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晚唐经济文化生活和人文景观以“浮世绘”的形式一一呈现出来,为读者细致勾勒了一幅晚唐风情画。
在小说细节的把控和处理上,马原突出体现了“粗”和“细”两个特征。“粗”着重体现在马原在并不追求“拟古”的阅读体验,在《唐·宫》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语汇运用上,马原基本采用的是现代白话小说的风格特征,这种方式好处在于不会给现代读者带来一种“隔”的感觉,大大降低了小说的阅读门槛,里面人物对话浅白晓畅,“池浅王八多”、“异装癖”、“热脸贴了冷屁股”、“搞搞清楚”等现代词语不时掺杂期间,甚至出现了过生日吃奶糕、敷面膜、做美甲、后宫嫔妃们讨论美容与形体等现代生活才有的情节和桥段,增加了阅读趣味性。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一些情节和事物缺乏考证,导致文中出现皇太子向母亲请安时与母亲拥抱、唐末才从西域传到中土的西瓜在小说里寻常百姓家就能吃上等明显不符合史实的情节发生,显得娱乐有余而严肃不足。“细”则表现在马原有意识地在小说中注入妆容、养生、美容、药材等细节知识,并让它们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这些与中医养生相关的知识既旧且新,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一方面赋予小说以极强的感受性,一方面无声地推动情节自然发展。同时,马原还将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的诗词歌赋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李商隐《锦瑟》《登乐游原》,温庭筠《金虎台》,杜牧《江南春》等诗作产生都与三人同玉央的交游紧密相关,成为小说极具可读性的精彩部分。
可以看到的是,在进行《唐·宫》创作时,马原努力想要摘除身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因此,他一直竭力避免任何技巧与形式的运用,确保整个作品的质朴流畅。但同时,马原又有意识地将目光放在对当下现实的观照上,对小说主题进行了现代思考,让穿上古装的小说人物演绎现代的故事,将以往单一的政治视角转换为文化视角、人性视角,使得历史线索更加复杂生动,更具有真实感、立体感的美学品格。
马原赋予了《唐·宫》现代女性职场文学“同质异构”的特点,让读者很容易从古装华服背后读出不同时空下女性“职场”生存困境,以及背后潜藏的相同文化本质。小说里后宫女官的工作生活与现代女性职场生活有着相同的共性,一是空间的封闭性,二是权力的唯一性,三是秩序的不可撼动性。通过这种微观的政治结构,极致展现了一个相对固定空间里人群内部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争斗。在无关乎国家社稷的宫闱深处,主人公玉央和清蔷、胡蝶、范娉柳、安其凤等众女官,她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改变自身命运,努力去把控生活的主动权,但是封建和男权文化对女性地位的全面宰制让她们举步维艰,要么成为霸道狠毒充满“雄性”特质的女强人,要么从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出局,实际这都体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治或是“职场”体制对女性的异化和改造。无论在什么样时代,职业生活都是展现历史潮流、社会关系、人性参差的绝佳放大镜,它叩问的是最直接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现实,影射着当下的现实社会矛盾和价值取向。
马原通过对玉央、清蔷、胡蝶、方汀等十多名复杂精彩而又性格鲜明的女性艺术群像的刻画,充分彰显她们个性天赋和能力才干,赋予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鲜活的灵魂。在众多女官里面,玉央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她出生微寒却天资聪颖,拒绝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藏拙”的告诫,选择入宫成为女官,立誓为全天下女子编著《容妆全书》,显示她对封建女性极端弱势地位的强烈反抗意识。在奋斗过程中,无论是面对荣辱得失和灾难祸患,都能做到波澜不惊、顺势而行,甚至对陷害自己的人保持怜悯宽容、以德报怨,最终赢得所有人的尊重。她的个人成长历程实际上是在中华悠远的民族文化中寻找自我完善的过程,体现了以“内在超越”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特质。同时,马原之所以选取唐朝作为故事背景,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历史上唐代是道教蓬勃发展时期,道教所倡导的自然和谐、反对禁欲,以及儒家礼教对社会控制的减弱,促使唐代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礼教对自身的约束,因而更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就会越大,野心越大,风险也越大,显然马原没有忘却自己曾是先锋文学引领者的身份,向《唐·宫》这部历史题材小说里加入了更多来自当下时代的现象和隐喻,显示出强烈的企图心。在《唐·宫》里,马原将数个世纪以来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男性与象征着强大、力量、荣誉、公正的雄性标志全部进行了解构。首先,小说里基本所有的男性形象都处于被模糊、异化和弱化的状态,要么隐匿在女性形象背后,要么行动和主张深受女性影响,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皇帝唐文宗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勤勤勉勉、宵衣旰食,致力于复兴王朝,但又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和气魄,以至于在朝堂上难以掌控各方势力,策划的“甘露之变”最终一败涂地;他在后宫治理上缺乏驾驭局面的能力,被杨贤妃略施苦肉计就骗得王德妃被流放、太子李永被软禁,双双死于阴谋之下。马原还设计了太子李永的一个隐疾——“异装癖”,他三番五次要求宫女将他打扮成女人。马原在文中并没有交代这样安排的原因,但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来理解,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一个高大的男性形象作为参照和学习的榜样,跟他相处最多的自然是他的父亲,而如果看到父亲更多的暴露出性格的懦弱而不是雄性气概时,其内心深处会慢慢地怀疑自己的性别属性。这样的安排无疑与当下时代女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力量的存在有关,体现了马原对“他时代”的瓦解和“她世纪”的到来的先验预言。
另一方面,小说中男性与女性精神世界的不匹配性也最为突出。伍尔夫曾指出,“多少个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于正常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的美化作用……如果(妇女)开始讲真话,镜子里的形象就缩小。”在主人公玉央的人生经历中,她与杜牧、李商隐、太子李永、太子马球教头杭龙都有过深刻的交集,甚至四人都对她产生过恋慕之情,但无论在勇气、胆色、聪慧、见识上,这四人跟玉央相比都远远不及。四人当中,玉央唯一倾心过的人只有李商隐,李商隐也有与她共结连理的意愿,却因为害怕母亲的反对而懦弱地选择了回避。即便是虚构人物杭龙,在小说里高大英俊、孔武有力,多次保护了玉央,但马原也没有过高的对杭龙形象进行美化,其对政治局势的误判和鲁莽的行动显示了其眼光的短浅,玉央始终无法与他在精神层面完全匹配,鲜明体现出“女性不需要靠爱情而得救”的“反言情”的言情小说特点,由此透示出马原对传统文化中白马王子和公主、英雄救美情节的颠覆以及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冷静审视和批判,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映射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品格。
三、重逢与告别:失落的标签时代与永恒的先锋精神
近年来几部长篇小说不温不火的反响让许多人感慨马原英雄迟暮。马原老了,从年龄来看的确如此,他的写作也不再全然执著于形式,没有刻意去重复年轻时特有的那股新奇、叛逆和不屑一顾的劲头,而是渐渐走上一条较为平和的道路。人们对于马原作品流露出的失望情绪更多是对过往先锋情结的失落。
如今的马原再去重复自己二三十岁的写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苏童、格非、余华也没有重复自己在80年代的创作,他们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这样的选择显然明智合理而且具有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当年先锋文学的炙手可热,着重体现在形式实验和语言实验上,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今天无法延续,这不仅是写作者年龄的问题,更是社会与时代的问题。80年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精神产物的存在,它的地位被极端神圣化了,先锋文学作为反叛精神的一种意志体现,它不是一种恒定的标准概念,而是对创作自由的一种把握,是对时代审美的颠覆与突破,当这样的要求得到一定的认可,这种先锋性就变成习以为常的事物,难以继续称之为先锋了。
从过去一贯的“叙事圈套”到饶有荒诞意味的现实题材再到历史题材通俗小说《唐·宫》的推出,马原来了一场断裂式地自我告别。他抛开了过去引以为豪的先锋姿态,回归到写作本身,开启了广阔的文学尝试。这场告别也许不意味着某种结束,对于60多岁的马原来说或者还是新的开始。他仍然笔耕不辍,对于文学而言,这是幸事。《唐·宫》的出现不能证明马原完全倒向通俗小说和现实主义。等到他的下一部作品问世,可能有浓烈的先锋气息再度复归,也可能又迈入另外的领域。不管评论几何,那张多年前贴在他身上关于“叙事圈套”的标签已经慢慢被揭掉了。从近年来他的写作走向来看很难猜测其未来的选择,只是我们从马原的作品中能明确感觉到,他在多数人心中固化了多年的标签化时代已然终结。
我们还应该欣喜地看到,在读者对马原一辈先锋作家回归后的失望情绪中,还能感知到今天人们对文学先锋性的再度期待。“80年代先锋文学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破坏之后没有一个应该树立的东西”。当时的先锋文学借现代主义外力和时代浪潮的助推势如破竹般地席卷了文学界,在摧毁了许多旧有观念和秩序的同时也试图建立新的规则,但这种重建至今仍没能完成。没完成是因为它失去了某些核心的本质,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启蒙者面临的共同困境——文学再生长机制的缺失。单纯依靠80年代短短的文学“黄金时代”无法催生出完整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看似热闹的现代主义脱离了文学自身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没能激发出文学内在的自生力量,造成表面虚假繁荣根基却脆弱不堪。当形式不再新鲜,外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有所变化的时候,文学盛景便颓然衰败。
过去的先锋是一种突击式的觉醒,它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很强的时代依赖,而今天我们需要的先锋却没有成长起来,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今天的70后80后作家也没有间断新的文学尝试,只不过获得的关注度远不如80年代。对先锋的热切期待普遍存在于较为平淡的文学阶段,寄希望于老派先锋作家再度成为时代弄潮儿显然不切实际。80年代的先锋作家纷纷转型并不是否定“先锋”追求本身,这也正是认识到过去的创作实验脱离了本民族文学的自身根基故而难以持久,因此,无论是向现实主义示好还是与通俗文学握手都是试图弥合断裂的文学自身生长机制,这样的尝试多种多样,并且将一直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