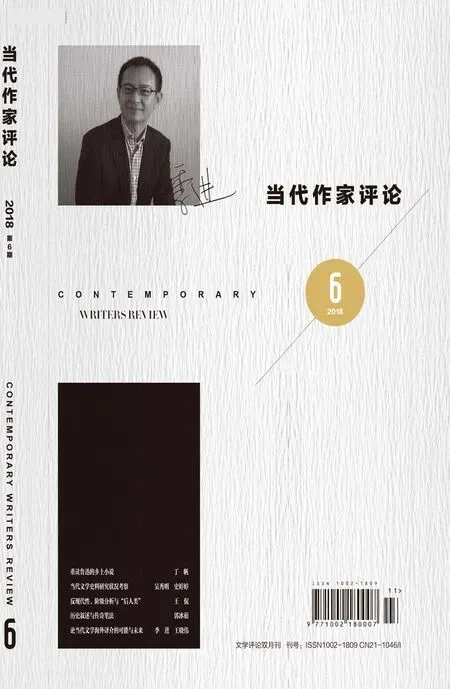最大的变革和最小的反应
——由鲁敏《奔月》兼及其他
杨庆祥
一
……大巴在梵乐山山区意外翻车坠崖,随后爆燃,部分乘客落水不救。全车含司机导游计39人,遇难8人,致伤21人。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我们的女主角,小六,被算在这遇难的8个人中。不过情况有点特殊的是,只找到了7具尸体,有一人下落不明:
贺西南敏捷地抓住后者不放,认定那就是小六。还有一位母亲也在为她的女儿争抢这个配额。像抢一顶帽子,两人都急着往自己头上安。……又有部门提DNA验证,那名母亲不知为何突然垮了,瘫倒地上,决计不肯。贺西南就此胜出。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第一步。
然后,这个可怜而执著的丈夫开始为他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而展开福尔摩斯式的旅程,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被吊起了强烈的同情心和好奇心——必须承认,好奇心更多一些——好奇有二,第一是小六是否死了?第二是,贺西南如何继续他的看起来有点蠢的行为?
鲁敏几乎是立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第二章她就明确地告诉读者,小六并没有死,她是借助这样一个事故实施了蓄谋已久的一次“逃离”:
小六简单地考虑了一下,随即最大限度地拉开双肩包的拉链,粗手粗脚地从里头翻捞出她常年随身带着的一只小蓝包……然后紧跑几步,掷铁饼般牵动腰臀使劲儿轮圆手臂,顺着一个处心积虑的弧线,双肩包飘入半空……管它呢,啊哈,别了。
这真是一个漂亮的抛掷!鲁敏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她并非仅仅要讲述一个关于“爱与死”的通俗故事,不是,她中断了读者渴望情节、热爱戏剧性的猎奇之心,她将本来可能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的结尾——小六死了或者她被某人拯救了——提前告知了大家。这其实已经意味着一部小说的终结。
但是,天哪,这才是小说的第二章。
该怎样将这部小说继续写下去?这已经不仅仅是讲故事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对小说观念、主体人物进行重新放置和安排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鲁敏来说,她制造了一次危险的坠崖——她自己现在就在悬崖的边上,她比小六更危险。
而危险是小说的动力,新的质素开始产生。从《奔月》开始,我们也许可以看一看,已写作20年、可冠为“著名作家”的鲁敏如何摆脱种种因长期写作而造成的美学惯性,并完全不顾已经贴在她身上的带来了众多象征资本的标签,开始——起跑!
二
现在要展开小六的新人生了。小说的叙事由此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贺西南和张灯对过去的小六的重构,在这个部分,小六以不在场的形式在场;第二部分,是小六逃离后的“新生活”,在这个部分,她以在场的形式不在场。第一部分也许很好理解,第二部分为什么说是以在场的形式不在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回答另外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小六究竟逃到哪里去?或者说,鲁敏要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来安置这个从以往的生活秩序里面逃逸出来的人。
这是个难题。很多的批评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批评家李伟长在其文章《逃离的方向,小说能走到哪里?》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奔月》来看,鲁敏毫无悬念地让小六离开了她原有的真实的生活秩序,但是小说家又无法将她送去真空,从原来的轨道脱轨,生活并不可能就此变成无轨列车,还是得建构一个平行的时空安放小六。这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奔月》正在发出一种邀请,邀请读者共同想象,那个可能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类似于一种实验。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经想象过一种场景:在一座圆形的房间里,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写作他们的小说,前提是隐匿他们已经留在文学史上的赫赫威名。福斯特以这种方式强调艺术的普遍性,以祛除“年代学这个大敌”,从而从艺术的角度更好地讨论那些所谓“伟大作家”的写作。我想借用这个实验,将几个不同时期的鲁敏放在这个圆形房间里,假设她们都在写作一部关于“逃离”的小说,这几个不同的鲁敏会将女主角小六送到哪一种可能的世界里去呢?
有一个鲁敏可能会将小六送到东坝去吗?在东坝系列里,鲁敏暂时搁置了现代生活,或者说,她有意通过一种带有挽歌情调的叙述将现代生活“原乡化”,在时空上将东坝设置为一个相对稳定、自洽的生活共同体。在东坝里面生活的人物,比如《离歌》中的三爷和彭老人,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他们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一种对遥远文化的追忆和复制之中。如果鲁敏将小六这样的现代性人物抛掷到东坝,也许会引起一种失衡。《离歌》里面也确实隐约提到了一次,当彭老人死去后,他在城市里工作的儿女回来了,他们对老人们心心念念的习俗、规矩表现出的是“不懂和冷漠”。不过也仅仅如此,鲁敏对此一笔带过,东坝的生活和彭老人的儿女们的生活是如此的隔绝,不可理解,那么,作为彭老人的女儿之一的小六,她应该不会选择回到东坝。她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想起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会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几乎无路可以抵达之处。鲁敏最后终止了东坝系列的写作,一方面固然是小说家的求新求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意味着,对于鲁敏来说,乡愁式的、可以在经典谱系中找到清晰传承的这种书写已经耗尽了其可能性。
另外一个鲁敏呢?会把小六送到《六人晚餐》里面的那个大工厂区吗?虽然现代解释学已经不再认为对文本的解读具有唯一性。但如赫希这样的批评家依然小心翼翼地给出了“意谓”与“会解”这样的区分,“意谓”是作者的意图和设置,而“会解”则是读者的阅读和反应。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六人晚餐》也许是《奔月》之前鲁敏作品中“意谓”和“会解”最分裂的一部作品,我看到很多的批评家都将“会解”的重心聚焦在工厂这样一个特殊化的区域,并由此判断这是一部关于反映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说”——我也曾一度想当然地将此作为前提来判断这部小说的得失。但后来再读这部小说,发现从小说的文本结构和叙事指向来看,它可能无意满足批评家的这样一种“期待视野”。《六人晚餐》更像是一部心理探索小说——注意,这是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比较少见的一种类型——而不是一部“社会剖析派”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社会性内容的呈现不是通过社会性的景观书写来完成的,而恰好是通过个人的心理探索来完成的。《六人晚餐》里面的人物,几乎都处于一种稍微紧张的青春期的心理创伤之中,并不得不在这种创伤中毁灭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丁成功、晓蓝等等——更像是《奔月》中小六的青春期。他们也一直渴望着“逃离”,在某种程度上,小六“逃离”前的生活,可能正是他们当时逃离的目标和指向。那么,小六会反向而行吗?青春哀悼一次就好了,如果要再来一次,最好的笔法显然是喜剧的反讽,但是很显然,鲁敏的气质并不适合做一个讽刺作家,她虽然在小说中也偶尔点缀一些小小的恶作剧式的描写,但那更像是一个作家的童心未泯,而并非指向强力的讽刺或者揭露。从心智的角度来看,《奔月》中的小六要比《六人晚餐》里面所有的人都要成熟、理性,有着非同一般的主见和判断,即使鲁敏有意将她送回那个暧昧的工厂区去小小哀悼一下她的青春期,估计也会被小六拒绝,毕竟,成长不可逆回,这就像小说一样,当它发现可能性的万花筒,就不会贪恋那单一的“成长故事”。
该轮到第三个鲁敏登场了,在这个圆形的写作房间里,不同的鲁敏之间已经叽叽喳喳讨论了很久,也有一大堆未完成的小说手稿放在电脑的硬盘里,这些都可以成为研究的资料。但是正如《林中路》所暗示的一样,对于一部小说来说,它选择了一种可能就无法选择另外一种可能,它选择了一种故事型就无法选择另外一种故事型。或许有人会拿卡尔维诺或者博尔赫斯来反驳我,但是即使在最著名的《寒冬夜行人》里,可能性也只能在可能性本身之中进行选择,这是小说的宿命,和人的宿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现在,轮到了写下《荷尔蒙夜谈》的鲁敏了。坦白来说,这是目前我最喜欢的一部鲁敏的作品,这是一部完全“活在当下”的小说,我所谓的“活在当下”并非指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一定生活在2017年或者与此前后的时间,而是说,这部小说里面人物的思考逻辑和行动逻辑都是当下的、即时的、本能的,是一种基于欲望和利益逻辑而推进的故事,因此,这部小说抛弃了道德的面具,也没有有产者那种温柔敦厚的美学,相反,它撕掉了景观化的面纱,赤裸裸地呈现人性的扭曲和夸张,同时,它暗含了一种“飞翔”的美学,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贪恋这种本能欲望的同时也试图挣脱“欲望”的罗网,完成一次绝地反击,在最激烈的小说《三人二足》里,女主角最后从高楼坠落,以身体之轻对抗了欲望之重。
这,已经非常接近小六所需要的配置。
三
圆形房间里的三个甚至更多个鲁敏并非是我的模仿或者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对鲁敏的阅读和接触中所得到的认知,提醒一下各位熟悉鲁敏的朋友,你们或许没有注意到,鲁敏微信的昵称不是鲁敏,而是——假鲁假敏——这是她的分身术的多么直接的体现。
不仅仅小六是鲁敏的一个分身,而且小六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亦有多个分身。对《奔月》来说,鲁敏将一个“小六”留在了南京,而另外一个小六,来到了一个叫乌鹊的县城:
不大不小,既保留着县城式的老派与迟钝,又勤奋好学地改头换面,模仿和趋近着一种难辨真假的大都会气质。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回到乌鹊县城其实是重新回到鲁敏熟悉的底层生活的书写,由此鲁敏可以驾轻就熟地开始书写故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同时也低估了鲁敏借由小说这一形式探索精神深度的雄心。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所分析的,鲁敏不可能重复其东坝书写和《六人晚餐》式的书写,她只可能进行一种“此时此刻”的书写,因此,小六去的地方,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而只能是一个此时此刻的“并置时空”。在这一点上,鲁敏无限趋近于她的前辈大师鲁迅,在鲁迅涉及逃离的两部作品《奔月》和《伤逝》中——很多人将《伤逝》的这一主题忽视了——并置时空并由此产生的“此时此刻”感是其现代性和批判性最有力的源泉,即使以历史题材著称的《奔月》,其语境也是完全当下的。
并置的时空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同一性。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将“乌鹊”打上双引号,以强调它的“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指的是,“乌鹊”的所有场景、气息、人物乍一看似乎和其他现实存在的地方完全一样,甚至连小六都觉得其气息也很是熟悉。但是随着小六进入到“乌鹊”生活的内部,却发现似乎什么地方都有一点点不对劲——至少在我阅读的观感中,小六在“乌鹊”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普通的日常,但却总是隐藏着小小的变形。这不仅仅是“真假难辨的大都会气质”,而且分明就是“真假难辨”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并置时空的此时此刻,但另外一方面,这一并置时空的此时此刻又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形和位移,一个卡通的装扮,一个电灯的位置,一对老人的外貌,小六还是生活在原有的生活之中吗?我觉得不是的,已经出现了一种“脱落”,这是现代小说里经常使用的一种结构手法,通过“脱落”,小六和她的生活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并离析出适当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小六甚至也不在“乌鹊”——“乌鹊”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装置,虽然这个装置看起来如此真实。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所谓的生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时间的生活,也就是物理性和生理性的生活,饮食男女、财米油盐是之;一个是价值生活,也就是精神性和意义性的生活,求真求善求美、天人感应、物我齐一是之。而现代生活的症候性之一是,时间生活以压倒性的优势挤压着价值生活。在现代高度精确的时间刻度表中,生命被分割,价值被悬置,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之间的撕裂导致了主体的撕裂,从而让完整意义上的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和谐共存的个人生活无法完成。
鲁敏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做过营业员、统计员、团委书记、秘书、记者、公务员等职,工作结婚生子走亲戚做家务,该干嘛干嘛,可以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路人甲。她总有着奇怪又固执的想法:如果我从这既有的乏味的一切中消失?如果我成为另外一种人并进入另一种生活?”这段话往往被视作是一种“写作的动机”,但是这一段话也可以视作是一种时代判断,对单向度的时间生活的厌倦,以及对价值生活的渴望。我们可以说鲁敏的前期写作都可以放在这个谱系里,但是,只有在《奔月》这里,她的这种主题变得如此清晰有力:重新召唤一个主体出现,并围绕这个主体重建价值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小六的全部生活都是梦一般的生活:小六在南京的生活像一场梦,小六在“乌鹊”的生活像一场梦。小六作为母亲、妻子、女儿、情人、售货员、采购员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场梦。在这个谱系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系列作品:《楚门的世界》《穆赫兰道》《南极》《逃离》——现代生活由此变成了一个“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只有通过小说、电影、戏剧的形式才得以展现其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全新的小说(艺术)观念,不是小说模仿现实,也不是现实模仿小说,而是小说和现实互为镜像,彼此造梦,小说由此可以自由行使其创造的权利,而无需再考虑现实对其种种限制。《奔月》在这一点上有着足够的“先锋性”:以小说的形式探索现代个人生活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是多么的微小。
四
那么,一个疑问是,新的主体出现了吗?有价值的生活呢?
如果按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标准来看,主体似乎并没有真正完成,“新生活”也不过是对“旧生活”的重复。“在旧有的地基上进行‘重建’,小说家的注意力难免更多地落在那些熟料上,而对重建照看不周。苛刻一点说,重建没有得以真正完成。作为被移民的新乌鹊人——小六,并没有在新的身份中真正建立足够清晰的自我”。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敏的这次“逃离”并不是要建构一个浪漫主义的“世外桃源”或者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乌托邦”,她对小六生活世界的全部书写都指回小六自身,也就是说,生活世界——现实的和变形的——是小六,同时也是鲁敏得以展开其全部精神生活和内在价值的一种取景器。
现在,借着这个取景器,小六在两方面同时展开对其“自我重建”的努力,一方面是通过他人之眼,一点点回溯一个普通女性波澜不惊的生活后面的暗潮汹涌;另外一方面,是通过自我的亲身“历险”来揭露生活本身的无意义和荒诞感。在这个过程中,鲁敏发现了“目的论”的不合理性,任何对“最后”和“最好”的许诺恰好都是一种不真诚的欺骗,事实是,主体并不能脱离万有引力之束缚,飞到月球上去。即使真的如神话所想象的奔月成功,却依然逃脱不了人之为人的种种牵绊——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鲁敏的《奔月》由此创造了一个寓言的结构,她没有从家族史、日常生活史、传奇剧等等这些年流行的写作路径去开始“我”的故事,也没有用简单的“目的论”来终结这个故事,更没有用一种假象的彻底断裂来虚构她的人物。《奔月》的寓言结构在于它高度尊重了小说作为“白日梦”这样一种现代观念,以黏稠、绵延的叙述方式将主体及其生活世界悄悄地进行了重新配置。现在——
主体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但仅仅是一点点。
世界也有一点点变形了,但也仅仅是一点点。
有价值的生活由此掀开了厚幕的一角,但仅仅是一角。
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够?或者说,主体花费如此大的精力但是却只是完成了如此小的变化,是不是有点遗憾?
在1960年代,科幻小说的巨擘阿西莫夫在其经典作品《永恒的终结:关于时间旅行的终结奥秘和恢弘构想》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MNC和MDR。前者是指Minimum necessary change,后者是指Maximum desired response.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指:最小的必要变革和最大可能的反应。在阿西莫夫的想象中,对现实世界的一次小小的改变——甚至是将一只杯子移动肉眼都无法察觉的距离——可能会带来时空巨大的重构。这是那个时代提供给阿西莫夫的观念:世界不但可以改变,而且改变得不费吹灰之力。
而在鲁敏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颠倒,这一惊人的颠倒借用阿西莫夫的说法来表述就是:最大必要的变革和最小可能的反应。无论是《奔月》还是《荷尔蒙夜谈》中的人,都用尽了全部力气试图改变生活,但是往往收效甚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提供给鲁敏的观念:世界如铜墙铁壁,难以撼动。这正好是鲁敏的时代起点,个人的努力如飞蛾扑火,但也说不上是徒劳无功,因此,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也不能放过,不但不能放过,还要以十倍百倍的力量来对此进行加持或者助力:
小六快跑……小六快跑……小六快跑……小六快跑……
小六快跑。她总算是实现了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逸走了。她一无所知,她万有可能。……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轻与重,在引力和挣脱引力的飞翔中,鲁敏写作的寓言性和时代性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