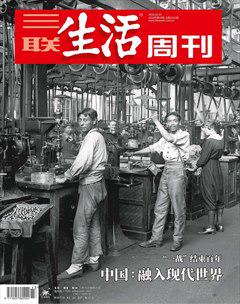张以庆,一个记录者的故事
张星云
留白
张以庆告诉我,2004年拍完《幼儿园》后,他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湖北电视台请了一个长假。他管那叫“留白”。
“留白很重要,每拍完一个片子都需要足够的留白。”
结果,他一休十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常是一种舟舟的状态。”他不坐班,台里没人管他。在家什么也不干,就躺着,有时遇到换季整月起不来床,发呆,浑身无力。“就是废了。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激情。”
他开始吃药。
“抗抑郁症的药,头几次吃副作用比正作用更大,吃完会更焦虑,这时你只能接着吃。但吃上了就不可能断了,就像降血压药一样,终身服用。”他说他直到那时才发现,世界上两万多种疾病,人类真正能治愈的才50多种。
他的抑郁症是从1999年拍《英和白》时开始的。
片子讲的是最后一只作为杂技演员的大熊猫“英”和它的中国女驯养师“白”相依为命,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生活了14年的故事。如今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点开播放这部19年前的纪录片时,“90后”“00后”观众打出的弹幕中,最多的两个字仍然是“压抑”。
“在一间70平方米的房间里,拍一只被关在笼子中的大熊猫和一位不说话的驯养师,没有任何场景变化,按理说只要3分钟就能拍完,但要剪辑出50分钟的片子,这太可怕了。”张以庆说自己最典型的抑郁症状就是那时开始的。“后来越拍越觉得,人们的内心就是一个笼子,每个人都生活在笼子里,我们本质是孤独的。”
人们认识张以庆,是因为《舟舟的世界》。这部拍摄唐氏综合征患者胡一舟的纪录片,让对音乐有着特殊敏感的舟舟成为尽人皆知的“天才指挥家”,也让张以庆成了纪录片领域一个有点传奇的人物。《舟舟的世界》拍完没多久,经朋友介绍,张以庆认识了武汉杂技团的英和白。张以庆觉得,白是一个很独特的女性,她并不认为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跟她有什么相关。在他观察及拍片的一年多里,只见她上过一次街。对她来说,困扰主要来自内心。她拒绝采访,甚至拒绝交谈。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动荡,有一半意大利血统的白,似乎已经把人生看得通体透彻。除了安宁地陪伴英,她别无所求。但采访和拍摄,就是剥夺她的安宁。
张以庆花了三个月时间与白沟通。白在看过《舟舟的世界》后,对张以庆有所了解,她就勉强表示可以一试。但在拍摄的前晚,白突然改变了主意,说不拍了吧,希望你能理解。选题已报,资金也到位了,而且已经花掉了一些。张以庆在电话里力争,电话从夜晚打到凌晨。最后时刻白心软了,但只是同意拍摄,不同意采访。
纪录片出来很长时间白都拒绝看。直到有一天夜里,终于看了片子的白打电话给张以庆说:“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理解我,那就是我父亲,今天有另一个人走进我的灵魂,那就是你。”几年后,熊猫“英”去世了。从此再没有一个媒体记者可以进入白的那个房间。“她拒绝。你解读她,她不需要解读。”后来张以庆去看过白,但觉得没法帮助她。“白以她個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给予了我最深刻的理解。”
《英和白》后,张以庆收获了巨大荣誉。此片获得了当年四川国际电视节四项大奖,那一届BBC参评的片子才只获得了三项。也是此片,让他在2002年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
省委宣传部下了红头文件《关于向张以庆学习的决定》,湖北电视台在大厅里立起了巨大的展板,宣传张以庆的“三个代表四个精神”,全台召开大会向张以庆学习。“那时开大会有个程序,首先是宣读省委宣传部的决定,其次会有个人在台上倒背如流地说我的事迹我的好,最后就是我上台来讲自己怎么艰苦怎么牛,这个要命,我就过不去,我要疯了,因为抑郁症就是不能见大场面。”他说他就像成名后被推到台上表演的舟舟,明显的社交恐惧症,手是发抖的,思想混乱,语无伦次了。
那次开大会的前一天,张以庆需要面对领导念一遍自己的发言稿,通过了第二天才能发言,但他平生没写过发言稿。“最后我被顶到墙根了,幸亏那时我还可以表达,我就说,诸位领导,我想说一个你们谁都不知道的事情,在给《英和白》做后期的时候,我经常想自杀。我的痛苦我无法表达,我连自己都处理不了,我经常跟自己过不去。我不是你们表彰稿中写的那个张以庆。”

纪录片导演、独立制片人张以庆
遇到舟舟
张以庆第一次遇到舟舟是在1995年。
那时张以庆正在拍摄纪录片《起程,将远行》。他跟踪拍摄五名不同专业大学生的毕业实习,来展现人们初入社会的那个特殊节点。其中一名来自兰州的女大学生在武汉乐团实习,每天背着比她自己还高的低音提琴去乐团。
他在拍她实习的时候,却总被乐团指挥台斜下方的一个小男孩吸引走了注意力。那个男孩拿着铅笔也在指挥,身前的谱架上摆的不是谱子而是别的书,但他指挥的神态完全不亚于真正的指挥。那个男孩就是舟舟。
舟舟的父亲胡厚培是武汉交响乐团低音提琴手,因此将从小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舟舟带在身边,舟舟就这样和乐团一起生活。张以庆回忆他初识舟舟时,是乐团最低谷的时候,只发60%的工资,排练时小提琴手们拉60%的音符,管乐手们吹半口气,“只有舟舟永远是饱满的,那种生命的饱满,所以让我特别震撼”。《起程,将远行》拍完后的一年里,舟舟的样子在张以庆脑子里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舟舟的世界》。
张以庆用了七个月在武汉乐团观察和拍摄。拍摄临近尾声时,武汉乐团常任指挥梅笃信为了让摄制组尽快收工,刻意制造了“一个小高潮”,在摄像机镜头前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舟舟。舟舟在众人的欢呼和欢笑声中指挥乐团演奏了《卡门》。尽人皆知,这组镜头后来彻底改变了舟舟的命运,这是后话。
当时张以庆为了这部片子拍了足足2100多分钟素材,70多盘录像带,然后又花了五个月制作。初剪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骑上自行车环武汉东湖一圈,然后回去写解说词,但每天只写一句。
张以庆告诉我,《舟舟的世界》拍的重点不是舟舟,而是通过讲述健全人对待唐氏综合征患者的方式,来展现健全人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其中人与人的普遍关系。“其实舟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把他作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
以前,张以庆听到有人在看片子时说,这傻子挺好玩的,就浑身来气。现在他想通了:如果人们因为了解了舟舟,走在街上碰到弱智人,眼神变得柔和一些,态度变得友善一些,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舟舟是幸运的,他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长大,他的家人,武汉音乐团的乐手,甚至每次无偿给他食物饮料的武汉商场员工,都在温暖地照顾着他。这一点张以庆与舟舟也是相似的。
1986年湖北电视台编导景高地在家中见到来访的张以庆时,后者只是一名武汉手表厂的工人。那时的张以庆32岁,在工厂干了10年,开过机床,看过仓库,主持过黑板报,因为对文字敏感,10年中他渐渐由工人演变成宣传干事,在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手表厂计划自费拍一部宣传片,请了湖北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原本只负责写旁白的张以庆却机缘巧合地兼任了导演。那次经历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导演上的天赋要远远高于写作,外加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他开始“不安分”了。
张以庆写了部纪录片的脚本,找到当年拍手表厂广告时认识的景高地。为了让对方印象深刻,张以庆拿着脚本连唱带说地“演”了一遍。后来成为湖北电视台副台长的景高地如今依然记得当时的印象:“那是一部拍武汉少年宫合唱团的片子。当时的纪录片都要讲怎么克服困难,怎么艰苦锻炼,怎么最后成才,但他的脚本完全不同,是通过一个孩子的内心独白来讲合唱团里的点滴感触,通过一些气氛来烘托这么一件事,我听了很感动。”
就这样,在景高地的帮助下,张以庆被“借调”到了湖北电视台,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童年,七彩的歌》,进而顺利转入电视台系统,成了湖北电视台青少部的一名员工。手表厂工人的命运就此改写,但张以庆后来却越来越发现,电视台的工作和手表厂差不多,每天写解说词,策划常规少儿节目拍摄,他又觉得压抑了。
转机来自于《红地毯上的日记》。张以庆偶然间看到了湖北艺术体操队的训练。为了控制孩子们的体脂,体操队教练只允许孩子们吃肉和菜而几乎没有主食,为了控制女孩发育,甚至不让她们多喝水,家里来信需要检查,一年只有四天假期,连教练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张以庆觉得这么好的题材,如果只把体操队请到青少部节目组拍个六一儿童节晚会就太可惜了,应该拍个专题片。
但张以庆没有资格将台里的摄像机借出来拍非常规的题材。于是他就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三年。好在他“随时去,这些孩子像植物一样长在红地毯上,永远在那”。这三年里,每周日,他骑着自行车去体操队训练馆,在那里看一天,为拍摄做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连“什么季节的几点几分阳光会落在红地毯上的什么位置我都清楚”。
1990年,機会终于来了,他找来专题部的摄像师,又从台里借了摄像机,花了400块钱,拍了三天半。已经观察了三年光线,但真正拍摄的时候张以庆又傻了,因为连续三天阴天,他说那是磨炼他耐心的代价。
《红地毯上的日记》获得了当时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最高政府奖项金童奖,也改变了张以庆在湖北电视台里的地位。
他被调到纪录片组,并得到了台里领导们的特殊照顾——完全的创作自由,不需要报选题,不需要被规定在多长时间内交一条片子。“我30年来,没有做过一部领导交办的片子。”此后他接连拍出《起程,将远行》《导演》,以及《舟舟的世界》。
当然,这份体制内的自由也曾引起过别人向领导抱怨,领导只回一句:“你们谁能再拍出个《舟舟的世界》来,你们谁都可以像张以庆一样。”
《舟舟的世界》彻底改变了张以庆的命运。除了片子入选中国电视金鹰奖、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艺术电影节,湖北电视台更是完全将《舟舟的世界》作为模本,有人保持着每两周看一次的记录,有人甚至连这个镜头紧接着的下个镜头是什么都了然于胸。
这部纪录片也彻底改变了舟舟的命运。1998年末,当时中国残联的理事长偶然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舟舟的世界》,激动之余立刻打电话到武汉找到舟舟,邀请他参加1999年残联的新春晚会。在北京保利剧场,舟舟指挥中央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做了一场演出。由此舟舟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被冠以“天才指挥家”名号。从1999年到2006年,舟舟出访五国三大洲,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会城市,被中央领导接见,与施瓦辛格、刘德华同台。2000年,在世界顶级的卡耐基音乐厅,舟舟指挥美国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出,被视为他一生的顶峰。
成名后的舟舟并不完全给张以庆面子,有时候,当着众人,舟舟拒绝跟张以庆握手。所有人都认为是张以庆改变了舟舟的命运,但舟舟就是舟舟。
张以庆说他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舟舟了。今年5月《新京报》刊登了一篇有关舟舟的最新报道,如今已经40岁的舟舟从巅峰时每年168场演出至现在不足10场,所在的残疾人艺术团也已经有大半年没给他发工资了。张以庆说:“始终会有媒体采访我提到舟舟,我说你们需要再思考一步,你们老把他当明星来说事,认为他是天才。但如果一名唐氏综合征患者能一直有商业价值,那说明这个社会是有病的。我当时拍舟舟,是希望正常人看到舟舟之后病能好点。”
采访过程中,张以庆经常会半开玩笑地称自己真的很像舟舟。他说他像舟舟一样只爱吃肉;在各个高校纪录片放映现场,设备不够好就会当场生气;他还说他受不了批评,一挨说就垂头丧气。
他拍舟舟,拍出的是他自己某方面的偏执和障碍,而拍英和白,则拍出了他自己的孤独。“我这人一辈子活了别人八辈子,因为我可以在别人的世界里感受那些感受,这让我觉得太奢侈了。”

纪录片《君紫檀》剧照
幼儿园
《英和白》让张以庆发泄着孤独感,但正是这种拍摄方式,让他陷入了抑郁症。他也曾想通过拍新片来治疗。《英和白》之后,他开始为《幼儿园》的拍摄做准备。
张以庆的最初设想是,从人之初性本善的角度出发,用孩子的天真纯洁去洗涤和净化成人的内心。此外幼儿园里无忧无虑,他想着每天拍拍干净又快乐的孩子们,可以过一阵没有压力的日子。
可到了幼儿园,孩子们的种种行为出乎他的意料。孩子们撒谎、欺负别人、打架,其中有仇恨、嫉妒,也有自私,孩子们的哭泣取代了想象中的欢笑。老师问孩子:你这么大个儿,你怎么长高的?孩子张嘴就说: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老师们的养育下长这么高的。
所有的预设都被推倒了。张以庆有些不知所措,他说自己在不知道要拍什么之前,必须学会不拍什么。于是他决定不拍老师讲故事,不拍孩子们做游戏,不拍唱歌,不拍画画,不拍六一儿童节。他认为像这些节日,都是成人按他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先排练两个月,再跳集体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快乐的,其实他们是痛苦的。还有其他导演都会拍的,比如老师,他也基本不拍。
最终他拍摄到的5000多分钟素材清晰地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今天孩子们面对的这个社会跟成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被公共媒体影响并渗透,一切成人社会所涉及的诸如生存意识、文化冲突、社会地位、权势、金钱、婚姻、战争,无一不在孩子们的生活和话语里投射出来。在镜头前,孩子们会攀比自己父母的工作,说如果收了钱会分给领导一份,他们谈到爱时很腼腆,但谈到恨时,会说自己四岁时就恨日本人恨得流鼻血,以后要当科学家造坦克,造出坦克打日本人。
选择拍幼儿园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初《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张以庆的纪录片摆拍痕迹太重,并不是真正客观地记录,而是主观地融入了很多导演的理解。不服气的张以庆要拍一部写实的片子,由于孩子们的可爱和小狡猾都在一瞬之间,于是《幼儿园》中的所有镜头都是抓拍。但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剪辑成了更大的挑战,5000多分钟的素材全是碎片化的,完全没有线性逻辑。张以庆看一遍素材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看了三遍半,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把素材放了足足一年没有动,那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年后他重新拾起素材,用了半年时间,剪辑成了69分钟的片子。两位园长、三位班主任,还有纪录片中每周末最迟来接走孩子的那位母亲,都看到了片子。园方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张以庆说,面对现实确实不容易,但你总得对几十年后负责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些孩子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再看这部片子时的感觉,因为我们想表达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这个社会共性的东西。那位母亲也在电视台工作,看了片子以后,她说她想过来和张以庆一起拍纪录片。
《幼儿园》获奖无数,但原本打算通过它来治疗自己的张以庆,抑郁症病情反而加重了。2004年之后,他给了自己10年“留白”。“重复自己,重复别人干过的事情,我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我就不干了,这样节约了资源也节约了自己。”
“匠心”
在之后的10年中,张以庆说,老伴对他治疗抑郁症帮助最大。他们如今相识11年了,依然没有结婚,两人分别独立生活,每周末见面,每天打一小时电话聊天。他在欢乐的时候她很冷静,他在抑郁的时候她也很冷静,她会把他的病当作正常状态。“圈内都知道张以庆是一个特别无法驾驭的人,你别挨近了,近了可能会受伤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处。但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我的幽默她全懂,你会觉得有个人在身边一直默默给你鼓掌。”
10年中,张以庆接到的拍摄邀约无数。让张以庆决定正式复出的选题始自一次偶然的邀请。当时投资方已经把钱准备到位,想请他拍摄一部关于紫檀家具传奇大师顾永琦的传记纪录片。张以庆一听“传奇”两个字就没了兴趣,“我听得都烦透,我不喜欢传奇”。但邀约依然有吸引力,他开玩笑说,当时打算带上老伴应邀去顾永琦所在的南通看看,“就当走个过场,好吃好喝去玩一趟”。
当张以庆触摸到顾永琦细致的紫檀家具之后,他却很快同意拍摄,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拉上台里一直以来和他共事的出资人王琼、曹海英作为该片共同投资方。于是这也就成了60岁的张以庆的退休之作。
张以庆10年后再回到纪录片拍摄,其实这个领域里的很多东西都变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东方时空》风格的“记录老百姓的生活”淡出了。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人们开始以宏大的文案策划、精美的镜头和抒情的文本讲述,来记录美食,记录故宫,记录中国传统文化。《君紫檀》开拍前,投资方对张以庆说,希望他能拍得像当时很火的日本纪录片《寿司之神》一样。
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看来,尽管《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热让从业者惊呼纪录片的春天甚至夏天来了,但实际上纪录片从来不是大众传播的主流,在电视台体制内,它依然排在电视剧、综艺节目和新闻之后,是最后一类。
而湖北卫视原总监景高地也认为一部纪录片的走红与创作者并无太大关系,更多是与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空间和认知有关。当年《话说长江》能火,是因为人口无法流动,人们不能到处行走。而后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了,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时候,《河殇》出现了。《河殇》之后再次出现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就要等到24年后《舌尖上的中国》,“情怀”和“匠心”成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担心张以庆这部新片会拍成高级广告片,充其量是个民营企业家的好人好事。但张以庆关注的点不在此,他决心通过纪录片拍出紫檀家具的“触觉”。
他一改《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的风格,去掉了以往作品中的线性叙事和强烈的冲突感,拍摄对象也不再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取而代之的是光影、唯美的画面、悠扬平缓的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洋歌剧配乐。他请京剧名家关栋天在鏡头前唱《短歌行》,让张婷唱《望江亭》,王彩云拉京胡,还有昆曲、评弹、古琴,他还请了文化名人陈丹青、邓雪松、张永和来采访顾永琦,他甚至自己出镜来与顾永琦对谈。
这种风格的改变,既是导演沉寂10年后寻求突破自我,也可以理解为张以庆逐渐走出抑郁症,与社会重新发生连接的过程。
10月底,张以庆带着新片《君紫檀》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接连进行了三天展映和研讨会,参与讨论的嘉宾从电视台总编到资深导演,从高校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到新闻学院院长,大都是十几年前曾与他共事过的同行。人们夸赞他的新片的理想主义气质,“代表了一代人对英雄主义的一种追求”。讨论会后半段的话题也谈到了张以庆的抑郁症,有人说他的病是因为“感受力太强了,太敏感了,而高度工业化社会不适于这样的人生存,你要麻木一些才活得快乐”。也有人说,只有“像张以庆这样的疯子”,才会拍出如此极致的东西。
我在采访中问他,《君紫檀》会是封山之作吗?他回答说:“一个人是有天花板的。我60岁使劲儿往上冲,一个人的经历、力气、灵气,是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