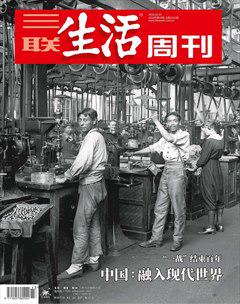通往参战之路:北洋政府的危机与转机
刘怡
27岁这一年,伍朝枢终于体会到了父亲伍廷芳在前清时代为李鸿章参谋外事谈判时的心理感受:沮丧,苦恼,但又不得不为之。更令他郁闷的是,抛出这道难题的,正是19年前令父亲名誉蒙羞的同一个国家。

1918年11月13日,在西什库天主堂出席终战庆典的“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中)。绰号“梁财神”的梁士诒对中国参加大战曾发挥过关键作用
时间是1914年9月2日深夜,中华民国政府的8位内阁总长,政事堂国务卿(国务总理)徐世昌和左右丞、副总统黎元洪,总统府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税务处督办梁士诒以及几位书记官围坐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的澄怀堂办公室,焦虑地等待着大总统袁世凯的问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年纪在50岁左右,早在前清时代就已经身居高位并且彼此熟识,但对如此棘手的情形依旧一筹莫展。或许是考虑到僚属们的困境,三位年纪尚轻但通晓国际事务的政事堂参议被紧急召来,安排在会议桌的下首,以便随时提供咨询。他们是33岁的早稻田大学法学学士、安徽人金邦平,26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担任过大总统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以及前清驻美公使伍廷芳之子、剑桥大学法学硕士和英国法学协会会员伍朝枢,分别对应与中国外交关联最为紧密的日、美、英三国。回想1895年,伍廷芳曾经以中国代表团一等参赞的身份随李鸿章赴日,亲身参与了耻辱性的《马关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这位毕生自豪于自己的法律专業主义、此时正在上海安然过寓公生活的老人并不曾料想到,当年困扰过自己的日本威胁,时隔不到20年便再次逼近了下一代中国人。
身材矮小壮硕的袁世凯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当天传来的突发消息: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通报,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先头部队已于9月1日深夜在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登陆,对德国在华的海军基地胶州湾租借地展开包抄进攻。日方同时还暗示,基于军事行动需要,将对德方控制的胶济铁路全线以及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济南实施占领。尽管自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以来,战端骤开的可能性便已出现在中国政府要人们的预期内,但日方竟早于事前公布的最后期限9月15日展开军事行动,并公然无视中国政府在8月6日照会的《局外中立条规24条》,在胶州湾以外的龙口地区实施入侵,依旧令众人感到猝不及防。作为专业人士,顾维钧和伍朝枢给出了基于国际法准则的反馈意见:既然中国已经决心对欧洲大战置身世外、严守中立,就必须以严厉的姿态应对日方破坏中立的行径。中方应立即向山东半岛调兵,坚决抵制日军肆无忌惮的侵入。
然而这毕竟只是年轻书生的热血之见。几分钟后,陆军总长段祺瑞就给出了令人沮丧的答复:受装备差距,弹药匮乏和后勤、运输能力不足所限,即使中国军队在山东只部署最低限度的正面防御,也仅能抵挡日军约48小时,随后便难以为继。届时中日双方已处在准战争状态,局面将更不易收梢。袁世凯的亲家、外交总长孙宝琦则以沉默给出了暗示:对如何处理“武力保卫中立”这一无任何先例可循的命题,他本人全无头绪。长久的沉默之后,仍是袁世凯本人做出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效仿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旧例,将胶济铁路潍县车站以东,龙口、莱州以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划为日德两国“交战区”,撤出驻扎在其间的中国驻军,潍县以西则仍为中国中立区。9月3日,此项决定被通报给了在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节。
当年日俄战争爆发之时,袁世凯已是权倾朝野的清廷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领全国大半新式军队。他当然知晓:所谓“局外中立”的安排,从一开始起就是废纸一张。日俄双方实际的冲突范围,很快就突破了清廷划定的“交战区”边界;双方强征中国民夫、捣毁中方民政机关、劫掠财富以及残害平民之举,更是贯穿于战争始终。以此类推,指望以一项事后追认的声明限制1914年的日军在山东的行动,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事实也的确如此: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车站之后,并未即时东进、尽快攻下德军盘踞的青岛和胶州湾,而是继续发兵西扰,将青州、济南等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和周边矿山、公路一概收入囊中,甚至设立临时管理机构,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准殖民统治。当年11月青岛被最终攻克之后,中方向日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鉴于战事已毕、“交战区”在事实上丧失效力,日方应尽快安排从山东撤军。但对方完全不予理睬。

1955年11月2日,一名6岁女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墓地悼念安葬于其中的“一战”战殁者。十字架上装饰有终战日的著名标志物“悼亡虞美人”
继续推进一项明知无法奏效的外交政策,反映的是袁世凯此际万般纠结的心理状态。他曾经悲观地告诉顾维钧,尽管国际法的“理”似乎指出了中国在奉行中立政策时本应享有的权利,但亚洲大局的“势”和中国本身缺乏“力”的困境迫使政府只能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向日本的胁迫低头。另一项不便启齿的原因是:在扑灭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并颁行了新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后,袁世凯本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尽早实现“改变国体”、帝制自为的内政问题上,殊不愿这一良机为外交上的纷扰所阻断。顾维钧日后回忆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既然在国体问题上的倾向已经愈发复古,则在外交事务上对前清萧规曹随,在袁氏眼中也就不再成为大问题。
但并非所有人都怀抱类似的看法。就在日军占领青岛之后不久,参加了9月2日中南海会议的伍朝枢、梁士诒以及前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同时萌生出了交结英国和其他协约国要角,以化解来自日本的安全压力的想法。驻美公使夏偕复则建议中国以中立之身调停欧洲战事,通过缔造新的和平来改善自己的外部处境。通过使中国问题由中日双边架构变为国际化,特别是借由欧洲大战的时势、实现中国外交局面的改观,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外交家的共识,并着手付诸实施。尽管此时距离中国实际参战,还有整整两年半的间隔。

1919年6月3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在北京街头
神父外长的课题
即使是在百事一新、异象频生的民国政坛上,陆徵祥依然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作为平民家庭出身的外交干才,他的道德观念和行事法则曾颇受身为新教传教士的父亲的影响。40岁那年,陆徵祥改宗罗马天主教,嗣后虔诚之心愈发炽烈,最终竟在57岁的盛年退出政坛,以比利时天主教本笃会神父的身份在异域度过了余生。他也是清末外交官中最早与欧洲女性缔结新式婚姻的少数几人之一,通晓俄、法两门外语。这样一位背景特殊的人士,得以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崭露头角,正是此际中国日益与世界接轨的缩影。
晚年的陆徵祥反思平生功过,曾经留下过一句振聋发聩的遗教:“弱国无外交。”不可谓不沉痛。但在他本人亲历的大部分政治活动中,恰恰是要为中国这一弱国谋外交,以外交策略的得分弥补中国军事、经济硬实力上的缺陷。庚子之变前后,陆徵祥曾随前清洋务重臣许景澄、杨儒办理对俄外交,深知中国边疆危机之险恶与盲目排外之无益,更对清末新旧混杂、外交决策完全系于个人之身的旧体制抱有极深的个人看法。辛亥革命之后,南北两政府于1912年实现合并,袁世凯有意延揽一位与同盟会素无渊源、又能外于官场老迈恶习的新人物出掌外交部。陆徵祥遂从驻俄国公使任内被召回北京,成为北洋政府外交事务的主要掌舵者。
作为北京官场中的外来者,陆徵祥的最大贡献,在于迅速实现了中国外交系统的专业化和独立化。归国之前,他即正告袁世凯:在他本人主持外交部期间,既不向其他部会推荐官员候选人,也拒不接受其他部会对人事安排的置喙。1912年10月他上任后不久,即参考法国制度草拟了《外交部组织章程》,设立一厅四室的固定编制,将全部在京办事人员压缩到100人以下。在选拔和任命新官员时,他要求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的考试,不以籍贯为依据,原则上要求至少通晓一门外语。前清时代,驻外使节大多加有钦差衔,可直接向皇帝上奏,对使馆事务也近乎一人包办。而陆徵祥要求将所有驻外使领馆人员逐步替换为专业外交人员,仅对总长负责,组建了一套责任明确、人员精干的职业外交家班底。整个外交部系统除去总长为特任官,须随内阁更迭变换人选外,其余次长、参事、公使、领事等皆为简任官,职务变化不甚频繁。这使得外交官群体在民国初年变动频仍的政局中,始终得以保持稳定,能够持之以恒地推行为中国争取平等地位的外部目标。
陆徵祥晚年曾感慨:“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绝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我那时培植60余青年,我绝不用私人,只选择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专业外交人才。”在1912~1920年他执掌外交部期间,外交系统办事人员具有留学经历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前清遗留的老迈庶务人员则被大刀阔斧地裁汰。伍朝枢、顾维钧等年轻留学生能以未及而立之身与闻机要,参与最高决策,与陆徵祥的倡导关联甚大。甚至到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北洋时代的外交官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南京政府所留用。

1935年青岛街头一景。“一战”爆发后,日本出兵占领原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海军基地,直至1922年底方才交还给中国
此举当然不是为了自矜己才,而是鼎革之际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勢复杂性使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英俄两国乘机策动西藏和外蒙古谋求独立。在随后展开的关乎宗主权(外蒙古)和边界划定(西藏)的一系列谈判中,痛感前清遗留的条约体系淆乱不堪,在观念和细节上都存在莫大的差池。有鉴于此,陆徵祥在外交部设立了“条约研究会”和参事室,延揽一批常备的国际法人才,细致研究前清遗留条约的漏洞和国际法学界的新动向,以为最高决策提供咨询。1912年12月,外交部还组建了定期集中议事的“保和会准备会”,名义上是为派团出席1915年第三届海牙和平会议(当时称“保和会”,后因大战爆发而取消)做前期筹划,实则已经开始整理基于中国本身利益诉求的国际法提案,希望借助未来的大会予以公开和实现。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一战”关系研究专家徐国琦认为:在1914年前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外交才俊、言论精英、工商业人士以及知识分子思考群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群体”。他们秉持一种建立在世界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理念,对旧文化、旧秩序和旧的国家认同发起了公开挑战,希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也是这个群体,最早觉知到了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的潜在机会——1914年8月17日,外交部秘书刘符诚就青岛战事问题前往东交民巷拜会法国公使康悌(Alexandre-Robert Conty),后者提及:待将来战事平定,各国必有一大会议,届时中国应设法取得列席资格,如此方可使本国问题不由外人决断。
康悌所透露的关于战后和会的消息,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群体”第一次窥见国际秩序即将迎来决定性的重构。伍朝枢率先就此发声,11月7日,他向袁世凯呈上说帖,建议中国拒绝单独与日本就山东问题展开谈判,而要将协约国领袖之一英国拉入其中,举行中英日三方交涉。如若不遂,亦可将中日争端付诸战后召开的“国际公会”,借他国之力来挽回损失。10月31日,陆徵祥在保和会准备会第52次会议上提出:日本以武力夺取德国在华租借地,属于国际法上并无先例的新问题。鉴于战后和会必就此争端做出裁决,中国应当尽快着手研究既有法条并撰写相关论文,以为合法收回山东主权做出准备。然而短短两个月之后,这位神父外长就开始缺席随后的讨论,因为袁世凯给他安排了一项一言难尽的新工作——主持对日双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