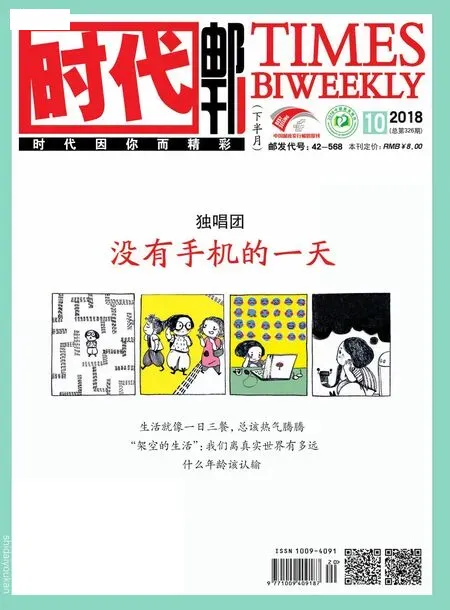广场舞大妈:她们的孤独你不懂

梳洗打扮、绾起发髻,换上白净的运动服,只有每天傍晚,华灯初上,广场舞的音乐响起,62岁的何慧芳才觉得找回了自己。
从学校接回上小学的孙子,为开出租车的儿子和在商场卖货的儿媳煮好饭菜,收拾好翌日早餐的食材,把客厅的地板拖干净,收拾好晾干的衣服……在整个白天10多个小时的忙碌后,她给自己挤出了一点点属于私人的时间。
离家不远的广州市天河区棠徳路,是岭南民间广场舞的大秀场。这条20米宽的小区主路,两侧甘棠、棕榈树林立。一到傍晚,从南走到北,健身操、交谊舞、太极拳、扇子舞、健美操、恰恰舞甚至武术刀剑拳法齐齐上演,上千人的广场舞队伍更绵延近一公里长,所有的音响齐鸣,咿呀啁啾,热闹非凡。
何慧芳是这条人海长龙中的一员。这支30多人的队伍,跳的是健身操,高亢动感的音乐响起,她们手脚随着音乐摇摆,整齐划一,看不出每个人的特色,“整齐就是好看,跳得不一样不就乱了?”
“人多了,就不害怕了”
10多年来,棠徳路一直是舞者的乐园。在这里跳舞的人,不少是来自河南、湖北、四川的老人,她们的子女早些年在广州打拼,如今在广州买房结婚生子,老人们被子女接来,照顾孙辈。
来自河南南阳的何慧芳,儿子在广州开了10多年出租车。两年前,老伴得病去世,儿子把她从老家接到广州,方便照顾。“儿子儿媳都上班,我接孙子上学,给他们做做饭。”何慧芳说。
初到广州时,母子之间时常爆发“战争”。儿子觉得把母亲接过来是享福,但北方人何慧芳并不习惯这里,虽然“冬天能看到树开花觉得稀奇”,但跟广州人言语不通,常年没有说话的伴儿,让她十分怀念在老家晒太阳聊天的小姐妹。
年轻时,何慧芳是当地纺织厂的一名女工,习惯了人群扎堆的生活,和姐妹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做工、一起吃食堂、一起看电影。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厂里元旦文艺会演,她参加了压轴节目,第一次登台和姐妹儿们演出大合唱,激动得一夜合不拢眼。
“我们要当革命的螺丝钉,但谁不想当大红花。”何慧芳说,她曾私下打听过县里的文化演出队,想进去当演员,怯生生地问了一圈儿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纠结着、挣扎着,后来便下岗了。后来她推着车子卖炸串,扎在小商贩中间,“被城管撵着跑”。
刚到广州,她听收音机,听不懂,看电视,没意思,老觉着不得劲儿,下楼上楼,在小区里一趟趟地转。“楼下那么多跳舞的,要不你也去跳跳舞?”儿子劝她。
马路上跳舞,一群人围着瞅,何慧芳有点难为情,直到遇见一个慢慢熟络的河南老乡,老乡拉着她,一起报名进了健身操团队,学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无师自通,“就跟大合唱一样,人多了,就不害怕了,这么多人一起跳,观众不一定在看你。”
现在,何慧芳的健身舞已经跳了一年多,舞蹈和做饭、看孩子一样,成了日常不可缺少的部分。
借助广场舞,她正一点点甩掉孤独。她结识了同是来看孩子的老乡,开始和听不懂在说啥的湛江生意人交朋友。
这段时间,手机微信也装上了,主要功能是跟舞友们聊天,“感觉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
“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种幸福”
和何慧芳一样,数量庞大的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成为全民关注、争议的焦点。公开资料显示,这一群体的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

在抗议者看来,她们是“噪音扰民”和“挤占公共空间”的代名词。广场舞大妈们的舞姿既不美好,又缺乏公共道德,无疑要遭到年轻人一致的嘲笑。
但在研究者看来,这隐藏着更多的社会基因。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王芊霓曾专门到何慧芳的河南老家,历时半年进行田野调查。她接触了6支广场舞队,和20多位舞者进行深入访谈,亲自加入广场舞团队,试图揭示其背后争议的逻辑,“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不符合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的期望,二是广场舞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合乎现代人对公共空间安静有序的期待。”
何慧芳曾遇到反对大妈们跳舞的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大声斥责音响让他们不能睡觉,“我们也理解年轻人,上班累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在晚上的饭点跳。”何慧芳说。争吵的时候,几十个大妈七嘴八舌,“我们辛苦了一辈子,照顾老照顾小,老了跳个舞都不行?”年轻人悻悻离开。
也有大妈们败下阵来的时候。春节回河南老家,何慧芳组织过一群同龄人跳广场舞,“有人嫌吵,左邻右舍都认识,跳了一两次就不再跳了。”
有时候晚上跳不过瘾,早晨7点多,何慧芳给儿孙做好早饭,下楼跟舞友再跳一两个小时。她们专门买了音量小的随身听,别在腰上,跳完舞再结伴逛菜市场,给孩子们准备晚饭。
王芊霓把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独自一人在家,她们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外地就读”。
“促使女性去参加广场舞的具体原因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孤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广场舞正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这些女人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心灵按摩。”这名研究者得出结论。
步入暮年的何慧芳,对此深有感触,“年轻人怕吵,老年人怕不吵,怕一个人在家,怕没动静,你现在理解不了,等你老了,就知道有人吵也是一种幸福。”她说,她打算把广场舞活到老,跳到老,开心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