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演讲: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我是老大。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一顿打,让我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我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但新鞋让我走路特别艰难。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要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我就被确定将来要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家里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账就行了。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一两千考生,县立中学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的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要我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此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内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为我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这才让上了中学。
既然上了学,家里也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还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我还要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时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过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然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些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了一些东西,自尊心就建立起来了。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在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1973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后到《延河》编辑部工作,一直到1982年,我才开始专业创作。
03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时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大多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那时侯我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我的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
业余时间,我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包括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当时,好些文章中的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古代就不是这样。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那时,我在写作上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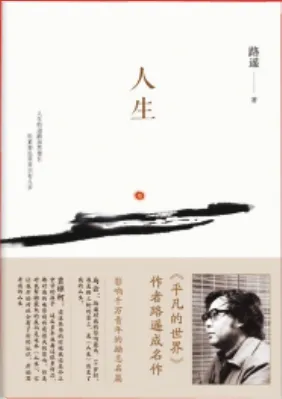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电话、电报接踵而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要求改编。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遇到困难时,就会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我知道,我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作为严肃的问题摆到面前。在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到困难会很大。
首先是漫长的过程,意味着我要在文坛上消失很长时间,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葬送了自己。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我到了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我做了大量的准备,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创作的精神状态,我不想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因此,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05
《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反映了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故事可以编,但要有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为此,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首先,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个房子,一天一天地翻看、做笔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还要细细看,譬如我经常去一个烧砖厂,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我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每当我看见桌子,就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做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没办法,眼里涌出热辣辣的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子,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看病,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里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西安待不下去了,我回到了陕北,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崩溃了。回到榆林,熟悉的人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给我,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说这是吃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休息了一年,接着写第三部。1988年5月份,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这时,X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要求最晚在6月初将第三部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第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可我只能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了一桌饭等着庆贺我。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就开始痉挛,连笔都拿不住,怎么办?
我把开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扔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写完后,我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到六年前自己的样子,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我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的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是一行一行的,很美。这就是审美!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