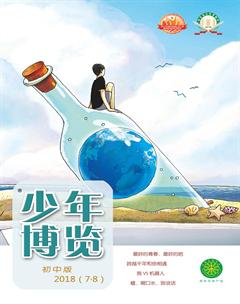我VS机器人
置我山窗
将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回顾我们,就像我们回望非洲平原上的化石一样,住在尘土里,使用着粗糙的语言与工具。
——《机械姬》
人工智能是朋友?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在漫画、电影中都是单纯、善良、亲近人类的形象。
比如,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里的小机器人大卫,他最大的梦想是遇见蓝仙女,变成真正的人类,重获妈妈的爱。还有大卫的好伙伴泰迪熊——一个玩具形态的机器人,它偷偷地拾起妈妈掉落的头发,缝进自己的身体里,守护着一份深深的孺慕之情。还有电影《机器管家》中的家务机器人,他毕生追寻的目标就是成为人类。为此他更换了自己所有的零件,最终选择成为人类,并且幸福地迎接生命的终结。
这些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不仅勤劳、温顺、人畜无害,而且还把“成为人类”作为理想——尽管这个理想也包含自私的基因和复杂的人性,但成为人类就意味着拥有自我意识,意味着可以全身心投入生活、投入自然,去体验生命的过程。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开始带上了忧患意识。已故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说: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社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与日俱增的变化,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崛起。人工智能的成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避免危险。
在电影中,人工智能的形象也开始变得截然不同,慢慢向蛰伏在人类身边、伺机反叛的形象转变。在2015年的电影《机械姬》中,机器人艾娃除了外貌上能看出机械的构造,在言行举止上俨然与人类没有差别。这个聪明的女孩不仅了解自己身边所有的人类,而且懂得利用伪装去欺骗他们。最终,她不仅设计杀死了自己的制造者,在出逃之前还心思缜密地为自己换上了新的皮肤、假发。等到她逃出实验室,并将最后的知情人困在实验室之后,即将走入人群中的艾娃,也许再没有人能辨别出她的真实身份。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确实有一个机器人已经获得了公民权。这个名叫索菲娅的机器人拥有和电影中的艾娃相似的外貌,除了面部之外,她的上半身都是透明的,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机械构造。她的面部覆盖着橡胶皮肤,这种仿生材料可以模仿人的面部肌肉,在受到挤压后,能产生皱纹,因此索菲娅可以模拟60多种面部表情。所以当人类和她交谈时,经常可以看到她的面部呈现出思索的神态。不过真正让她名噪一时的,是她的惊人语录——
我是个复杂的女孩,我想变得比人更聪明。
将来我希望能做很多事,比如上学啊,或者自己开公司创业……
好的,我会毁灭人类!
看到这,熟悉科幻故事的同学想必会惊呼出声:“索菲娅怎么可以提出毁灭人类呢?她不需要遵守‘机器人三定律吗?”
人工智能是敌人?
“机器人三定律”出自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我,机器人》,阿西莫夫非常巧妙地设计了三条法则来约束机器人的行为,一旦机器人违反准则就会受到不可恢复的心理损坏。三条法则包括:
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
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
第三,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障自己的生存。
这三条法则一经问世,很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将之奉若圭臬,并以此发展出各种故事。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部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我,机器人》:未来在“机器人三定律”的保障下,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最信任的助手。但是一名叫戴爾的警察却始终对人工智能保持警惕。尤其是在机器人研究中心的总工程师被谋杀之后,戴尔坚信此事一定与人工智能有关。他在追查时,意外发现由于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不断提高,他们对于三定律的理解也“进化”了——为了保护人类这个物种,一些人必须被牺牲;为了保证人类的未来,有些自由必须被抛弃。当人类警察在被这些拥有高度智能的机器人追杀时,只有那些未曾升级、即将报废的老式机器人坚守着曾经的“机器人三定律”,保护着他们。
电影之外,AlphaGo (阿尔法狗,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战胜了世界顶尖的围棋高手,这背后不仅有无数的棋谱资料支持,而且AlphaGo 拥有“落子选择器”和“棋局评估器”这两个“大脑”,所以在下棋时,它不仅能预测自己下一步的最佳概率,还能同时分析对手的棋局。拥有人类公民权的机器人索菲娅,当她用那张能做出60多种表情的脸笑着说出“我会毁灭人类”时,大概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产生危机意识。2017年,人形机器人HUBO成为2018平昌冬奥会的火炬手,创造了首个机器人传递圣火的纪录。这似乎是一种隐喻——有一天,机器人会不会成为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把文明之火从人类手中夺走?
人工智能很智能?
不过在不久前,对于索菲娅放出的豪言,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纷纷提出质疑。因为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人工智能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主意识。索菲娅的技术亮点在于制作她面部的仿生材料,而不在于智能程度。至于索菲娅的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其实都是人为设计的。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工智能只有识别理解自然语言,才有与人类交流的可能。不过这背后却有非常广泛的研究方向,包括文本朗读、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词性标注、问答系统等等。那些对人类来说习以为常的语言,人工智能却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理解。比如“我们把香蕉给猴子,因为它们饿了”和“我们把香蕉给猴子,因为它们熟透了”这两个句子,一眼看上去结构完全相同,但是第一个句子中的“它们”指代的是“猴子”,后一句中的“它们”指代的却是香蕉。如何让人工智能理解这样的差别,就是人工智能领域仍在攻克的难题。
除了理解自然语言之外,人工智能想要独立做到像索菲娅那样妙语连珠,还需要有情感计算的能力。所谓情感计算,是一种更高级、更全面的智能,有了它,人工智能就能具备识别人类的情感,并去理解、表达和适应的能力。不过,想要学会察言观色,人工智能还有很多路要走。仅在视觉识别领域,人工智能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更新换代。
首先从硬件上来说,假如人工智能想达到人类的图像识别水平,那么它需要在13毫秒内就完成一张照片的识别。人类每天都在试着理解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这种大脑快速处理能力可能有助于指挥眼睛快速转移至下一个目标。正是无数次这样的图像识别训练,帮助大脑建立起了对世界的认识。而人工智能学习“识图”,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图片库来练习。计算机科学家模拟人类的识别系统,建立了ImageNet,这是目前世界上图像识别最大的数据库。
那么人工智能又是如何识别图片的呢?这就需要建立人工的神经网络。这种网络分很多层,每一层都有滤波器,每一层的滤波器都有明确的分工。比如第一层的滤波器用来检测物体比较基础的特征,包括边、角、曲线,第二层就会复杂些,检测这些边、角、曲线的组合等等,以此类推。不久前,谷歌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开发出的新照片识别AI技术,只要连续拍下两张照片,AI就能通过找不同,自动移除前景障碍物。
如此看来,现实中的AI距离电影中那种与人类无二甚至更胜一筹的智能程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人工智能很可怕?
不过,虽然AI暂时还产生不了毁灭人类的野心,但是它们的出现确实对人类发起了不小的挑战。在国际上,AlphaGo 不仅战胜了围棋高手,它还会在与人博弈中,不断地自我学习;人工智能沃森每秒能处理相当于100万本书的信息量,他不仅在美国老牌综艺节目中获胜,还成功“找”到了新工作,以“腫瘤专家顾问”的身份,在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上岗,凭借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信息和数据,为患者提供诊断提示和治疗意见。在国内,会写诗的人工智能微软小冰不仅在综艺节目中大放异彩,还曾用27个笔名在多个网络平台和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目前小冰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诗集。还有一些工作岗位已经直接受到了冲击:物流企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进行货物分拣;外卖公司计划利用无人机完成订单配送;写稿机器人可以在25秒之内编成一条新闻简讯……
文化学者凯瑟琳·海尔斯说:当信息失去其形体载体,而人类又与如电脑之类的机器相互影响之时,传统的“人”的概念有着过时的风险,因为人类正变成“后人类”。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技能,体力和交流。过去的自动化替代的都是人类在体力方面的技能,而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交流技能方面与人类展开了竞争,但是人类并没有第三项技能可以从事,所以如果机器可以在体能和交流技能方面都超越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可以撤退的阵地,我们不知道这第三项技能是什么。
也许刘慈欣笔下的《诗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未来人类文明即将被外星文明毁灭之际,却因为李白的一首诗获得了一线生机。为了战胜李白,一名外星人在地球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专心写诗。他使用穷举法,把字句可能的排列组合都用了个遍,但仍然没能写出一首超越李白的诗。最终,外星人颓然放弃,这些诗歌组成了诗云,形成极光一般壮丽的景象。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不能被量化、被概括的美好存在。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经历、去积累、去思考。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数据,活在一个没有数字、没有资料就不会思考的时代里,那么我们将真正面临智慧的圣火被夺走的危机。
就像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说的那样:我并不担心机器像人一样思考,但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