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白莲教起义
☉[日]增井经夫 著 程文明 译
白莲教及其出现的要因
清朝自嘉庆时期开始衰弱,这种变化的具体反映便是史称“白莲教起义”的教团组织的起义,它历时甚久,且反抗顽强。所谓“白莲教”,是一个基于佛教阿弥陀佛信仰的民间结社,南宋以来,曾作为邪教被官府禁止过。至元代,农民多信奉此教,认为弥勒佛作为救世主现身的弥勒教信仰掺入其中。明太祖也曾利用这一信仰,创建了他的大明朝。明朝建立后,亲身经历此教,深知其实力的明太祖,随即将其作为邪教加以禁止,但教徒们另立名号继续发展该教。明清交替之际,白莲教受反清复明思想影响,屡屡成为反清运动的温床。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率清水教发动起义,乾隆五十年(1785),河南樊明德因信奉混元教而遭镇压,这些组织都属于白莲教系统的结社。此外,査阅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还有冠以各种各样名称的大小团体被清廷处以严惩,其理由是蛊惑民众,或闯入官署。
这些结社大多有着共通的、极其原始的动机:或是说大灾马上就要降临了,加入我们可以避免厄运;或是说只有某某才是救世主,得跟着他一起行动;等等。其仅凭此招揽信众,还缺乏一种可自成一体地发展、扩大的因素。加入该教的信众大部分都是贫农,那些即使是弃家流浪也不会后悔的人是白莲教的基础,所以其信众的连带意识未必有多强。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信仰,是一种饶幸的野心。不过,若是被动员加入的人变为多数,那底层百姓当然就拥有了共通的空间,进而也就产生了连带意识。白莲教徒起义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均衡,人民生活差距很大,纷争不断。四川的山区等地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外来移住民很多,公序良俗尚未最终形成,所以纷争既多,百姓生活的不均衡现象也非常严重。
虽然白莲教是以颇具佛教特色的教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固定下来,其基础也变成了以祈祷、巫术等为主的土俗性的东西,与以其他民间结社的系统、名号相异的团体相比,在内容上已经基本无异了。这意味着白莲教已不是一个宗派不同的教派,而是一个可以马上同其他教派合流、共享同一地盘的团体。若是出现不能合流,相互拒绝对方的情况,那应该是主要缘于地域或生活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基于教义上的不同。所以一般认为,元代末期红巾军起义后,宗教意味浓重的结社团体几乎归属同一范畴了。故此,白莲教才能爆发性地一下子聚集起数十万信徒。在明朝末期,也有人豪言称:我教信众不下二百万。
起义的发端
在山东发生的王伦的清水教起义,朝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镇压该起义之时,为防止同类民间结社进而也走向起义,朝廷加强了对他们的镇压,将河南的樊明德等率领的混元教教徒视作危险人物,将其中心人物刘松发配到了甘肃。刘松的弟子刘之协便改混元教为三阳教,称刘松的四子为弥勒佛转世的救世主,还将一个名为王发生的童子改名为“牛八”,说他是明王朝的后代。“牛八”这一名字,是明王朝朱姓“朱”字的拆写。不久后,称将会发生大事的信徒以加入本教可避免水火刀兵之灾为名扩大结社,其在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信众大幅度增加。乾隆五十八年(1793),政府对混元教信徒的抓捕行动开始。牛八是小孩,所以被流放到了新疆;其首领刘之协在潜伏于官衙中的信徒的帮助下潜逃,继续传教六年,其组织能力为白莲教的大起义奠定了基础。
为逮捕转入地下活动的刘之协,朝廷严令各地方抓捕,如此一来,很多地方胥吏开始以此为借口搜查民宅。那些胥吏贪得无厌,相较于被搜者是不是白莲教徒,更在乎被搜者是否出钱息事,以致富人破产,贫者无辜而死,时状惨然,特别是湖北官宪之横行尤为严重。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在各地揭竿而起。以湖北襄阳的姚之富、齐林之妻王氏等的黄号为首,张添伦等的白号、张汉潮等的蓝号等白莲教起义军向四川、江南、陕西进军。在四川,达州徐添德等的青号,王三槐、冷添禄等的白号,龙绍周等的黄号,罗其清等的白号,冉文俦等的蓝号等与湖北起义军遥相呼应,起义规模迅速扩大。这些起义军士兵在入教之时都提供粮食,之后平均分配战利品,过着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同时还不吃肉食,禁止奸淫等。总之,为强化其组织的凝聚力,他们制订了一些极具特色的政策。
按照清朝的法律,如果一般的百姓暴动或起义,城市因此被攻破,其守备官吏当被处斩,但未能对邪教煽动民众之举事前查知者受到的处罚却仅是免职。因此,所谓的民变一发生,地方官吏都称其为邪教祸乱,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在湖北、湖南,清军也曾击败白莲教起义军,但当时这种自发的起义相互间关联不大,仅个别的起义被清军镇压了下去。嘉庆皇帝曾亲自审问了嘉庆四年(1799)被捕的四川的王三槐,据传当时王三槐只是反复回答着“官逼民反”四个字,让嘉庆皇帝愕然。
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虽然在湖北、四川的两股大军会合后,起义军的组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一的军事行动也变得多了起来,但清廷派出了满族武官额勒登保、德楞泰等指挥讨伐,湖北、陕西的起义军开始逐渐败退。讨伐作战中,清军大体上是让被称为乡勇的义勇军冲在最前线,汉人军队绿营军兵紧随其后,满洲八旗军在最后观望;与此相对,起义军方面也是强行驱使难民冲在前线,信众士兵跟在其后。当时的难民和乡勇同为百姓,所以作战时,双方都必须在其后督战。一位名为梁上国的清军将领曾在他的奏章中就此写道:贼徒之中,怨恨官吏者十之有二,苦于饥寒者十之有三,被强行驱从者十之有四,真正的教匪仅十之有一,怨恨官吏者和苦于饥寒者一开始都不要命一般,其势锐不可当。但反乱数年,其势已渐缓渐弛,在地方荒废,可掠夺之物资变少后,贼徒之势必将弱化。
嘉庆四年(1799),嘉庆皇帝断然肃军,免去讨伐军经略大臣勒保之职,以信赏必罚之举,撤换了一批官员,并委任额勒登保代为经略,重建了指挥系统。其结果是官军的机动性大为增强,各地的自卫策略也得到了强化。对于以军事建国的清朝来说,认可民众拿起武器自存自卫虽是冒险之举,但嘉庆皇帝当时之所以敢于迈出这一步,是因为面对起义军的游击战,除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
如此一来,随着坚壁清野对策的推行,起义军的状况愈加艰难,逐渐成了官军所说的流贼,在他们转战各地的过程中,有的乡勇加入了起义军,使起义军内部愈发分散。虽有很多核心人物相继被官军捕获,但新的领导人物也不断出现,在甘肃、四川等地,起义军重新得势,且拥有了若干据点。尽管以嘉庆四年前后为转折点,起义呈现出大势将去的态势,但教团中的很多中坚教徒仍然狂热地坚持反抗,他们有时强行剪掉加入者的辫子,有时在加入者脸上刺上“莲”字以防止其逃跑,同时放弃大规模作战,转入了游击战。
嘉庆五年(1800),清军在四川的新店子、马蹄岗展开了最后的歼灭战,起义军因此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再未能重整旗鼓。白莲教既没有一个中央指挥体系,也不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民族意识较强的组织体,虽然它聚集起了数十万的民众,动员力量惊人,但缺乏新王朝的宣言和仪式化的统治形式,自始至终在本质上都是一次农民暴动。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说,是由于专制政治的魔咒依旧残存,束缚着农民的抗争。
嘉庆七年(1802),清政府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功臣、将领论功行赏,庆祝起义平定。虽然嘉庆八年、九年仍有一些被解散的乡勇与残存的白莲教教众联合,继续在陕西、湖北一带斗争,但都相继被征讨、平定了。嘉庆十年(1805),清政府将平定起义的军队撤回、收编,这场前后历时十年,令五个省的土地近乎荒废的起义结束了。据统计,在镇压、平定白莲教起义上,清政府的花费多达一亿两千万两白银,曾经充盈的国库几乎消耗一空,清朝的财政状况更加困难。
天理教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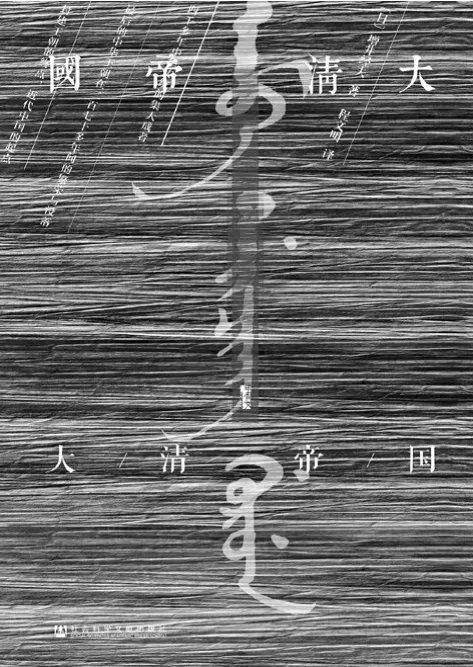
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这并不是说白莲教就消失了,同样的民众结社团体开始改名换姓,变换场所,反复不断地在各地涌现出来。由于它们也是一种组织程度比“邻组”更高的社会生活的必要单位,所以都将民间信仰作为其组织核心。与此相对,几乎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明末以来一直悄无声息的东南沿海的海盗,却自嘉庆五年(1800)前后,开始在其首领蔡牵的率领下再度活跃起来,清朝称其为“艇盗”。艇盗猖獗促使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建造了一种被称作“霆船”的炮舰,并最终以此击溃了蔡牵,但蔡牵本人通过施贿闽浙总督逃过了一劫。当时,即便是在对海盗的海上作战中,清军的腐败也甚为严重,卖武器给海盗者有之,不战而以金钱怀柔海盗者有之,嫉妒诬陷有功者等也大有人在。在此种状况下,李长庚送齿归乡,这象征着他即使尸骨难以返乡,也要至死剿灭海盗的决心。直至在嘉庆十二年(1807)的一次交战中被炮击阵亡,他毕生都在追剿蔡牵。嘉庆十四年(1809),蔡牵最终在定海被李长庚的部下歼灭。
虽然诸如白莲教起义、艇盗祸乱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有,并不足为奇,但在清代之所以能持续十年之久,恐怕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专制政治的抗争已到了极其强劲的程度。将这判断象征性地展现出来的,是天理教徒闯入皇宫这一对朝廷而言的突发事件。实际上,这一事件并非偶发之举,而是一次有计划的袭击,虽说本质上这是一次受迷信、占星术蛊惑而生的事端,可它袭击的毕竟是清代统治的中枢所在。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华北地区出现了一种被称作“八卦教”的信仰。据说在几个支派完成合并后,“八卦教”改称“天理教”。构成天理教核心的是当年河南滑县的一个木匠李文成,他通过学习天文占星术而成为该教首领,又以其组织能力使该教实力得到扩充,进而准备了武器、马匹等,待机举事。另外,还有时为河北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胥吏的林清,他也在成为当地教团首领后聚集起了数万之众。通过滑县胥吏牛亮臣的居中牵线,李、林二人联合,共同约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起事,届时李文成号“天皇”,得河南,林清号“地皇”,取河北,另有李文成一派的冯克善号“人皇”,据山东而立。
由于此谋未举事发,滑县知事强克捷在九月五日速捕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严刑夹断了李文成的下肢。随后三千余教徒袭击官衙,杀死强克捷一干人等,救出李文成,天理教众随即在河北、河南、山东省界之处蜂拥而起,称李文成为“大明天顺李真主”,在滑县设立了军政机构。另一路起义首领林清则命二百教徒潜入京城,自己坐镇北京郊外的黄村,等待李文成约定派来的三千援军。
潜入北京的天理教徒先是伪装成百姓推车送货,后待日没之时分为两队,分别自东华门和西华门闯入清宫。这一行动中,虽然早有宦官内应指引,但在东华门,由于门役关门迅速,所以仅有十几名教徒得以闯入。八十多名自西华门闯入者则自行反关了城门,打起事先准备好的写有“大明天顺”、“顺天保明”的白旗,径直闯入紫禁城内。
当时,嘉庆皇帝正在前往热河离宫的路上,不在宫中。嘉庆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取枪抗袭。递来火枪的宦官未填弹丸,这位皇子便将自己衣服上的扣子装入枪内射击,击中目标并使闯入宫中的教徒出现溃乱。不久,这些起义者和充当内应的宦官被随后赶来的禁军逮捕,林清本人也在十七日被官府抓获。虽然林清的冒险主义带来的仅是一次破天荒的入侵紫禁城案,未能收获任何成果,但其中反映出来的,在胥吏、宦官等群体中与起义教众持同一立场者大有人在的现象说明,招致动乱的弊病已经成为一种痼疾。其后,清廷开始全力讨伐李文成,加强了对滑县的围剿。李文成虽自重重包围中逃脱,本欲流窜举事,终遭穷追无路,不得已自杀而亡。
官僚群体中的清官
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官僚政治百年之间便腐败至如此程度,以致清代社会陷入这般动乱不定的状态。何为盛世?何谓和平?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促成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本身施以反省的问题。官僚对君主负责,对民众却不负担超越道义的责任——这种体制,一旦君主的威慑力不复存在,也便变得全然没有任何责任可言了。所谓历时百年的盛世,与其说是在官僚组织内部构建了一种钢铁构架,莫如说是已将其腐蚀殆尽了——实际上我们也难以认为全然如此。因此,若试着在这种动乱不定之中探求一些不同之处,则不得不言及那些清廉故事。
四川的白莲教起义首领王三槐被捕之时,嘉庆皇帝曾亲自审问他:四川官吏全都是你所说的那种无恶不作之徒吗?王三槐当时回答说:清官当有刘青天。所谓刘青天者,即时任四川南充县令刘清。据言其人公正无私,深得民心,当时前后有百余战,起义军均避刘清而去。刘清屡屡孤身前往起义军军营游说,归降者多达两万余人。一次,在起义军的阵营中,刘清看到当年曾为自己部下的罗其清——他当时已经成了起义军的首领,二人抱头痛哭后,罗其清盛情款待刘清并带他参观了军营,起义军也都列队迎送。刘清后来出任山东盐运使,在参与讨伐滑县天理教起义后,又出任云南布政使,接着自己请愿当了武将,成为登州镇总兵。
这样的例子散见于清代的一些记录之中。当然,由于记录者欲彰显这类青天白日般的官吏,并期待后人能以此为鉴,所以在当时,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也曾被大书特书。清朝同样推崇朱子学,曾极力防止朱子学的空洞化。但仅凭朱子学,是不足以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青天白日般的官吏的。大凡一种思想具现于ー人之身,仅此思想是不够的。清廉也好,爱也好,这些产生于思想之前的东西,必定是一种可用作培养的土壤,而它那丰盈的养分有没有普遍存在于清朝盛世却是个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