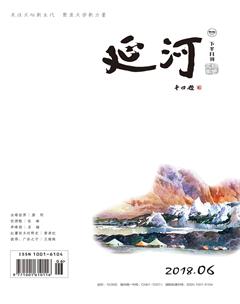红薯的乡村野史
黄孝纪
秧
我是在今年清明节村族祭祖的盛大聚会上,猛然记起,又提出这个问题的。
当我打算给红薯写一篇乡村野史,很多与红薯相关的旧时记忆便纷至沓来。可是,当我渐理出一个头绪,我发现,我已记不起红薯是如何在乡下育秧的了。可谓尚未开始,即卡了壳。
按照农历,这个月我满了四十七周岁。十几年前,我的父母先后去世。他们是做了一辈子农活的乡村老农,经验丰富。只是关于红薯育秧的事情,我已无法向他们询问。我脑海里依稀记得,儿时,生产队的禾场上,乌黑的猪栏淤,如同现今国民家中麻将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麻将牌,一条条,方方正正,是红薯秧的育床。
现在的情况是,我的这个两三百户人家的故土乡村,早在多年以前,就没有家庭养猪了。所有旧日的猪栏,都在一轮新农村建设热潮中一扫而光。哪里还有污浊的猪粪猪尿?哪里还有稻草浸泡得发黑发臭却肥沃的猪栏淤,用来肥田,肥土,做红薯秧的育床?村里的青壮年人,成了飞入城市的候鸟,一年里,只在春节和清明两个重大的节日急匆匆飞返乡村。水田都荒废成了野草丛生的旱地,往日里种植红薯的旱土,谁又还会在意呢?
电话打给我的大姐。她今年六十四岁,虽然多年来一直住在县城带孙子孙女,提起红薯育秧,果然还是记得真切的,甚至还有点兴奋。可以感觉到,那种远逝的生活场景,在她暮年的日子里,荒疏又亲切。她说,红薯育秧是在惊蛰之后,天气晴好,气温暖和。出了猪栏淤,筑成小腿高的育床,铺一层平日烧柴火积存的柴灰火淤,寸把厚。从窖里挑了备留的红薯种,个头适中,表皮要好,腐烂的,老鼠咬烂的,一概不要。红薯头上根下,略微倾斜,搁置火淤之上,密密麻麻,铺满育床,再撒上一层火淤。砍来新鲜的杉树枝叶,覆盖密实。杉树叶密集尖锐,既焐热,又防老鼠偷吃。几天后,揭去杉树枝叶,红薯已经发芽,长出紫红色的嫩茎和嫩叶。
清明节回故乡扫墓,村族举行开村初祖祭祖酒会,席开数十桌,摆满古宗祠的上厅和中厅。我有幸被安排坐在上厅,与村里辈分最高的长者一席。笑语喧哗,气氛热烈。寒暄攀谈中,我猛然记起此行的一个目标话题,关于红薯的育秧。一桌人中,除我之外,都是一辈子务农,且年岁在六十多岁至八十多岁之间。我的问题,引起了他们的热烈回应。几个老人一齐说开,各说各话,脸面生动,以倾吐这件荒疏多年的农活为快事。末了,我又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哥复述了一遍。
这位老哥的讲述大体与我姐讲的一致。不同的是,他说猪栏淤的育床上,先是铺一层秕谷或谷壳,放满红薯种后,再铺一层秕谷或谷壳,这样保温又透气。育床两侧,竹片弯插成拱,盖上薄膜。
到此,我的记忆得到了复原。我仿佛看见,惊蛰时分,青砖黑瓦的村边,一块一块大禾场上,筑满了一条条长方体的黑色的育床,空气中散发猪粪的味道,红薯紫红色的嫩秧,在春风里摇晃,生机勃勃。
有些事情,有些传统,哪怕原本是日常的生活,比如红薯育秧,只要断了一代人的传承,就成了历史,成了恍若隔世的追忆。
插
红薯秧长成十几公分高,就要移栽到园土里。
这个时节,村南一大片沃土,萝卜,白菜,大青叶菜,诸般菜蔬,经过了一冬一春,已然长蒿开花。砍了,拔了,翻土,整地,成行,开坑,是此时的主要农活。晴和的日子,园土里,村巷里,奔走勤快的农人,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两个陈旧发白的大木桶一前一后,装满了或稀或稠的大粪。整个村庄,整个原野,春风里飘拂着浓浓的大粪的臭味。
开好的土坑,村人提了粪桶,拿了长柄淤勺,舀了粪汤,弓着身,退着小步子,一一浇上小半勺。后面跟着的人,提一箩筐柴火灰,再一一撒上一把。这项工作,分田到户后,多是夫唱妇随。红薯秧也从育床上拿了下来,小心码放在谷箩筐里,挑到园土。一坑一个,栽上,培土,露出一丛红红嫩嫩的秧苗。
村前的稻田,阡陌交错,放眼所见,一片碧绿。一块一块的水田里,长满了野草和紫云英,开着繁花,粉云一般。到处蛙鸣鸟飞,水流如歌。红薯秧的育床,经过多日的发酵,已是顶好的有机肥。村人赤脚,卷了裤腿,用耙锄挖了,拖进筛子,一担一担,挑到水田里,倒在紫云英的花丛中,撒开。大禾场又再次恢复原状,空空荡荡。旷野里,时闻农夫驱牛犁田的吆喝。健硕的老水牛,拖着木犁和农人,在紫云英的花丛里,缓缓地行走,转圈。
湘南的天气,要雨有雨,要晴有晴。晴晴雨雨之中,红薯秧迅速生长,变化了色彩和形状。藤蔓匍匐,蔓延交错,叶片如撑开的绿伞,铺满了整片园土。
那时候,村里种植冬小麦。山野间的旱土,冬小麦与红薯轮作。端午前夕,小麦金黄。割麦,收麦,打麦,晒麦,卖麦秆,挖麦土,开红薯坑,村庄投入新一轮忙碌之中。
端午节,吃新麦子做的面条,糖包子,馒头。天气自此转入炎热,晴天渐多。不过这段日子,天公总会作美,下上几场及时雨,将开了坑正要插红薯的旱土浇个透湿。
冒着雨,或是趁着雨刚停歇。村人,我的父亲母亲,穿了蓑衣,或缚了薄膜,戴上斗笠,挑了竹筛,拿了镰刀,赶到园土里割红薯藤。红薯藤挑回家,放在屋旁的禾场或檐廊。家家户户,大人孩子,每人一把剪刀,坐在矮凳上剪红薯藤。
拿一根长长的红薯藤蔓,每隔三个枝叶,略于节前剪一刀,长度二十公分左右,大致整齐,叠放竹筛或箩筐里。此时的红薯叶茎,粗壮又嫩,剪剩的,零散的,折断的,收拢了,去叶撕皮,冲洗后,切成指节长,用来清炒,或者和上刚摘下的青辣椒,是农家最时鲜的菜肴。碧绿,脆嫩,甘甜。
天气耽搁不得。这几天,山沟间,山坡上,目光所及的旱土,到处是弓着腰身,屁股翘天,男男女女插红薯的身影。每个土坑丢一截红薯藤,一手抠开坑窝的湿土,一手拿了红薯藤,一插,培上土,一按压,成了。红薯藤直立土坑,枝叶朝上。
太阳一出,刚插的红薯藤,叶片随即焉了,软踏踏垂了下来,挨着土坑,病人一般。这样的景象,看着惹人担心。不过,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红薯命贱,生命力强大,就如同山村的農人,有了泥土的滋养,不经意间,就扎了根,恢复了活力,长得蓬勃起来。
黄黄的土壤,逐渐被浓绿爬满,覆盖。
挖
割了第一茬红薯藤,园土里的红薯种,就算完成了它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传宗接代。以后的日子,任由它们自然生长,藤蔓长了,厚了,轮着一茬一茬地割,用来煮潲喂猪。大集体的时候,大队生产队有饲养场。包产到户,园土成了自留地,家家都养猪。
插下的红薯藤,日生夜长,枝叶茂密,还需要薅一次藤。这件活多是在烈日下进行,因为节气已进入盛夏,晴多雨少。况且,夏日的雨,来得凶,收得快,打在脸面生疼,砸在地上,一粒雨就像盖下了一个大圆章。果断,决绝,绝无春雨的缠绵。薅红薯藤虽不是一件重体力活,却也十分辛苦。低头,曲腰,翘臀,一行一行地缓慢朝前挪步,一双手不停地翻捡红薯的藤蔓,扯断枝节上的根须,薅去杂草。上空烈日如火如烤,浑身汗湿,汗水在脸面上汇聚,滴落。一块红薯土薅下来,腰酸背痛,难以直身。自此以后,一直到霜降挖红薯,这几个月期间,红薯的生长就全凭天然,不需人力了。
不过,烦心的事情还是有的,比如偷红薯藤。偌大的村庄,家家户户养猪。野外的猪草,家家户户有人扯,日复一日有人扯,扯得猪草都疲于生长,难以招架。偷别人家的红薯藤也就十分自然了。只要有可趁之机,管它是园土里,还是红薯地里,或扯或割,下手生猛,匆忙溜走。这种状况总会被主人家细心的主妇发现,虽然逮不着是谁偷的。怒火中烧,总要发泄。骂村巷子,这是已逝岁月的特别印记。主妇,粗着喉咙,大着嗓子,扯着哭腔,祖宗十八代,任何能想到的恶毒的咀咒脏话,脱口而出,沿着所有的村巷,一一骂去。对重点怀疑对象,绕屋三匝地骂,指桑骂槐地骂。骂得唾沫横飞,声嘶力竭,一村颤抖。
相比而言,我们小时候,更喜欢偷红薯吃。放学捡柴的时候,一群伙伴结队上山。山边的红薯地,我们总要大摇大摆走进去光顾一番。长了大红薯的地方,泥土上拱,裂开,露出粗壮的红薯柄。我们用手扣土,或者用小木棒扒,或者用镰刀挖。虽是山野孩子,我们却也懂得不糟蹋,并不将整蔸红薯扯断,只是扒出其中的一个个头大的红薯,甚至还会用土掩盖扒出的孔洞,让其余的小红薯生长。村庄种植的红薯,大体两种,白红薯和黄心红薯。我们只偷吃白红薯,白红薯甘甜汁多,脆嫩爽口,饱肚又解渴。
辣椒下树的时候,暮秋已然来临。园土要翻挖,用来种植冬季的菜蔬,萝卜,白菜,诸般青菜,故先挖这里的红薯,我们也叫挖红薯婆。这片红薯,累月不停割藤喂猪,结的红薯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多,而且这时候的藤蔓也差不多是稀稀拉拉,短而小。挖一蔸红薯,甚至春日里种秧的红薯婆还在,又黑又老又空又烂,没什么用,猪都不吃,扔了。这片园土挖下来,只有大小不一的不多的红薯,一两箩筐就装了。
大面积挖红薯,是在霜降之后。此时,油茶已经摘下山,晚稻也已经收割,整天是晴好的阳光。挖红薯之前,要先割掉红薯藤。全家出动,全村出动。割,缚,挑。地里,路上,全是人。红薯藤湿重细长,成人一担挑两大捆,孩子的扁担每头只能跨上两三扎,一路藤尾扫地,挑回家。单是这项活计,一家人都要耗上好几天。挑回家的红薯藤,或者挂在屋墙外的竹蒿子上,或者挂在檐口下的横木,或者堆放在杂屋的楼上,任其风干变黑。漫长冬季,干红薯藤是猪的主饲料,用时,铡刀切碎,与剁好的猪草菜叶同煮。
紧接着就是挖红薯。也是全家全村倾巢出动。扛着三齿锄,挑着箩筐筛子,带着矮凳。清早出去了,要天黑才收工。中午送红薯回家,也是匆匆扒碗饭。挖红薯是一件苦力活,齿锄笨重,挥舞,挖下,一翘,一拖,俯身捡起一蔸红薯,磕磕土,顺势丢在身后,全身牵动,十分费力。这件工作,主要靠家中的男劳力完成。年少的时候,我有时也挖红薯,三下五下,一双手掌的指节处,就磨出花生粒大的水泡,水泡穿了,特别痛。而且,我常把红薯挖烂。可见,挖红薯还是一项技术活,瞄准位置,果断挖下,红薯完好,没有长期的功夫不行。捡红薯,摘红薯,是妇孺的事情。坐在小矮凳上,细心地分拣,大小各别,放进不同的箩筐和筛子。粗糙的手掌,满是灰土和薯浆。
累了,饿了,歇一歇,卷一筒烟,喝一碗茶。挑一只红薯,镰刀削皮,大嚼。又甜,又脆,又香。
藏
相比而言,我觉得我们村庄的这种窖藏方式要好一些。
小时候我没有见过竖窖,一个脚盆大的孔洞,笔直钻入地层深处。站在旁边往内看,黑咕隆咚,深不可测,令人战栗。说实话,我还是成年后才真正见识,在我岳父家的村后坡地,密密麻麻,像张开的大嘴,随时准备将从此经过的人吞噬。多年以后,我在报社做记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村庄的两个孩子,中午突然不见了。全村人出动寻找,也无踪影,以为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多星期后,才被发现,是掉入废弃的竖窖,侥幸捡回了性命。这样的竖窖,储藏红薯,将红薯取出来,都不甚方便。不但每次都要背楼梯上下,而且窖底下二氧化碳浓度高,时常还有昏厥的危险,甚至丧命。据说,有经验的人,先从窖口拉了绳索,放下一盏煤油灯,燃着,没事。灭了,可不能冒险下去。
在我们村庄,储藏红薯的,是横窖。村庄坐西朝东,在西山的脚下。这是一座红色黏土的山,山脚被人为挖削成笔直陡坡,丈把高。沿着南北走向,是一溜方形孔洞,窑洞一般,高宽不一。这些横窖,入口虽是一个,里面一条主道两侧,是深浅高矮不一的支窖,常常是几户人家一同共有。从土里挑来红薯,到了横窖门口,放下。一筐一筐端进去,仔细叠放在自家的支窖。到了傍晚,为防止他人动手脚,在红薯上面撒上石灰,以作记号。挖红薯的这几天,窖里不断添加红薯,一家往往要藏一二十担。横窖洞口有门,能上锁,共用。窖壁下挖有简易小沟,一拳宽,以让窖内土壤渗水流出,保持干燥。严寒的冬日,我曾多次跟随父亲到窖里拿红薯,外面寒风刺骨,里面却十分暖和。
并不是所有的红薯都储藏窖里。在地里分拣好的红薯,麻皮癞脸的,挖烂的,个小的,一律挑回家,倒在厅屋一角,用来喂猪。品相好的,也要挑几担放置堂屋的楼上。樓下是灶台,每日火燎烟熏,红薯少了水分,多了糖分,更好吃,拿取也方便。
老鼠是红薯的大敌。不但窖里的红薯时常有啃烂的,放在楼上的红薯,更成了老鼠的乐园。那时候,村庄老鼠特别多,晚上熄灯后,木楼板上如同跑马,嚯嚯嚯嚯,嘭嘭嘭嘭,吱吱吱吱,奔跑,磨牙,拖拽,啃咬,让人烦不胜烦。“死耗子!死耗子!”我的母亲时常在黑暗中大声骂,起身顺手拿一根长棍子往楼板上咄咄地撞几下。老鼠顿时安静了下来。不过,刚刚躺下,楼板上又跑马如初。第二天起床一看,红薯又咬烂了不少。
窖里偷了红薯的事情,也偶有耳闻。乡野山村,人物形形色色,总是难免。不过,抓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村族罚款,抄家,打断手脚,甚至引发家族械斗流血。毕竟,红薯是每一个家庭养家糊口的命根子。
到了深冬和初春,横窖里湿气重,腐烂的红薯多了起来。窖门口附近,时常看到丢弃的一片烂红薯,看着恶心又可惜。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特地到旧村的山脚转了转。因为多年前修建高速铁路线,旧村拆得只剩几栋旧瓦房。陡坡上荆棘密布,杂树丛生。昔日那一溜横窖,已无法见其踪影。
食
作为典型的南方人,一日三餐,我还是喜爱米饭。但在乡村生活的岁月里,一年中,总有几个月时间,一家的主食要偏重于红薯。这样的话,可以多节省些稻谷,以备来年春夏之间,青黄不接之所需,免得到时告借无门,挨饿。
漫长的冬季,焖红薯几乎每天必吃。灶膛里燃着熊熊柴火,有时,也是炭火。一家人围灶而坐,黑夜,一灯如豆,昏黄,寒风在拍打窗板。灶口乌黑的大鼎罐,有白色的热气窜出,浓浓的红薯的芳香。母亲揭开铁盖,一根筷子已能轻易插入薯中,熟了。这是十分寻常的一顿晚餐,热红薯,一碗白菜,或者萝卜。临睡之前,灶内尚有余火。母亲端来篾烘笼置于灶口上,把红薯从鼎罐里拿出来,一一摆放在烘笼里。偶尔,鼎罐里的水焖干了,底上积了一层乌黑的红薯糖,用调羹舀出来,粘稠。每人分吃一点,甜,且有股焦糊味。
村中有喝早茶的习俗,我家也是如此。早上我们起床时,母亲已经烧火泡好了热茶。洗漱后,端上红薯和萝卜条咸菜。一家人烤着火,呼呼地喝茶,大口嚼着红薯咸菜,随意言说,咂嘴有声。在篾笼里烘了一夜的燜红薯,水分收干,流着酱黄色的红薯糖,十分香甜。我们早上去上学,书包里往往也是带上几个焖红薯,边吃边走。
煮红薯汤,一般是中午。大红薯削皮,剖切成拇指大小,四四方方,大煮一锅。红薯汤甘甜,现在想来,是味美又有营养,且已好多年没吃到了。然在少小时候,天天喝红薯汤,喝得愁眉苦脸,还是很想吃米饭。
煨红薯是大人孩子都爱干的一项消闲之事,尤其是在大土灶里烧柴煮潲的时候。拿几个大红薯丢进灶膛里,用长柄炉叉子扒灰掩着。干柴火不断塞进去,火焰猛烈,火星飞溅,哔哔啵啵。不多时,红薯的焦香从灶门口溢出。煨熟了,扒出来,表皮炭化乌黑,灼热。拍拍灰,剥去表皮,色泽金黄,热气浓香扑鼻,令人馋涎欲滴。
许多时候,焖好的红薯吃不完。母亲就逐一把剩下的闷红薯撕去表皮,切成小指厚的红薯皮,每日放在火笼上烘烤,黄澄澄的,看着就喜欢。烘好的红薯皮,装进瓦瓮里,能存放到来年的夏天。吃的时候,柔软的,糖分足的,可以干吃。坚硬的,蒸软了吃,又甜又香。父母去世后,有好些年,春节去舅舅家拜年,舅妈都会送给我一大包黄澄澄的红薯片。两年前,舅妈患了眼疾,行动不便,年近七旬的舅舅跟随他的儿子女婿甚至还去了广东,在一家小厂做了门卫,家里也就没再种植红薯了。
红薯经过加工后,还能做成菜肴。记得小时候,村前的水井旁边,曾建有几个砖砌的方池,里面抹了水泥。冬天里,常有村人洗了红薯到机房里打成碎渣,挑到这里来洗浆,过滤,沉淀。反复几次,放干池里的水,得到一层沉浆。铲出来,用木桶提回家,适当加水搅拌均匀,就成了白白的红薯浆。舀一勺浆,在方形的铝皮容器中摊开,放入灶火上的大水锅里,盖上木盖,蒸熟。倒出来,摊在簸箕里,就成了一块黑亮的红薯烫皮。累积成叠,再切成筷子宽的条条,晒干,就成了红薯粉条,我们叫和结。干红薯粉条经年不坏,既可以做汤粉,柔软滑口,也可以与豆腐丝豆芽白菜丝同煮,是村人爱吃的一碗大杂烩,昔日村宴酒席的开席菜。
过年的日子,用红薯油炸的美食也挺多。红薯洗净去皮切片,做成油炸红薯片。切成丁,便是油炸红薯丁。刨成丝,粘上糯米浆,炸成圆圆的红薯丝油糍粑,或者炸成因形得名的螃蟹丸子。油是自产的新茶油,薯是堂屋楼上火燎烟熏过的,糖分足,炸出来的美食,又甜又脆又香。
酿
曾有好些年,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拌嘴,都是因为红薯烧酒的缘故。
在母亲看来,要两三百斤红薯才能酿出一百斤好烧酒。母亲给父亲算了一笔账,一日三餐酒,一餐喝一杯,二两,一天下来就半斤多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单喝酒就要四五百斤红薯。假如不节制,一天喝了一斤,那该多少红薯?要是没酒瘾,不喝酒,又该节约多少粮食?
母亲数落的时候,父亲沉默。父亲喝了一辈子的红薯酒,有酒瘾,就如同母亲有茶瘾一样。没酒就没了胃口,就浑身无力,就会想得流清口水,就干不了农活。这样,母亲看着又心疼了,心软了。父亲就又喝酒了,和容悦色,仿佛换了个人似的,精神十足。就算没酒的日子,母亲也会去别人家借,或者到别人家买,为父亲备办好。不过,母亲已经给父亲定下了规矩,一餐只能喝一杯,而且是母亲特意准备的小盅子。
母亲严管父亲的喝酒量,主要是家贫,子女多,生活困难。当然,估计也还与年轻时遭受到的一次惊恐有关。母亲动不动就会翻出几十年前的那件老事来抖一抖。说是一次父亲在外喝醉了酒,回到家中,母亲只责怪了两句,他就拿了菜刀要砍人,吓得母亲慌忙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大姐跑出家门,到别人家躲藏了一夜。而父亲晃着刀,撒着酒疯,在村巷里大喊大叫的,直跑到酒醒。母亲抖父亲这件臭事的时候,父亲往往是面带羞愧的笑容,低头不语。事实上,我从有记忆起,父亲就是一家人中脾气最好的,他性格温和,从没打骂过我们,也从未看见他喝酒醉过。
母亲一辈子限制着父亲的喝酒量,父亲也乐于遵守母亲制定的规矩。每年挖了红薯,母亲首先想到的,是给父亲酿红薯烧酒。红薯烧酒,是村庄每户人家的必备。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酿酒自然是她的拿手活。酒药也是她自己采来药草调配,抖烂后,揉成丸子,装在米筛里晒干,乒乓球大小。
酿红薯烧酒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先一个过程,是挑选几担好红薯清洗,在谷箩筐里用盾刀(盾形,五寸宽,刀刃朝下,长柄朝上)盾烂盾碎,一锅一锅煮熟,倒入大瓦缸,拌和酒药粉,捂盖好,发酵多日。这件事多是母亲亲手做,父亲也偶尔帮帮忙。相比而言,蒸酒则细致多了。发酵好的红薯糟舀入清洗后的煮潲大锅子,加水,盖上大木桶状的酒甑,酒甑与锅子接触的地方,用黄泥巴糊严实。酒甑与瓦过缸之间,由一根大竹筒连接,连接处也要糊好。过缸放置在一张矮方桌上,缸里加满凉水。烧火的时候,大锅里酒糟沸腾,酒气顺着竹筒进入过缸底的夹层,被缸里的凉水冷却成酒,流出缸嘴子,落入地面上预备好的酒瓮。火候的掌握也有分寸,火小了,酒出得慢。火大了,酒蒸汽来不及液化,从瓦嘴子跑了。酒不停地流出,芳香弥漫。过缸里的水也在不断变热发烫,需要不时更换,把热水舀出来,添加凉水。这项细致活,母亲一般总是独自完成,她不让我们插手,要不怕我们不小心烫着了,要不担心我们碰撞到坛坛罐罐,打碎了。蒸一次红薯酒,往往要几天功夫。装满几个酒坛子,为父亲备办一年半载所需。
母亲是个好客的人,父亲亦是如此。有人客来了,母亲总要设法弄几个好菜。父亲则以陪客之名,多劝客人喝几杯红薯烧酒,自己也笑眯眯地斟上,绝不含糊。每每这时候,我的母亲只是投去几眼嗔怪的目光,并不刻意阻止。
掏
在鄉村的季节里,在旱土里反复掏来掏去,只为了两样东西,花生和红薯。
盛夏烈日,收割了早稻,插下了晚稻,地里的花生也成熟了。在季节的驱使下,扯花生也成了全村性的整体行为,家家户户倾巢出动。花生扯了,多是在土里就摘下。花生苗则扎成小把,堆在土里任其晒干,日后挑回家,做水田的肥料。扯过花生的土里,很快就有村人蜂拥而至,大人,孩子,老人,每人一篮一锄,不停挥锄,掏土,捡拾花生。这样的场景要持续多日,花生土被反复掏过多遍,过滤出遗落的花生。一场暴雨过后,土里会零星冒出花生的嫩芽,白白胖胖的,小指粗。挖出来,既可生吃,也能凑成一碗菜,清炒,又嫩又甜。
相比而言,掏红薯的日子则漫长得多。即便收获后的红薯地里已经被人反复掏过无数遍,长冬农闲,还是有老人整日在周边村庄空荡荡的红薯地里,不停地掏,默默地掏,日复一日。他们往往早晨出去了,要傍晚才回家。他们的箩筐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大红薯,小红薯,烂红薯,甚至红薯根。
我的记忆里定格的最后一个掏红薯的老人,是我的父亲。那是1990年代的初期,我已从湖南省建筑学校毕业,分配到一家频临破产的小厂上班一两年。那个冬天,我失业在家,满面愁容,我的脾气也变得很坏。其时,姐姐们都已出嫁,我才20岁出头,父亲却已是年近八旬的垂暮老人。我整天闷在家中,母亲小心地侍候我的三餐。父亲则大清早默无声息地出去了,手提一个大菜篮,肩扛一把铁锄,穿一身黑色的旧衣服,身子佝偻。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吃过午饭多时。他提着半篮子红薯回来了,倒在厅屋一角。他拿了两只凉凉的闷红薯吃了,又默默地提了篮子扛了铁锄出门。
我是一个乡土的背叛者,自从跳出了农门,就差不多再也没有亲近过这片土地。那个时候,我们从心底里鄙视乡土,鄙视农民,鄙视农活。我们一心一意想远离乡土,在城市里寻找到一份舒适的工作,实现所谓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如今,乡土的鄙视者还在不断地增加,对乡土的鄙视也在不断加剧。在广大的一如我故乡的乡土,乡土已经无法提供足以维持乡民生存的生活来源。乡土在荒凉,颓败。昔日丰富的物产已然式微。高粱没了,穇子没了,小麦没了,荞麦没了,葵花没了,油茶没了,花生红薯也行将绝迹了。
在义乌车水马龙喧嚣的街头,偶然有推着推车的小贩放着吆喝的小喇叭:“烤红薯,烤红薯……”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一股熟悉的浓香拂来,常不免勾起对遥远岁月和乡土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