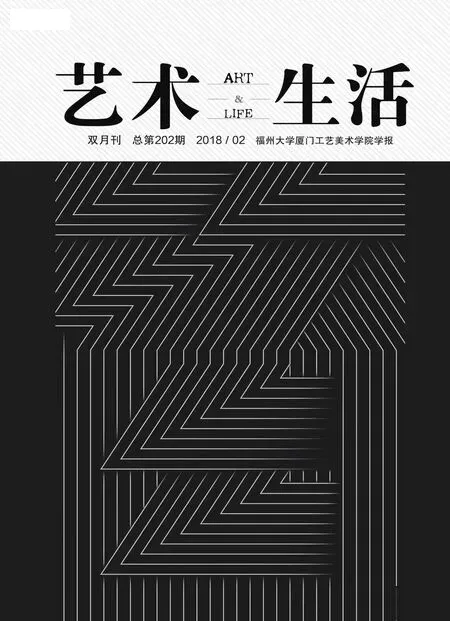中国水墨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拓展和精神延伸
张建华 林蕴臻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学院, 福建 仙游351254)
一、传统的登顶
西方传统写实主义规点认为:北宋山水散点透视写实主义是中国绘画艺术高峰,此后就日暮西山。但就中国文人画的品评标准,中国绘画艺术其实已经由高峰转向另一个山峦,一个山不在高的峰峦,一个不断产生伟大经典的峰峦。
中国绘画艺术何以由抽象的具象到具象的抽象,由写实转向写意却是文化哲学的命题。表层上看是与唐末五代之动荡战乱所造成的隐逸风气有关,其实其时禅宗思想的盛行是更为主要原因,代表画家有荆、关、董、巨等,斯皆隐者。
北宋初黄休复把绘画品评的标准由“神、妙、逸、能”转向“逸、神、妙、能”,这已经揭示了水墨画从形式与内容统一的“理”转向超出形式之外的内容去发展。苏东坡的思想及作品更强化了这样的走向。“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释义是: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信步归去,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那种看似淡漠无为却是悠远博厚的意境,此也树立了文人阶层审美的典范。由此,文人士大夫对水墨的推动,进入居功至伟的年代,建构起文人画图式技巧、意境等独特表现系统。
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夏圭的《临流抚琴图》表现的是外在的、自然的“逸”境,南宋画僧牧谿的《六柿图》表现的则是内在精神的“逸”境。《六柿图》画的虽然是六个柿子,但却绝不是表达六个柿子,按同时代西方中世纪绘画眼光视之,《六柿图》没有一张桌子、桌巾、盘子,没有质感、景感、光线、背景,这显然是个不存在于现实情境中的柿子;从北宋之前的诗意追求,细节忠实的眼光视之,《六柿图》无枝也无叶,无体态亦无细节,更无时间和空间,显然不是对景写生而来。《六柿图》开始,中国水墨就已经直逼“逸”的极限;它虽然是那么地混沌初开、平淡简易,但却可以是超乎时空、穿越无限,历万劫而生长。
不管是“超凡入圣”还是“超圣入凡”,1295年元代大画家赵孟頫以书法用笔入画,从而催生追求笔情墨趣的抽象化审美,开启文人画700余载的全新时代[1],代表作《山水三段卷》,表面上是具体的、现实的,写实的,从笔墨中透出的质朴而精妙、淡泊而醇厚、拙涩而秀润,貌似平凡无奇,其实是“超然物外”,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了。
不管是《六柿图》还是《山水三段卷》,都是人间寻常物。画家以笔墨借对象来写胸中“逸气”,山非山、花非花、雾非雾,这就是具象的抽象,从文人画中超乎寻常的、大巧若拙的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直至黄家另一人物黄宾虹那散发浓郁沉香而随意勾勒的画面。宾虹的山水恍若一团纠缠不淸、混沌未开的墨笔,浓郁、醇厚、润泽、隽永,似丑怪实美极、似保守实创新,似紊乱实清晰、似有限实无限,这一切都因笔墨而来,黄宾虹在小斗方内逸笔草草却有无穷意蕴,这是具象,更是抽象。

牧溪 《六柿图》

赵孟頫《山水三段卷》
文人水墨画的高峰在它初现时即已登顶,往后的大师只能是各领风骚而难以再超越。然而,久之必乏,“写我胸中逸气”太高,“逸笔草草”太简,“超圣入凡”太空,“超乎象外”太虚,如此高、简、空 、虚,使得文人画末流只知玩弄笔墨,一味求逸,而勿略知能、 妙、神。社会变革笔墨是精神,社会安逸笔墨是游戏,所以笔墨与时代脱不了关系。
二、笔墨之精神
上世纪之初,因西方强权的不断叩关而使中国的衰败益加鲜明,文人画当然也面临了更严厉的时代挑战,有志之士亟思水墨改良之道,徐悲鸿的“写实”水墨因时兴起。到了60年代后,又有刘国松的“抽象”水墨应运而生。
写实水墨系统在宋代已完备,比之徐悲鸿的写实或写生水墨,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徐悲鸿提倡写实的确是当时的一帖良方。长久以来,文人画只会写意不知写生,只求中得心源不知外师造化,只能满纸丘壑存心屮,而不捜尽奇峰打草稿,忽略写实和造型,徐悲鸿强调“写实”的内容决定形式,的确是当时水墨救亡图存的不二武器。
可惜的是,徐悲鸿的写实水墨最多在甚妙的等级,写实只能是改革水墨的手段而不能当为终极目标,但由他曾习北碑及推崇齐白石看来,他对水墨书法应更为深刻的认识。徐悲鸿的影响,既深且远,他使不少水墨画家开始对景写生,力求写实,矫正了不重造型的时弊,由此影响傅抱石、蒋兆和和周思聪等一大批画家,如石鲁能由写实入手,由能而神,甚至得意忘象,达到了逸品,不过,有太多以徐悲鸿水墨为师者,仍在肤浅的形似追求中打转。
笔墨独立于形象之外,就某种意义而言已是抽象了,笔墨精神与笔墨游戏均如是,徐悲鸿的贡献,是使脱离形象的笔墨重返形象之中,能不能再走出来,就看个人的努力与才气了,徐悲鸿走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后继者亦如是。
依西方观点认为,纯抽象水墨在古代中国未曾有之,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非未曾“进化”到此境界。上世纪60年代的抽象水墨画家,对传统文人画的认识太有限,对西方抽象的理解太片面,使他们能轻易地结合国际潮流与民族主义,西方形式与中国媒材就如此浅薄地结合了,代表画家有林风眠、吴冠中、刘国松等,他们的贡献在于开风气之先,在不同时代为水墨找到另一种展现的形式。
诚然探寻抽象之美,并非艺术的终点,抽象只能是改革水墨的精神而不能当做终极形式[2]。刘国松要革中锋的命,是不知笔墨之精神,于是革了僵化的中锋代以灵活的偏锋,而它们都是笔墨游戏。当然,刘对造型的掌握能力及气氛的控制的确过人,具象又抽象的日月与云山既新又古,既西又中,当然广受好评。不过,如此抽象水墨,除了如梦似幻,能有什么深度?[3]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刷新了建国后写实主义独霸画坛的笔墨形式主义的“审美疲劳”,但除了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可有内在精神的展现?
不管是内容主义为主还是形式主义为主,均非改革水墨的唯一答案,其解决之道,古已有之,两者兼具而已,它可以在对象与自我之间游走,它可以是具象也是抽象,但若有笔墨精神,就会是具象的抽象。
三、吐故为纳新
西方在抽象绘画兴起之后,重返具象世界的巨匠不乏其人,其中具象的抽象这一方向,与文人水墨的发展走向颇为相近,中国水墨的时空建构和哲学观照使其成为独特的艺术标准,也使其艺术规律有了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从而也构成了中国水墨笔墨语言独特的审美倾向,成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基本特征[4]。这是最民族也是最国际的。
意大利的莫兰迪(GiorgioMorandi,1890-1964)是较早展现此一风格的大师,其笔下的形状不一,瓶瓶与罐罐,随意排列后就可入画,其动人之处是笔触似笔墨。他在画布上轻轻留下笔刷移动的痕迹,以淡雅的中间色缓慢地画出瓶罐,画面如他的性情般澄澈、柔和、恬淡、素朴、温润,他借物咏情,抽象的情感甚于具象的瓶罐,画什么对画家而言并非创作的重点。
画者建华很长时期画荷的题材,所有的细部细节均可辨认地予以简,通过油彩反复堆叠的“笔墨”,使原本陈腐的形象因绘画性本质之突变而重新被加以关注,深沉、神秘、诗意、浓郁、寂然,由“笔墨”唤起的新的力量,使画者建华荷的题材更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百年来的绘画流变,抽象绝对居于最重要的核心位置,而写实与抽象的辨证、纠葛从未停歇。站在绘画本位的立场不论写实与抽象都有其深厚的传统,除了努力向西画学习,也必须反躬自省水墨传统,那么,抽不抽象,不会是个问题,过眼“见山不是山”,即能水到渠成。
四、当代的具象抽象
在水墨领域里,一向是厚古薄今的,能发思古之幽情的,往往是存世的水墨大师,总是只剩下绝无仅有的一位,无怪乎,每逢水墨宗师过世,媒体报导总是以“最后的文人画家”或“文人画的最后一笔”等词藻来形容,从傅心畲、张大千、李可染,乃至新文人画代表朱新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人画永远有硕果仅存的传承人物,证明它仍会顽强地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是一息尙存,而且会是不断焕发出奇异姿彩的画种,它已经是与汉民族发展相始终的“文化”,将会永远存在、与时并进。只个过,它的转进演化方式是隐而不显的,不像西方那样划代清晰。
水墨领域的绘画族外观之,百年来仍是满纸陈旧,而由族内观之,张大千富贵丰润,却是五百年来仅见,刘海粟雄奇魄丽,也是几百年只此一家;而吴昌硕清雅醇厚,也可说是一代宗师,还有黄宾虹的癫狂诡奇,更是绝无仅有。若再接着分析,以吴昌硕为例,其用笔舒放沉静,用笔盈秀稳敛,其笔墨中所透出的自在随意与浓浓的书卷味,已经是形象之外的笔墨了,这是意在象外,是有形象的抽象,只可惜吴昌硕较缺乏现代意识,以致减弱了他在造型上的可能进展。
具现代意识的水墨非常多,他们对于构成、形态、节奏、符号,都有清晰的概念,所以能轻易进入塞尚、梵高、米罗、克利,乃至波洛克、罗斯科的世界,凭借对造型意念的认知去从事水墨创作,这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抽象性格,单这种意识先行的创作,其抽象性并非由积淀转化而来,如此造型,往往只是有趣味而无意味的形式。看那些线条狂野、色彩鲜丽、构图奇特,但却仍充满文人墨戏式的现代水墨,把由此而来的荷花和张大千的荷花泪比,其深浅厚薄,一目了然。
石涛曾自署“小乘客”,他那见性又开天的水墨,当然是大乘境界,然而,欲达此境界,没经过一番“时时勤拂拭”的苦功是难以达到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和搬着画架对景写生,其境界高下之分往往在于抽象化的深度,这也是由再现式写生到表现式写意的关键所在。而能否自然而然地逐步抽象,与“小乘”经验的累积必然相关。
现代水墨早已经过抽象化的洗礼,但大多数是概念先行的文人墨戏式的抽象。当代,时时可看到许多气息清新的水墨画展。笔墨精神再度跃然纸上,水墨新生代,以混沌自在或调侃戏谑的笔墨展现了新的文人画风貌,沉静、深厚、饱满、戏谑、淸新,这是当代水墨“抽象化”的新世代,也是水墨当能与时并进的明证。
结语
长久以来,以西方写实精神成抽象观念来改革水墨的主张,导引了水墨发展逐渐“西化”的趋向,这样的改革,不但丧失了我们原本完备的写实与具象的抽象,也使水墨永远退居到当代美术的边缘地带。如果我们能看到当代西方油画许多逐渐水墨画的进展。应该自信水墨绝对是最为成熟内敛的画种,所有关于水墨改革的问题,其实是当代画家达不到水墨传统的水平,而非水墨本身难以开展。明乎此,水墨必将有新的转进,水墨当代精神终将与时代同行。
水墨的未来发展激越之处必得兼容并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学习西方来改革水墨形式,却很少回顾传统来恢复水墨精神,确立自身的艺术自信地位,当代水墨原有的文化形象和审美价值的本体形态信号并未有衰减或扭曲。这就值得我们对此作一番回顾和研究,从而思考中国水墨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拓展和语言延伸[5]。
——徐悲鸿经典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