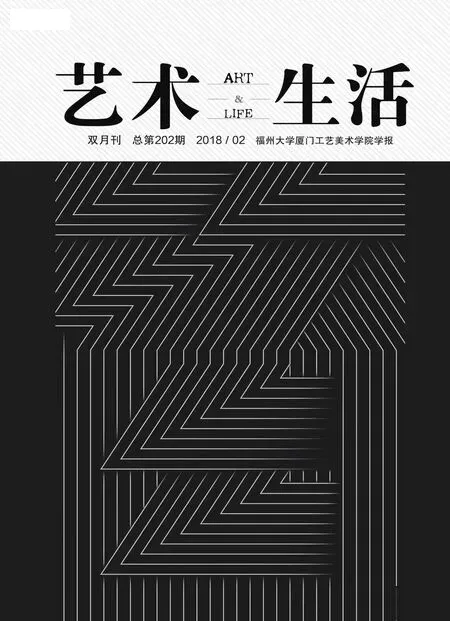现代主义美术在1950至1970年代的形式流变
——以杨秋人油画为个案的研究
赖荣幸
(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260)
肇始于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美术,曾一度社团林立,星光闪烁,成为与现实主义并举的重要艺术现象。但在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命题中,这些现代主义美术因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而面临着从内容到形式的改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那些勉为其难的被改造者和被遮蔽者,但事实上,现代主义本身具有批判现实和左翼的一面,也不乏以主流身份进入新中国,进而以积极姿态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并适应新的文艺思想的探索者。在新中国初期的美术创作中,是否可以找到一条有效联结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道路?或者说,在现实主义的宏大话语背景下,早期的现代主义美术家是如何坚持形式主义美学探索的?早期的现代主义美术家杨秋人(1907-1983),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考察个案。
一

图1 1932年决澜社第一届画展时合影,左前站立者为杨秋人
杨秋人1907年生于广西平乐,少年时举家迁居广州。1929年至上海,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参加决澜社。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主要在广东和广西从事艺术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华南文艺学院教务主任、中南美专副校长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等职。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杨秋人是因决澜社而进入美术史视野的。他与决澜社的关系,始于其在上海学习期间,因与王道源、陈抱一、倪贻德等现代西画运动先驱过从甚密,创作上带有现代主义倾向。1932年1月决澜社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会务会议,杨秋人是与会者之一,并于同年冬参加中华学艺社举行的决澜社第一回画展。他此后几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主要是围绕决澜社艺术圈进行的(图1)。
杨秋人早期(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存世极少,今天可以见到的作品和图片大约有13幅,以肖像和人物为主,线条粗犷,常用几何体造型,带有强烈的立体主义倾向,如1934年的《羽的颜》(图2),所画为其妻子钟羽的形象,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并有意夸张其眼睛、鼻梁和暗影。1946年的《骑楼下》,以灰绿色为主调,造型夸张,刻画了两个骨瘦如柴、头大身小的孩子在夜幕降临前陷入哀愁的情景。风景仅见《避风塘》《风景》两幅,均为决澜社时期的作品,其中,《避风塘》所画为海边景色,两处防波堤上各有一支灯柱,遥相呼应,堤内停放着一艘小船,堤外是辽阔的大海。《风景》所画对象为南京玄武湖,取景三面环山,山水相连构成的曲线,绵延穿过湖面的陆地以及水中的倒影,给人安详之感和宁静悠远的意境。虽然早期的作品主要见诸当时的黑白杂志,比较模糊,但我们还是可以隐约感觉到他对构图、线条和形式感的重视,体现出决澜社成员“色线形交错的世界”的艺术追求。
学生时代杨秋人在思想上就表现出左倾倾向,曾加入中国共青团并频繁参加学潮。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的解放战争期间,杨秋人被迫离开他所任职的广东省立艺专,后因政治环境趋恶劣而暂避香港,参加香港人间画会。1949年秋为迎接广州解放,他与张光宇、黄新波、阳太阳等人间画会成员在香港绘制巨幅毛泽东画像,运回广州悬挂在爱群大厦外墙以欢迎解放军进城。作为具有左倾倾向的民主人士,杨秋人随即被广州军管会任命为广东省立艺专及广州市立艺专两校联合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了其新时代的职业生涯和艺术创作。

图2 杨秋人 《羽的颜》 油画 尺寸不详 1934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秋人曾收集过土改及革命历史的题材并尝试创作,或许与工作繁忙有一定的关联,但更大的可能是这类题材本身并不符合他的审美旨趣。当然,作为新时代美术院校的领导,他显然不能再从事以往的现代主义和批判倾向的创作了,他必须找到一条联结以往创作经验的道路。
就今天可以看到的杨秋人作品(及图片)而言,总量大约有103幅,在时段上,1949年之前13幅,1949年之后90幅。如果将其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与其早期作品对比,首先感受到的是其内容上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作品大多是风景画,如果将其归类的话,大致包括:一是革命圣地,如井冈山《茨坪》、瑞金《叶坪》、延安《枣园远客》、莫斯科《列宁墓前》等;二是生产建设场景,如《晒网》《早勤》《剑麻山》《水电站工地的早晨》等;三是风景名胜,既有《庐山风景》等带有时代烙印的景点,也有《晨雾漓江》等表现自然美的风景作品。此外还有少量人物,主要是肖像写生。
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杨秋人巧妙地在圣地风景中表达革命主题,或者通过风景颂扬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让风景画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革命圣地和生产建设也是特定时代语境下艺术家深入生活的理想之地,进而通过创作达到净化自我灵魂和教育群众的目的。

图3 杨秋人 《列航》 油画 73×92cm 1961年

图4 杨秋人 《水电站工地之晨》 油画 86×110cm 1972年
二
题材的转变既是他对新时代的讴歌,也是其身份转变的象征,从早期的现代主义美术家转变为新社会的美术领导者。当然,笔者更关心的是,杨秋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艺术形式以适应新时代的?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他新中国时期的作品进行形式解读。
1.构图
杨秋人的作品,大部分与山、海、河、桥有关。尺寸较小,长宽大多是30-50cm左右,最大的长度也仅在100cm开外,但构图十分讲究和严谨,极少随意地写生。如1956年的《庐山风景》,为斜角构图,山峰自右上向左下延伸形成的曲线将画面分割为两部分,左下角为树木、房屋与山峰,右上角为河流、远山与天空。1958年的《列宁墓前》,将莫斯科红场的几座塔楼与排队的人群并置,形成自右下向左中、由大到小的透视关系,既显示出整齐而庄严肃穆的氛围,也体现了他对形式韵律的关注。1961年的《列航》(图3),左右两边翠竹斜依,中间空出的圆形恰如镜头,将近处的船只、远处的山峦和天空连成一体。近似的构图还有1962年的《晒网》,近景对称的两艘渔船从左右两边伸向画面中央,并留出伸向远方的视点。
2.线条
杨秋人的油画以线取胜。他作品中的线,有几种类型和功能指向,第一种“线”是普通的造型的线,即把线作为造型的手段,用于分割空间和区别物象,延续了现代主义美术重视线条表现的一面;第二种“线”是他喜欢表现带有线条特征的景物,如船只上的桅杆、电线杆、电线、绳索、桥梁等线条特征明显的建筑物;第三种“线”是对景物的排列形成的线条感。以1972年他的《水电站工地之晨》(图4)为例,作者十分注重线条的使用,在形体的转折处增加明显的线条,运送材料的船只排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船只后面留下长长的有秩序的曲线波纹,为作品增添了充满韵律的节奏感。1961年的《列航》,竹子用中国传统的双钩法造型,船只、山峦的边际均用线勾勒,船只在水中形成的弯弯曲曲的倒影也为画家所注意,而且船只之间有规律地排成线条,体现出他造型的严谨和画家自内而外的力量体现。杨秋人有时还借鉴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皴法来表现风景,如1957年的《海上之晨》,山体用块面堆砌而成,类似中国山水画技法中的斧劈皴,笔法结实有力,富有山岩的质感。1960年的《剑麻山》(图5)以密密麻麻的色点塑造山体,这种色点与新印象派的“点彩”有形似之处,同时这种表现山体特征的细小笔触,也使人想起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雨点皴”。
3.色彩
杨秋人的作品,大多以绿色为主调,他不仅以色彩造型,而且擅长用色彩去表现时间,他喜欢作早晨之境,云雾初开,宁静清新。或许是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影响,他有意减弱景物的明暗关系,注重物象的本色表现,具有装饰效果。如《水电站工地之晨》,以翠绿、土黄和湖蓝为主要色调,通过提炼取舍,以色彩区别形体,注重类型化色彩的使用和抽象形式美感。但与中国传统山水画不同的是,他也注重光线在色彩中的表现,如1981年的《归牧》,阳光洒落在山谷的中间,牛群呈现在视觉的中央,通过光色将近景、中景与远景拉开,占主要画幅的群山,并没有刻画具体的树木,而是通过色块和装饰性的色彩并置来表现其植被及远近关系,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空间表现与西方现代绘画的光色效果有机结合起来。
4.意境
黄渭渔在评论杨秋人的油画时说:“它们都像是一首首散文诗一样,短小精炼,以极其鲜明、秀丽的形象吸引着观众。”[1]杨秋人试图将现代主义形式与油画风景相结合,并借鉴中国山水画的形式构造油画的意境。上述所说的构图、线条、色彩都是其实现意境的手段并成功地将他们连串起来。如1957年作于东欧的《海上之晨》,海边的古堡静静矗立在山腰上,平静的海水伸向远方,在冷色调的清晨的海水的映照下,古堡显得遥远、冷清,似乎在述说着其久远的历史传说。1961年的《初霁》(图6),不同颜色的颜料在稀释剂的作用下流淌于画布之上,将漓江的峻峭与秀美表现得恰到好处,江中宛若水蛇的竹排使漓江更具形式美,岸边的茅屋和三三两两劳作的人们,又平添了几分生活的诗意。《归牧》通过别致的构图,让牛群有秩序地排列在一条横穿画面的直线上,与山峰形成一个长长的山谷,营造出幽静空灵而又明净的视觉图景。《晨渡》则以绿色和湖蓝为基调,峰峦叠翠,舒卷的白云徜徉于山谷之间,与水雾融为一体,山峰倒影若隐若现,江面舟船点点,早起的人们正准备渡江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晨雾漓江》表现漓江烟雾缭绕、碧波荡漾的朦胧之境,凤尾竹随风摇曳,婀娜多姿,远处群山若隐若现,是一幅随性淡然的作品。另外,杨秋人的所有油画风景,几乎都留有较大的天空的空间,类似中国画的留白,既为他的构图服务,也为营造画面的空灵意境作了很好地铺垫。
关于意境,吴作人在1960年的《关于发展油画的几点意见》中曾指出:“任何画都离不开‘意境’,‘意’就是理想,‘境’就是现实。……要立无产阶级的‘意’和写社会主义的‘境’,使两者相结合,以创造出充满革命豪迈‘意境’的新作品。”[2](P1037-1041)杨秋人有不少表现生产建设的作品,但与同时代表现火红的色调、灿烂的笑容、沸腾的矿山模式所不同的是,他借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尤其是宋画的表现方法来画油画,很多作品都以“晨”为时间,以绿色为主调,巧妙地以自己所特有的创作方式,在风景中道出社会建设的主题,轰轰烈烈的生产工程建设在他笔下成了优美宁静、意境悠远的风景,给人清新、宁静的视觉享受。与其他艺术家略有不同的是,杨秋人以风景为题材切入新时代的艺术创作。这恐怕与风景的装饰性和民族性有关,他难以割舍现代主义的形式影响,又要适应新时代的文艺要求,人物画创作对他而言显然

图5 杨秋人 《剑麻山 》油画 54×81cm 1960年
图 6 杨秋人 《初霁 》 油画 73×92cm 1961 年是勉为其难的,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线条、造型和空间表现,却与现代主义美术有诸多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大约在1970年代,杨秋人写了一篇名为《关于形式美》的手稿,这篇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充满辩证思维的文章,全文仅约800字,虽然在强调内容、题材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讨论形式美,但仔细阅读全文,形式美才是他强调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形式美是很重要的,艺术一定是美的,美的艺术才有感染力,在艺术中,真实与美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3]在形式美受到质疑与批判的年代,可以说是难得的真知灼见。
三
作为早期的决澜社成员,决澜社的艺术倾向深刻影响了杨秋人的创作,或者说,正是因为他本身对现代主义的诉求使他加入了决澜社。当时发表的代表他们艺术行动纲领的《决澜社宣言》强调:“我们往古光荣的历史到哪里去了”,“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欧洲的艺坛实现新兴的气象”,“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4](P8)这份宣言有几点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反对当时的中国艺坛追求纯造型的世界,并希望追溯历史,借鉴欧洲现代主义构建新时代的中国艺术。作为诞生于1930年代摩登都市的现代主义美术团体,经过抗战的现实改造以及面对1949年之后的新的时代语境,显然需要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径。
相对于其他现代主义美术家而言,决澜社成员大多还是以主流身份进入新时代的,比如庞薰琹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倪贻德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杨秋人和阳太阳同时担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决澜社成员的作品风格虽不尽相同,但均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如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至上主义等的影响,强调色彩与线条表现,追求纯造型的艺术。或许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造型习惯和审美思想,使得建国后的他们大多不约而同地转向民族化的探求。如:庞薰琹致力于民族传统装饰图案研究及绘画创作;倪贻德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主张从本质上认识和继承民族艺术[5](P6-9);阳太阳转向水墨和写意山水创作,以富有节奏与韵律的形式表现地域风景;丘堤的油画带有强烈的装饰色彩;杨秋人则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油画风景结合。如果将杨秋人建国后的油画风景与《决澜社宣言》及其早期的作品进行比照,会发现其中的关联性是明显的。尽管时代迥然不同,但我们仍可看到他的艺术语言和结构范式的延续,如线条的强调、近乎平涂的色彩、刚硬的造型、讲究韵律的物象排列,等等。“色线形”的造型观念始终是杨秋人的创作的核心,他借助传统艺术的方式有效实现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嫁接。
当然,追求油画民族化也是建国初年的时代诉求和政治命题。自近代以来油画在中国的实践,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西化的问题,或中西融合,或调和中西,或用西方油画的语言表现中国内容,像早期的李铁夫、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陈抱一等人,尽管其学习油画的背景不尽相同,但其油画创作都无一例外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养分。特别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扬,民族化逐渐成为主导话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度提倡向苏联学习,但民族的、民间的话语体系始终伴随中国艺术讨论与实践的历程。作为以主流身份进入新社会的美术院校的负责人,杨秋人显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的创作实践汇入民族化的时代洪流。
结语
油画民族化是新中国油画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中间有过不少理论与实践,比如用经典西方油画语言表现中国精神的吴作人,将革命现实主义和写意手法相结合的罗工柳,从民间及敦煌艺术汲取资源并着重构建油画中国风的董希文,探索纯形式和意境追求的吴冠中,从延安走来由版画转向油画的“土油画”代表胡一川,等等。艺术家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入手,所汲取的“民族传统”也不尽相同,但都作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油画在中国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杨秋人是从现代主义开始的,他将现代主义的形式感与传统艺术的色彩、线条、造型结合,既有现代形式感,又不失传统艺术(宋画)的严谨和工整,进而建立了个人的艺术语言体系。杨秋人一生创作的油画作品数量不多,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更少,但无论是把他的作品置身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风格坐标还是世界油画的图像谱系,我们会发现他的艺术风格都是独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秋人是独辟蹊径的,这也是他的油画风景最重要的风格和最具价值的一面。事实上,如何构建具有现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油画学派,仍然是21世纪中国油画的课题,在这种语境中重读杨秋人的油画,或许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