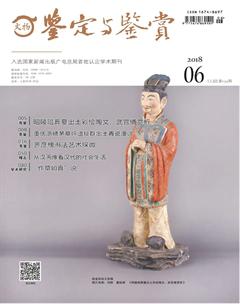从神坛走向民间: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
张睿祥 杨筱平 欧秀花
摘 要: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影响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人类对玉器的认识历经巫玉、礼玉、葬玉和玩玉四个阶段,而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玉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主要功能。
关键词:巫玉;礼玉;葬玉;玩玉
世界范围内的玉矿集中地区有中国、新西兰、墨西哥、印尼等,唯有中国玉器的发展源远流长,并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玉文化。倘若可用一类器物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联系起来,则非玉莫属。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爱玉、惜玉、琢玉成器,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杨伯达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一文中,结合考古资料将我国古代玉器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分为孕育、成长、嬗变、发展、繁荣、鼎盛六个阶段。而后又在《巫—玉—神泛论》中提出了玉器发展历经巫玉(神器)、王玉(瑞器)和民玉(玉翠饰玩)三阶段的论断。文章在此基础上,侧重玉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将玉器的发展历程分为巫玉、礼玉、葬玉、玩玉四个阶段,显示出人们对玉认识观念的嬗变过程。
1 巫玉阶段:史前—商代
玉石的发现大抵与人类捡选石料的活动有关。史前先民对玉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视觉和触觉的感受。《说文》:“玉,石之美。”因此,把玉石从普通的石头中分离出来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直接表现,而非现代矿物学上对玉严谨的科学定义。
人类发现、加工并使用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10000年,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址中普遍发现人类用玉的痕迹。玉料硬度大,即便我们通常所说的软玉,其硬度也为6~6.5度,不易雕琢。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且金属工具未产生的时代,一件玉器的成型费时耗力,极其不易,珍贵程度不言而喻。因此,玉器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少数人所能够享用的器物。只有拥有权威的人,才能支配大量人力为他们制作众多精美的玉器,
史前玉文化在全国的分布以及发展水平显示出不均衡性。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史前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一北一南,代表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两个中心。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与红山、良渚同样有着璀璨琢玉业的齐家、石峁、石家河、凌家滩等史前文化被揭示,为了解史前玉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考古资料显示,史前人类对玉料的加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浙江余杭市反山遗址M12出土玉琮(M12∶98)上的神人兽面纹(图1),采用细阴线刻,细如毫发,可谓东周玉器游丝毛雕工艺之滥觞;陕西石峁遗址发现的玉璧,厚度最薄者仅有0.2厘米,显示出极为高超的片状切割技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玉人(98M29∶15)背面的牛鼻穿孔(图2),残留的管钻芯的顶端直径仅有0.15毫米,令人叹为观止。
在蒙昧的史前时代里,玉器被赋予了通天礼神的灵性。《说文》:“灵,灵巫也,以玉事神。”玉的使用控制在被称为“灵”的事神人手中,他们在部落中被认为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物,有沟通上天与人世的能力,各种造型的玉器便是他们沟通天地的媒介,或者称为法器。又《说文》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而致福也。”甲骨文中“礼”的写法,形似两串玉器盛放在容器中,用来事神致福。史前遗址出土的一些玉器形制特别,在无法准确得知其用途时,只能以其大貌命名。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器、马蹄形器,良渚出土大量的璧、琮、钺,石家河的玉神面、玉虎头,凌家滩的八角星纹玉鹰、原始八卦图玉板等,很难将这些器物确定为日常生活实用器,那么意味着它们有其他特殊的用途。在红山、良渚遗址发现的大墓中,普遍有大量玉器殓葬,显示出“唯玉为葬”的习俗。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M1,随葬玉器种类丰富,墓主人头枕玉璧,两手各握一玉龟,腹部陪葬勾云形器,右臂佩戴玉环。墓主人身份特别,既是玉器的享有者,更是社会组织中宗教与政治为一体的化身。他的身份不同寻常,凌驾于一般部落成员之上,或为巫觋或为军事酋长,生前他满身披挂玉器,是何等神圣威严。
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夏商,并没有完全摆脱浓厚的巫术氛围。《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好占卜,事无巨细都要垂问神灵。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蜕变而成的王以及享有特权的贵族,他们依然是玉器最直接的掌控者。殷墟妇好墓出土了700余件玉器,玉质良好,种类丰富,展示了商代晚期辉煌的玉文化成就。
2 礼玉阶段:周代
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对殷商亡国的反思与总结中,重人事轻神鬼。周公制礼作乐,产生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表现在用玉方面,则规定了贵族各阶层用玉的质地、形制和规格,以玉为载体的社会礼制日臻完善。《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每逢朝觐,从天子到诸侯,各执不同玉器,以示地位身份。
孔子将玉器所具有的温润、缜密、無瑕、光洁等性能与君子所具备的仁、义、智、勇等美好品德联系起来,赋予“君子比德于玉”的独特人文意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促使了佩玉的流行。佩戴玉器类型多样,有腕饰、项饰,特别是诸侯及其夫人佩戴的由玉璜、珩、冲牙、玉管珠穿系而成的大型组玉佩,结构复杂,佩戴于颈部垂挂于胸前。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出土了一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图3),其夫人礼降一级,M2012夫人墓出土了一件五璜联珠组玉佩;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M26分别是芮公及其夫人墓,各出土一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63复原的组玉佩(图4),主体由22件玉璜自上而下依次排列,所用玉佩50余件,复原长度1.58米,是目前发现结构最复杂、用璜数量最多的组玉佩。《诗经》云:“巧笑之瑳,佩玉之傩。”郑玄笺:“傩,行有节度。”《礼记》载:“行步则有环佩之声。”佩者步伐的轻重急缓影响组佩发出的音效,只有步伐舒缓有节奏,组佩的摆动才和谐有度,在获得听觉审美效果的同时,表现出佩者仪态与风度之美。因此,贵族佩戴组玉佩,不仅彰显了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和无上荣耀的社会身份,更是为时刻提醒他们保持贵族高贵优雅的仪态。两周之际,随着周王室东迁,实力衰微,为彰显贵族特权而建立的系统化礼制受到削弱,礼玉时代渐趋消逝。
3 葬玉阶段:汉代
汉代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是玉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汉武帝时期凿空西域,丝路畅通,和田玉被大量开采并进入内地。玉料来源充足,这是玉器发展的根本保证。汉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家对玉的推崇一如既往,佩玉在汉代进一步发展。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不仅表现在将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之一,连汉代皇帝的谥号也均带“孝”字,全民行孝蔚为风气,厚葬自然成为恭行孝道的最佳方式。
另一方面,道教“长生不老”的宗教观和羽化登仙的神仙思想深入社会,继而影响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玉被神化成能保持尸體不朽、灵魂不灭的神器,促使以玉殓尸、裹尸制度的形成,并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葬玉流行并发展到了极致。丧葬用玉盛行,由周代的玉覆面发展到整套玉衣、玉九窍塞、玉唅、玉握、玉枕、玉踏的完整形式。用金银丝线编缀玉片而成的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所用的殓具。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出土了两件金缕玉衣(图5),使用者分别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这是首次发现的玉衣实物。其在丧葬礼仪中的功能近似于内棺,而非殓服。到了汉代,玉器礼玉的意义并非消失殆尽,比如玉片的编缀就有金、银、铜缕之别,所对应使用者生前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魏晋社会动乱,战乱四起,政权更替频繁,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玉器发展低潮期。魏晋玄学流行佛教兴起,兼之时尚“服玉”,以及当权者提倡薄葬,风气所及,丧葬用玉大大简化。魏文帝曹丕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明令禁止使用“珠襦玉匣”,玉衣厚葬之风不复于世,九窍玉塞也很难找到全套的。贵族墓葬中虽然也有少量玉器出土,但数量和质量都逊于两汉。两汉以来,日式渐微的礼玉进一步衰退,除了璧、圭一类作为礼玉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祀等礼仪中,传统的礼玉几近消失。《抱朴子》中有“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玉者,寿如玉”的记载,魏晋文献多载有餐玉以求长生的故事。意欲长生的贵族致力于搜罗古玉,将其碾为粉末服下,造成大量玉器的消失。
4 玩玉:唐至清末
唐代玉器在礼制上的反映当属玉带,它本是游牧民族系于腰间悬挂小型用具的带具,称为蹀躞带。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玉带出自北周若干云墓,是一条九銙八环蹀躞白玉带。玉带佩戴制度的形成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唐实录》载:“高祖始定腰带之制,自天子以至诸侯、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许用玉带。”《新唐书·舆服志》中对王臣贵族使用玉带材质、数量按等级做了明确规定。1970年10月,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了10副保存完整的唐代玉带銙,有九环蹀躞玉带銙、骨咄玉带銙、狮纹白玉带銙、白玉伎乐纹带銙(图6)、斑玉带銙等,形制纹饰不尽相同。这是唐代玉带銙数量最多、最完整、最集中的一次重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唐代玉带銙的认识,为研究唐代革带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宏观角度来看,唐代以后玉器明显世俗化,上古神秘的无穷魅力荡然无存。唐人不落旧制,大胆创新,在纹饰和器形方面均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祥瑞动物、果实花卉、舞蹈奏乐等一批寓意丰富极具生活气息的纹饰常见于这一时期的玉器上。陈设器、装饰品无所不有。镂雕、圆雕、高浅浮雕、局部细密的阴线刻,融会贯通。各种雕工精细、形态优美的玉器,着意表现技术的高超,甚至器形纹饰的设计超过了实用本身。如此,玉器浓烈的世俗人情味可见一斑。
北宋徽宗嗜玉成癖,上行下效,玉器制造业蔚然成风,琢玉名家辈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玉器世俗化、商品化的步伐,杭州等大城市出现了玉器加工与销售一体的玉肆。明代制玉高手陆子冈雕琢的玉器,纹饰细如毫发,无人能及,被誉为“吴中绝技”之首。到了清代,见于史籍记载的玉匠已不胜枚举。玉质之美、琢玉之精、用途之广空前繁荣,既不拘于礼制严格规范的桎梏,又与汉代神化色彩迥然有别。玉器自诞生之日起,经过8000多年的发展,暗藏其中的神秘慢慢脱去,附加的礼制意义也逐步弱化,成为备受中国上至皇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青睐的艺术品。
清代学者俞樾在《群经评议·尔雅》中说:“古人之问,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玉的情结依然是最深的,这是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无法相比的。在中国的词语中,与玉相关的词语、成语不胜枚举,如亭亭玉立、金口玉言、金玉良缘、抛砖引玉、冰清玉洁等,从古至今无不表达着美好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