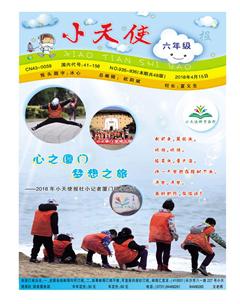灾之犬
沈石溪笔下的动物充满灵性,在它们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人类所缺失的那种单纯的美,每读一次,心就会被触动一次,是感动、感慨,还有一种无奈与叹息!
这是一条很漂亮的猎狗,黑白相间的毛色,匀称的身段,长长的腿,奔跑起来迅疾如风。名字也起得很漂亮,叫花鹰,意思是像鹰一样敏捷勇猛。
花鹰原先的主人是曼广弄寨子的老猎人艾香宰,但自从收养了花鹰,艾香宰家里就祸事不断。先是大儿子上山砍树,被顺山倒的树砸断了一条腿;过了不久,小儿子用石碓舂火药,火药自己炸响了,炸瞎了小儿子的一只眼睛;再后来是艾香宰带着花鹰上山狩猎,瞧见一只狗熊从五米远的草窠里钻出来,端起猎枪瞄准狗熊的耳根部位开了一枪,叭嗒,臭子儿,没打响,狗熊听到动静猛扑上来,艾香宰扔掉猎枪赶紧爬树,一只脚后跟连同鞋子被狗熊咬了去。
连续出了几桩事,艾香宰全家惶惶然,便从山里请了位巫师。那巫师一进院子,就指着拴在房柱上的花鹰说:“这条狗身上的阴气很重,会招灾惹祸。唔,它眼睛里整天淌黑泪呢。”艾香宰当即把花鹰拉过来,撩开它脸颊上的白毛,果然发现在白白的毛丛里,藏着几撮短黑毛,断断续续,从眼皮挂到嘴吻。艾香宰的小儿子抡起一根栗木棍就要朝狗鼻梁敲去,被巫师挡住。巫师郑重地说:“这狗杀不得,谁杀了它,它身上的阴气就像一棵树一样栽在谁家,祸根就扎在谁家,只能卖掉或者送掉。”
于是,艾香宰放出口风,谁给十块钱,就可以把狗牵走。那时的十块钱只能买一只鸡,一只鸡换一条狗,简直跟白捡了似的。可是寨子里的老百姓都晓得这是条不吉利的狗,再便宜也无人问津,我是知青,不相信神神鬼鬼的事,我想,花鹰本来就是一条黑毛白毛混杂的花狗,白脸上有几根黑毛,是很正常的,什么黑泪,纯属迷信。
我那时已对打猎很感兴趣了,特别想养一条猎狗,但猎狗身价金贵,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还抵不上一条中等水平的猎狗呢!因为囊中羞涩,想养条猎狗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现在有这等便宜,岂肯错过?于是,我毅然掏了十块钱,把花鹰牵了回来。
我用金竹在屋檐下搭了一个狗棚,里面铺一层柔软的稻草,并用两节龙竹做成一个食槽和一个水槽,吊在狗棚门口,给花鹰布置了一个新家。
花鹰对这个新家颇为满意,一会儿钻进稻草堆里打几个滚,一会儿蹿出来在我面前使劲摇它的黑尾巴,上下左右全方位地摇,像朵盛开的墨菊。它和我好像前世有缘似的,几天工夫,就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
每天大清早,它用爪子扒我木屋的门,準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白天,我无论上山砍柴还是下田犁地,它都像影子似的跟着我。有时,它也会找寨子里其他狗玩,但只要我一叫它的名字,它会立刻撇下它的玩伴旋风般地奔回我身边。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不想吃东西,它从垃圾堆里刨了一根肉骨头,把它认为最好吃的东西送到我的床边,可惜,我没法享用它的慷慨。
晚稻收割完了,农闲是狩猎的好季节,我带着花鹰上山打野兔。不知怎么搞的,在跳跃一条只有半米宽的小溪时,脚脖子突然扭了一下,当即肿了起来,疼得不能落地,拄着拐棍好不容易才回到寨子,敷了半个月的草药才见好转。
后来,我又带着花鹰到老林子里去埋捕兽铁夹,想捉几只肉质细嫩的豪猪,到集市换点零用钱。我刚把捕兽铁夹埋进布满野兽足迹的小路上,铁夹上的插销自动脱离,我躲闪不及,砰的一声,铁杆重重砸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手背上立刻蒸起一只乌血馒头,一个月不能捏筷子。
连续两次意外,我心里未免发毛,回想起巫师所说的流黑泪的话,心想,莫非花鹰身上果真带着阴气?
我信仰唯物主义,但不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想,我应当采取一点防范措施,就用剪子把花鹰白脸上那小撮黑毛剪了个干净。黑毛倒是没有了,但被剪去的地方露出红色的皮肉,一点一点嵌在雪白的毛丛里,黑泪变成了红泪。红泪,不就是血泪吗?凶兆加码,我心里更别扭得慌。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叫我魂飞魄散的事。那天夜里,我到邻寨的知青点找人聊天,半夜才带着花鹰回家,沿着昆洛公路走了一半,突然,花鹰咆哮起来,岔进一条小路朝山坡奔去。我以为它发现什么值钱的猎物了,便兴冲冲地跟在后面。天上没有月亮,星光朦胧,能见度很低,我高一脚低一脚走得晕头转向。花鹰突然停止了吠叫,奔回我脚边,嘴里叼着个什么东西,白白的,圆圆的。我弯腰从它嘴里接过来,凑到鼻子下一看,差点惊得心脏停止跳动——我捧在手里的是一只骷髅。我再瞪大眼睛四下一瞧,东一个土堆,西一块石碑,我正置身在一片乱坟岗里呢!我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扔了骷髅,转身就逃……
这时,我开始相信,花鹰身上确实裹着一团阴森森的鬼气。
我虽然只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卑微低贱,但这条命总比狗要值钱些吧,保自己的命还是保这条狗,我想,首先当然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我降价五元想把花鹰处理掉,仍没人肯要,杀又杀不得,卖又卖不脱,只好扔掉。
俗话说,撵不走的狗,喂不熟的狼。要想扔掉一条忠诚的猎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我把屋檐下的狗棚拆了,把花鹰哄出家去,可它仍从篱笆洞钻进来,躺在狗棚的旧址上,气势汹汹地朝我汪汪吠叫,好像在责问我:你干吗要拆掉我的窝?
真是个十足的无赖,你是我花钱买来的,我有权要你还是不要你。驱逐出家门行不通,就把你送到森林里去当野狗。我用块布蒙住花鹰的双眼,借了辆自行车,一口气骑了十几公里,又爬了两座山,扯了根藤条把它拴在荒山沟的一棵小树上,然后不等它咬断脖子上的藤条,我就迅速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但第三天傍晚,我正在水井旁洗脸,猛然听到村口传来一串熟悉的狗叫声,接着,它像球一样滚到我面前,眼里闪烁着久别重逢的惊喜,激动得叫声都有点喑哑了,拼命朝我怀里扑,伸出长长的舌头,要来舔我的脸。
我火冒三丈,飞起一脚朝它的腹部踢去,这一脚踢得很重,嘣的一声,它像一只被铲中的足球,哀哀号叫着,滴溜溜滚出去,挣扎了好半天,才勉强站起来,身体朝左侧弯曲成三十度的弧形,怎么也伸不直了,痛苦地在原地转着圈。显然,我踢断了它的肋骨,我有点于心不忍,可转念一想,不来点毒辣,怎能摆脱它的纠缠?我狠狠心,凶神恶煞地冲过去,抬起脚来装着要再踢它的样子,它夹起尾巴,伤心地呜咽着,逃进竹林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它被我像打冤家似的打成伤残,大概会变爱为恨,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可我想错了,它并没有因为我踢断它的肋骨而舍得离开我,我只要一出门,就会看见它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我的视线内。它不敢再扑到我的怀里来,也不敢再走到我的面前来,它总是在离我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弯曲着身体,贼头贼脑地窥探。
我只要一看它,它就使劲摇尾巴,如泣如诉地汪汪叫,目光充满了委屈,弄得我心烦意乱,有一种被鬼缠住了的害怕和恼怒。我连最后一点怜悯之情都没有了,忍无可忍,滋生了一种想要彻底了结这件事的念头。
那天,我用芭蕉叶包了几坨香茅草烤牛肉,来到寨子后山的百丈崖上,悬崖极陡,连猴子都无法攀缘,绝壁上长着一些带刺的紫荆。不用说,花鹰还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后面。我用柔和的声调叫道:“花鹰,过来!”它毫不戒备地从灌木背后蹿出来,汪汪叫着,跑到我面前,尾巴摇得比纺车还快,眼里一片晶莹的泪花,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这笨蛋,以为我真的要和它重修友情呢!
我看见它毛发上粘满了树脂草浆,斑斑驳驳,活像条癞皮狗,肚皮空瘪瘪的,怕是好几天没吃一顿饱饭了。这倒给我的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掏出一块牛肉,浓郁的香味弥漫开来,花鹰兴奋得朝我拿牛肉的手乱扑乱跳。我躲闪着,慢慢向悬崖边缘移动。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态度突然变得亲切使它高兴得忘乎所以,还是食物的香味刺激得它无暇去观察地形,花鹰在离悬崖一尺远的地方还无所顾忌地蹿跳着。我用身体挡住它的视线,摊开手掌,用牛肉在它的鼻吻前逗弄了两下,然后突然将牛肉向悬崖外面抛出去,随即横跨一步,闪出一片空旷。花鹰纵身一跃,向空中那块牛肉咬去,它倒是准确地叼住了牛肉,可身体已完全冲出了悬崖。这时,它才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急旋狗腰,想退落到悬崖上来,但已经晚了,它像块掉进水里的石头一样,从悬崖上沉了下去。
唔,老天可以作证,不是我把它推下去的,我对我自己说,它是不小心自己摔下去的,不是谋杀,是意外事故!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不用内疚,当然也就不必担心它身上的阴气在它死后会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我身上,扎根在我家。
我等着听物体坠地的訇然声响,可我听到的却是狗的哀叫声。我趴在悬崖上,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一看,哦,花鹰并没坠进百丈深渊,它只掉下去一米,就被一叢紫荆挡住了。它的身体躺在带刺的紫荆丛里,四只爪子艰难地抠住岩壁,嘴巴咬住一根紫荆条。见我的脸从悬崖上伸出来,喉咙里发出咿咿呜呜的哀叫,眼睛里泛起一片乞怜的光,这种时候了,还不忘记朝我摇甩那条黑尾巴。
我知道,它这是在向我求救,我只要伸出一只手去,就可以把它从绝境中救出来,但我没有这样去做。我观察了一下,紫荆悠悠晃晃,承受不了它的重量,它咬着紫荆条抠着岩壁,也不可能坚持多久,迟早是要摔下去的。我放心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回寨子去了。
我没想到狗的生存能力这么强,当天下午,我从流沙河钓鱼回来,一进寨子的龙巴门,就撞见了花鹰。它浑身被紫荆撕扯得伤痕累累,鲜血几乎把身上的白毛染红了,嘴角处豁开一条大口子,含着一团血沫。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也许是用嘴叼着紫荆条,忍受着倒刺撕烂口腔的疼痛,一点一点从绝壁爬到缓坡去的。也许是像坐多级滑梯一样从上面这丛紫荆滑到下面那丛紫剂,终于滑出百丈深渊。
我没兴趣考察它的历险记,只担心它还会来缠我,但这一次它学乖了,也知趣了,看见我,不再摇尾巴,也不再柔声吠叫,一扭头钻进水沟,躲得远远的。这以后,它不再像幽灵似的跟在我身后了,也不再跑到我的屋檐下来了,有时偶然在田边地角相遇,它也只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眼光多看我一眼。谢天谢地,我总算摆脱了它的纠缠。
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到流沙河去游泳,四周不见人影,静悄悄的。我游进一片芦苇,忽然听见芦苇丛里嚓喇喇一阵响,一条两丈来长的印度鳄,张着巨嘴,朝我游来。印度鳄虽然体形庞大,可身子在水里却异常灵活,又扁又长的尾巴像支巨桨,轻轻一划,就像支箭一样蹿了上来,离我只有十来米远了。我还泡在河中央呢。我急了,一面奋力划动双臂,一面大呼救命。要命的是,这里离寨子有一公里多,我嗓门再大别人也听不见。我想,我马上就会被该死的印度鳄衔住一条腿,拖进河底的淤泥里闷死,然后被大卸八块吞进鳄鱼的肚子里去,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了。
我绝望地游着,叫着……突然,我听见一阵熟悉的狗叫声,抬头一看,花鹰气喘喘地出现在河堤上。“花鹰,快来救我!”我赶紧向它招手。它毫不犹豫地冲下河堤,扑通跳进水里,迎着我游过来。它因为断了肋骨,游泳的姿势很别扭,弯折着身体,像在跳水上芭蕾。它游得十分卖力,四条腿拼命踩水。
花鹰好像从来没有和我闹过什么不愉快,好像彼此之间从未产生过隔阂,贴到我的身上,黑尾巴从水里竖起来,朝我摇了摇,用圆润的声音汪汪叫了两声,似乎在说,主人,你别怕,我来了!然后,它转过身去,冲着印度鳄发出一串猛烈的咆哮,似乎在说,你这个坏家伙,有我在,你甭想伤害我主人的一根毫毛!
花鹰为我挡住了印度鳄,为我挡住了凶恶的死神。
我爬到岸上,才敢回头去看,但什么也看不见了。茂密的芦苇遮断了我的视线,只听到芦苇深处传来狗的吠叫声和撕咬声,传来鳄鱼尾巴的搅水声……
我回到寨子,立刻动手在我的屋檐下搭狗棚。我要用草药接好花鹰被我踢折的肋骨,用香皂洗去粘在它身上的树脂草浆,煨一锅红烧牛肉滋补它虚弱的身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它离开我了,我想。
我把狗棚盖得特别宽敞,大得连我都能钻进去睡觉。我觉得我应该和花鹰颠倒一下位置,我只配做一条狗,而它,完全有资格做一个人。
我守在新盖的狗棚前,等着我的花鹰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