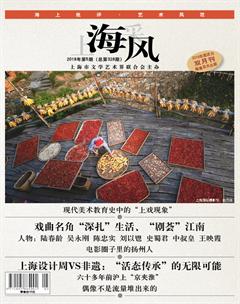赵松涛:我想在没有相声的城市做相声
木曰雨
“读经典,要感谢孔夫子这位好老头儿;读经典,要把每一句‘子曰记心头……”田耘社相声剧《子曰》,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届上海孔子文化节上颇为抢眼,它作为开、闭幕的重要节目在文化节上首尾呼应。
纪念老夫子,按理应该是庙堂之高的严肃场景,怎么会上演属于江湖之“娱”的一出相声剧?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让人有点费解。
其实,看名字也可以猜到,《子曰》当然是“孔子题材”,但想象之中,它应该很难与相声这种艺术样式、表演形式完美结合。难道从孔夫子的语录中可以发掘什么搞笑的段子?还是他和弟子之间有令人捧腹的奇闻轶事?至少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里读过的有限篇章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据该剧的创作者、田耘社创始人赵松涛介绍,《子曰》是在相声表演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戏剧的舞台调度手法,在说和演的过程中,讲述孔子的家族衍变和家庭身世,展现了凡夫孔丘到圣人孔子的成长轨迹。他创作《子曰》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中国人从走近孔子、了解孔子到践行孔子的哲言。
做体现上海城市品质的相声
赵松涛不仅是个优秀的相声演员,而且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相声团队经营者。别人问他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相声是北方曲艺,在上海能做起来吗?他的回答牛气得让人难忘:我想在没有相声的城市做相聲。
在赵松涛看来,与其说是他选择了上海,不如说是上海选择了他。
与上海结缘,始于当兵五年。因为在二军大服役,而熟悉上海,爱上上海,退伍后很自然地留在上海,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成为一名新上海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他都感觉自己深深地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甚至连饮食都很习惯。从思想情感到物质生活,从各种社会关系到妻儿老小都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的赵松涛,已经很难舍弃魔都这个第二故乡。
然而,这些对把相声事业放在第一位的赵松涛来说,都还是次要的。他最在乎,或者说最费思量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南方的时尚之都发扬北方的传统曲艺。
当然首先要回答,有没有可能。
赵松涛的答案能条分缕析地说出一二三四,显然早已经过深思熟虑。
所谓北方曲艺甚至说外来文化,一定可以在上海扎根。这是赵松涛斩钉截铁的判断,也是他作为新移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所作的果敢结论和优质评价。
理由当然很充分。第一,国家推广普通话这么多年,对国策执行一向认真到位的上海人,经过几代人不折不扣的“推普”,现在反而“上海话”成了濒临灭失的方言、需要拯救的对象,所以,凡是以普通话为主的艺术形式,在上海不会在语言上产生任何障碍。
其次,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的同时,也在消弭地域的隔阂,地球缩小成了“村”。互联网把各个地域的文化放在了一个大家都能随时随地取阅的大平台上,随着人们见识的不断增长,文化之间的差异会让人感觉不断缩小。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特征中有着非常显著的码头文化的基因,所谓海纳百川已经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文化消化功能。
第四,相声以及快板书本身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适应力,它们曾被视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短小精悍的作品形式本身就决定了它们的题材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动多变。
赵松涛看好相声在上海的成长前景,因而决心创办田耘社,让憧憬多年的理想照进充满挑战的现实。规范、时尚、多元、执著,是赵松涛总结的上海城市品质,也是他想要通过他的相声作品向世人传达的上海精神。
或许正是这股因为热爱上海而礼赞上海的创作冲动和理念,促成了一份“小剧场相声”的合作案,沪上重要文化地标之一的上海文艺会堂为扶植体制外青年文艺工作者,助力田耘社从“江湖之远”跑步进入“庙堂之高”。要知道位于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曾被誉为文艺家们的“家外之家”,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曾在此与海上文艺家们座谈联欢,如今亦是著名作家、书画家、影视戏剧曲艺表演家、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们常来常往、相聚相会之地。
田耘社“小剧场相声”在文艺会堂的驻场演出,既让赵松涛受宠若惊、与有荣焉,也让他如履薄冰、倍感压力。
传统相声谁都能说,为什么非要听田耘社的?赵松涛经常用这个问题拷问自己和团队。这个问题有点类似郭德纲的段子: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为什么你花钱听我说话?
赵松涛的答案是四个字“人有我无”。他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第一不稀奇,唯一才可贵。虽然田耘社是上海第一家民间相声团体,但赵松涛一直不喜欢以此作为“看点”“卖点”。“你老说这个没什么意思,得到‘第一的那一刻转瞬即逝,诞生先后的事是将来研究理论和历史的专家应该关心的,‘第一与生存质量和生命长度并没有直接关联,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唯一,这是需要执著精神的。”赵松涛认为,当你足够执著,执著到别人都不执著了,那么你就成了“唯一”。
当然这种“战斗到最后”的“唯一”,是体力、耐力、意志力层面的比拼结果,更重要更常态的比拼是智力、眼力、能力的PK。当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当别人还没因为种种原因退赛或牺牲的时候,如何棋高一着?
赵松涛与众不同的追求“唯一”的路径便是他深谙“因地制宜”的创作法门。既然田耘社驻场文艺会堂推周六小剧场相声,那么在后续新作品创作上,是否可以跟文艺会堂的所在地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属的每个文艺家协会进行深度合作,创作出一批能反映各个领域的上海艺术家风采的相声作品呢?
“想到这个点子,我整个人都很兴奋。我设想,在这样的交流和创作过程中,既能和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广交朋友,又能创写反映他们生活和创作现实的相声作品,岂不是有利各方的多赢好事?”赵松涛设想,每场演出前的五分钟,可以增加一个小快板节目,每次唱一位上海艺术家的成长轨迹、创作心迹或者专业成绩。别看五分钟只有一小段,坚持做下去,就能积累下来一套成系列的好作品。
赵松涛非常明白,相声跟其他表演艺术有个相同的问题:如果作品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地域环境而推陈出新,那么其生命力就会变得日渐脆弱,最终被广大观众抛弃而成为新的“非遗”。
迎合不易,引领更难
相声的核心技巧是要在剧场这个规定空间里带动观众进入规定情境,一块完成艺术创作。或者说,相声是一种互动的艺术,必须让观众一起参与创作。
这就要求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具备某种“内在联系”,演员要想办法在台上体现自身的价值。赵松涛说,好的表演作品里面一定会有各种“知识点”,演员千万不能假设观众不知道,而要站在平等立场上,假设观众都知道,这样与观众的距离才能自然拉近。“我师父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个观念,观众就是老师,是评委,是上帝。”赵松涛说。
作为田耘社的负责人,赵松涛对团队的要求极其严苛。他透露,他正在酝酿一套“田耘社相声规范”,规范到什么程度?具体到话筒怎么摆放也要“有规矩”:什么高度,什么角度,都要讲清楚。“一定是在不影响收音效果的前提下,话筒架收缩到最短,目的是尽可能少的遮挡演员的表演,尤其不能遮挡脸部,”赵松涛举例道,“桌子上的两条手绢、两把扇子和一块醒木又该如何摆放?原则是在桌上的投影面积最小,因为在表演过程中,这些东西不恰当的摆放和铺排也容易分散观众注意力。”
演員的服装也需要规范,赵松涛认为如果大褂的颜色过于鲜艳,观众一场节目看下来,视觉上一定会产生疲劳感,会觉得扎眼。“有的演出,背景是红的,桌子是红的,衣服是红的,简直就要着了!缺乏舞台美感。”赵松涛对舞台呈现的要求,真可谓是武装到牙齿了。不仅演员穿着打扮要一丝不苟地讲究,例如衣服与鞋袜的搭配,演员发型的规范,还有演出一律不戴眼镜,就连检场的工作人员都得穿着统一的大褂,不能随便对付。
对穿着都如此讲究,对作为语言艺术的相声来说,语言规范方面的“洁癖”那就更为“严重”了。
在赵松涛看来,在不涉及制造和组织包袱的一般叙述中,一定要用最好的、最讲究的语言。例如什么地方用“大家”,什么地方用“诸位”,什么地方用“各位”,这都需要斟酌和规范。
“我们对自己的语言规范提高了,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就会随之提高;观众要求更高了,反过来又会对演员的语言层次有促进作用。我们希望田耘社的观众逐渐形成这样的认同,就是你凡是在舞台上听到莫名其妙的‘屎尿屁‘我是你爸爸‘你媳妇如何如何就会觉得不对、难受、低俗。”
虽然赵松涛看起来像是个身段柔软、八面玲珑的人,但在一些事关相声行业走向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个不妥协的人。他坚持相声不能一味迎合观众,要引导市场,不能为了笑声放弃格调。田耘社就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尝试做最大的引导,“能带过来一个是一个”。虽然从市场号召力、业界影响力以及流量吸附力而言,田耘社或许不是最强大的,但只要坚持做自己的品质,长此以往,一定会有看得到效果。
竹韵板情,师徒情深
7月21日,田耘社在文艺会堂的第一场演出,赵松涛请来了师父张志宽,还特地在自媒体上打了广告“师父来了”!当天,73岁的张志宽先生表演了长达18分钟快板书《武松打店》。8月初的表演,老艺术家又被赵松涛请来撑场助兴,用相声的手法师徒三代演了一出《竹韵板情》。
作为张志宽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之一,赵松涛说起师父来,话头完全收不住。
1992年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牡丹奖、金唱片奖,首届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曲艺界七位之一),快板书开创者李润杰先生弟子,也是公认的当今快板书艺术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对师父的成就和地位,徒弟如数家珍。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成就和那么高的地位,但年届七旬的张志宽在快板书的推广普及和教学传承方面所作的贡献,如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赵松涛一直戏谑师父“大学教授去教1+1=2”:“只要问他快板的事,绝对有求必应。跟师父学过快板的人不下几千,如果算上辅导讲课,那就要好几万了。”
回忆与师父张志宽的缘分,时间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赵松涛清晰记得,那是1997年,他在连队里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快板大王张志宽》,文章里张志宽的头衔他至今记忆犹新——“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天津市曲艺团业务副团长”。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寻呼机都是那个时代的通讯新宠。赵松涛就这么慕张志宽大名拨通了“022-114”——天津长途查号台,虽经曲折,但还算顺利地问到了天津市曲艺团和张志宽办公室的电话。赵松涛向张志宽作自我介绍:我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名战士,特别喜欢快板,想跟您学。对方问:“你学过吗?”赵松涛答:“没学过。”“有板儿吗?”“没有。”“那我给你寄副板儿。”
就这么干脆,就这么爽朗,三盘录音带连同一副快板很快就寄到赵松涛的手里。当年的这三盘录音带是张志宽在1994年在甘肃录制的,加一块大概有十来段快板书作品。“就是这三盘录音带,对那个年代的快板书爱好者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赵松涛说。
7月21日那场演出,赵松涛的不少朋友来捧场,演出结束晚上跟师父张志宽一块吃饭,相谈甚欢,饭后大伙儿合影,张志宽一点人数,宣布“我代表徒弟赵松涛送你们每人一副快板”。20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爽。老爷子看到有人支持赵松涛和他的团队,热爱曲艺,就打心底里高兴。
当年,赵松涛收到张志宽寄来的快板和录音带后,就听着录音自己琢磨,自己练。当时赵松涛在长征医院刚启用的新大楼里看车库,就在看车库的这段时光,赵松涛天天一个人听录音,还不时给张志宽打电话、写信请教。
1999年,天津市曲艺团、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天津市曲艺家协会,举办全国首届快板书培训班,老先生给赵松涛寄来了招生简章、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封信,嘱咐赵松涛一定要来这个班。
当时赵松涛是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勤务中队的车辆调度员,他找勤务中队队长告假。队长知道赵松涛要脱产两个月去学快板,觉得他简直疯了!因为当时勤务中队年中和年终总结报告,都出自赵松涛的手笔,赵松涛一走,中队的笔杆子没了。赵松涛再找政治部副主任,给他看了招生简章、录取通知和张志宽的信,没想到主任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在天津为期两个月的学习,赵松涛如鱼得水,也坚定了走曲艺之路的人生方向。
记者:相声是舞台的艺术,但眼下不少知名相声演员都活跃在电视上,你怎么看?
赵松涛:这完全取决于演员本人的价值判断,就是回答“你要什么”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媒体和信息社会,在坚守剧场的同时,也必须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和平台来推广。比如田耘社,除了在正规的剧场演出,还积极地下基层、进社区、去高校,这些也都属于舞台演出的某种形式。
我师父他们当年的舞台演出的精湛技艺是被“计时收费”逼出来的。当时的茶馆剧场,从下午2点演到晚上10点,门票上都有明确时间点,收费是按照实际在场观摩时间来的。这8个小时的节目是循环演出的,每个人大概要登台四五回。第一天唱《武松打虎》,观众觉得挺新鲜;第二天还唱《武松打虎》,观众可能还凑合着听一回;第三天再唱《武松打虎》,肯定有人出去抽烟了。一出去,就把账结了,待会儿进来,再重新开始计时收费。所以,这种计时收费要求演员得“会得多”,每天得换着演,逼得演员一年至少得有30个大段,每天演2段,至少可以半个月不重样。
记者:你是怎么和相声结缘的?
赵松涛:从小我就喜欢听相声,觉得特别好玩、可乐,同样的故事情节经相声演员这么一说,怎么就和看到的书本上的故事那么不一样?
后来,我当了兵,来到了大上海,一呆就是十多年,在部队期間,我也没有停止对相声的喜爱,还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景寿的无私帮助,接触到了相声历史,了解了一些相声创作规律,也找各种机会看了不少传统相声节目,发现了相声背后真正吸引我的东西,不仅是说学逗唱,更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风民俗、人文情怀。
后来,我主动联系到了我的恩师,魏文亮先生,他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徒弟,于是很快我就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相声,于是,2004年8月,从部队退伍,又经历了看似稳定的工作之后,我最终决定辞职出来全职做相声。
算起来,从在部队工作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相声算起,我在这个行当里已经13年了。
记者:最难忘的学艺经历是什么?
赵松涛:从开始到现在我的学艺经历都挺难忘的,想想我和相声的关系,就好比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最后却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业,从事了这个专业,并将此确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一路都难忘。
但是最难忘的还数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汪景寿教授之间通信的那段岁月。当时的我没书,没资料,没学习方法,出于热爱,我仅凭满腔热情,给老先生写了求教的信。没有想到老先生不仅亲自给我回信,还给我寄了很多很多资料,这些资料直到今日,可以说都是相声艺术史上堪称一流的专业著作,有《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曲艺概论》等等,那时候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不懂的地方再写信问,就这样一直自学着到了今日。所以我今天所建立起来的相声观和那会都有关系。
记者:台下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赵松涛:其实我平时挺不“相声”的,台上我能又说又唱,又蹦又跳,各种神态表情,眉飞色舞,生活中我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喜欢在家看书、看电视、听戏、喝茶、养花、养猫、约朋友一块聊聊天,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出去玩,不喜欢出去旅欧啥的,有时间就喜欢——呆着。
现在我已经四十不惑了,人生到这个阶段于我而言就是凡事都应该简单一点,用中医的方法来过日子,中医讲浅淡虚无,人不能太争强好胜,不能索取得太多,渴望得到的太多,老话说:“出来混是要还的。”得到的多,还的自然也多,另外还得顺应自然规律,天亮了就该起,天黑了就该睡,这个季节长什么就吃什么,不要违背规律,不要违背天地的自然法则,老老实实地做人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