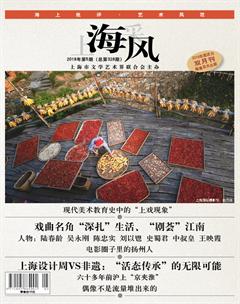“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6月9日,打开手机,惊悉香港老作家刘以鬯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发《2046》中的经典台词“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表示哀悼。我想起与刘先生的文学情缘,不由得悲从中来。掐指算来,认识刘先生,至今刚好30年。尤其在1988至1995年期间,我的文章经刘以鬯先生之手发表在他主编的《香港文学》和《星岛晚报》等报刊上的,就有十七八篇之多。后来他从《香港文学》社长兼主编任上退休后,还给我留过他家的电话。可惜后来他耳聋得厉害,打电话问候他也听不清是我,联系便中断了。今年上半年,突然接到香港一位孙先生的电话,说要为刘以鬯先生的百年华诞出一本书,是刘先生给了他上海的我家电话。他想要我作陪去访问刘家的上海故居,刘先生告诉他,是我替他找到了上海的老房子,拍了许多照片寄给他的。可惜孙先生打算来沪的日期我恰巧不在上海,所以没答应陪同。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刘以鬯先生就驾鹤西行了。
初识刘以鬯
说起我与刘以鬯先生的海上文学缘,还得从30年前说起。那时,我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年轻讲师。一个偶然的机会,系里要我开设一门“台港文学研究”课程,供中文系和全校学生选修。我手头毫无资料积累,一筹莫展之际,正巧复旦大学举办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台湾版《游园惊梦》的录像观摩和研讨活动,邀请钱谷融先生出席,钱先生有事不能去,便派我代表他前往复旦大学。那是1988年初。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台湾版话剧《游园惊梦》的演出实况录像,深深地为《游园惊梦》的精彩剧情和演员的精妙演技所叹服,回家后就写了一篇有关话剧的评论《戏内套戏,梦中蕴梦——论白先勇及台湾版话剧〈游园惊梦〉》,写完之后,也不知该投给哪家报刊,搁了一段时间。不久,便收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研究中心主任刘兆佳教授的邀请函,邀请我于年底赴港出席“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撰写论文翻阅香港报刊时,发现了1985年创刊的《香港文学》,便试着把那篇拙作寄给了主编刘以鬯先生。真没想到,从未谋面的刘以鬯先生,竟然把我这个无名之辈的文章配上了《游园惊梦》的演出海报、剧照等发表在当年《香港文学》7月号上。
1988年12月,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刘以鬯先生邀我到坐落在湾仔摩利臣山道38号文华商业大厦顶楼的《香港文学》编辑部去做客。还没进门,他已在门口迎候,先让编辑部的杨先生替我在挂有“《香港文学》杂志社”字样的牌子旁拍了一张照。这张照片刊登在第50期《香港文学》封三,还注明:“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易明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钱虹来港参加‘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曾与本港文艺界朋友就文学上的问题进行交流,并收集有关港台文学的研究资料。”后来,我每次访港,到《香港文学》杂志社去见刘先生,他都会让人替我在此牌子旁拍张照,然后刊登在《香港文学》的封二或封三并加以说明。他主编《香港文学》时,封二封三上辟有“香港文学活动掠影”栏目,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传递有关香港本地的各种文学活动及海内外文学界人士访港交流的信息。这是刘先生主编《香港文学》时形成的一个文学传统,一直坚持到他从社长和主编的任上退休。他退休后,《香港文学》就改版了,封二封三也没有“香港文学活动掠影”栏目了。
那天是第一次和刘以鬯先生见面。他一见了我,便跟我講起了沪语,并且还操一口与我们年轻一辈所说的上海话不太一样、带有尖团音的正宗沪语,比如,他说“我们”是“我伲”而非“阿拉”,“我爸爸”是“伲爹爹(读dia音)”,“从前”是“老底子”,诸如此类的老上海话,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人早已不会说了,所以我听来倍感新奇。交谈中,得知他于1941年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后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文科大都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故而他与我,算起来还有一层“校友”之缘,虽然前后相隔了整整40年。我之所以敬重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以鬯的名字是施蛰存先生跟我推荐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大同大学附中念书时就已在上海滩《人生画报》上发表过少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写一个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贵族女子面临困境的故事。当时漫画家华君武专门为此作了三幅插图。那时,他不过是个十七岁的文学少年。他写诗,写小说,后来收在《刘以鬯卷》“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中的《沙粒与羽片》《七里嶴的风雨》等作品也表明了他具有的创作才华。至于他赴港后写出《酒徒》《对倒》等“现代现实主义”(这是刘先生一贯倡导的)小说,从而启发了王家卫拍摄出《2046》《花样年华》等“前卫”电影,更是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了。
怀正文化社
但我有些不明白的是,刘以鬯先生抗战胜利后很少写作,他一边上班谋生,一边却“为他人作嫁衣裳”:在上海创办并经营一家出版社。刘先生2010年7月27日在《东方早报》上回忆道:
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那时候,上海和国内其他作家们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比如抗战的时候,有个出名的年轻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国际饭店来见我。我很欣赏姚雪垠的小说,我问他,“你在上海住哪里?”他说,就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就帮他出书,还对他说,“你就住在我出版社里。”他就住在出版社书库里,也在里面写稿,和我们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
这家出版社名叫“怀正文化社”,规模虽然不大,名气也不算很响,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那样一种战乱频繁、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竟出版了徐訏的《风萧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巨著,此外还出版了诸如姚雪垠的《雪垠创作集》(四本)、熊佛西的《铁花》、许钦文的《风筝》、王西彦的《人性杀戮》、丰村的《望八里家》等文艺书籍。施蛰存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他四十年代的一本散文集《待旦录》,就是1948年怀正文化社出版的。事隔40多年之后,年逾八旬的施教授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往事。当时,出版社就设在刘以鬯家里。据说“怀正”这一名称,也是源自刘家“怀正堂”之堂名,取其“浩然正气”之意。至于将出版社改名为文化社,则是徐訏的主意,他认为这样业务范围可以更宽泛一些。
怀正文化社成立后,不但为作家出版书稿,还为作家提供过清静的创作和居住环境。比如刘以鬯先生提及的姚雪垠,当时就曾住在刘家的二楼(即刘先生回忆中提到的“书库”),并创作和修改了《长夜》《差半车麦秸》《牛全德和红萝卜》等现代文学名篇。我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自然对此怀有某种既是职业的也是个人的好奇感。我问及怀正文化社后来的境况,刘先生摇头作答:“四十年代末,通货膨胀,物价涨得太厉害,怀正文化社陷入空前的经济困顿之中,放出去的书账根本收不回来,实在无法继续维持出版业务,只得离沪赴港,另谋发展。谁知此一去就是整整四十年,再也没能回过上海。”听了这番话真令人感伤。回到上海后,我就想去刘家旧居一趟,亲眼见见当年的怀正文化社是什么模样,无奈当时忘了问清路名门牌。事情一忙,也就搁下了这一念头。
旧居“拆除”了?
1989年四月初,我应邀去复旦大学出席“第四届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巧遇香港大学讲师梁秉钧(也斯)先生。他说行前受刘以鬯先生的委托,要去刘家旧居(即怀正文化社旧址)拍一些照片,请我和陈子善先生做向導带路,我欣然奉陪。会议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们乘一辆的士从复旦大学东苑宾馆出发。正值清明时节,细雨蒙蒙,竟如天地间垂下千万条雨线,总也扯不断似的。梁先生掏出一张刘先生草绘的地形简图,上面写的是几十年前的旧路名,明确标示出刘家旧居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交界处附近,门牌为“江苏路559弄99号A、B”。梁先生解释说,刘先生关照说他的旧居为一幢独立的两层楼花园小洋房,在进弄堂靠左手一侧(后来我才搞清楚,刘家旧居应该是三层楼的花园洋房,且在进弄堂靠右手一侧)。
过静安寺,越愚园路,转眼便到了江苏路。我们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一头扎进雨的世界,开始寻找。沿着门牌数过去,又数过来,不禁傻了眼:原来江苏路上压根儿就没有559弄,靠近延安西路口的弄堂倒是有一条,但那是563弄。此弄左右两侧皆已成篱笆墙围起来的建筑工地,高高的脚手架迎街矗立,脚手架前的巨型广告牌上一条醒目标语赫然而现:“建设美好的明天!”一打听,才知这一带旧屋已基本拆除,废墟上将耸立起新的高楼大厦。难道整条559弄全被拆除了?我们想问个明白。好不容易找到马路对面的江苏路地段房管所,谁知那天恰逢星期日不办公,房管所内连个人影都没遇见,我们只好失望而返。梁先生翌日即离沪赴杭,无法再来此寻访。这次未能了却刘先生的心愿,我感到有点内疚,便抄下刘家旧居的地址,以便日后重来。
山穷水尽处
转眼便到了五月中旬。我捡了个没课的下午,推着自行车走进江苏路派出所的大门。到户籍科一问,原来江苏路559弄就是现在的563弄。我一阵惊喜,庆幸那条弄堂总算还在,便趁机打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99号户主是否姓刘。一位年轻的户籍警瞟了一下我的工作证(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唯有工作证可以证明我是高校教师的身份),请我在柜台外面稍候,便从身后的大木橱中取出一摞厚厚的户籍登记簿,刷刷地翻起来。过了一会儿, 他抬起头望着我:“对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559弄99号的户主不是姓刘。”(后来刘以鬯先生告诉我,这幢住宅是他爹爹在战前买地为他兄弟两人建造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业主唯恐越界筑路的房地产被敌伪没收,都找外国人在律师楼做假的转让手续,而产业的所有权仍归原来的业主。他爹爹也曾将那幢房屋与邻近一位美国商人在律师楼做过这种手续。一九四八年,他兄弟二人离沪后,此宅由他母亲住过一阵,但不久其母搬去愚园路,后来就回到浦东老家直至临终。所以,户主不姓刘也是真实的。)
我转念一想,还是去原559弄实地考察一下。我踏进江苏路563弄。这条弄堂当时已经徒有虚名,与其说是弄堂,不如说是过道更恰当:长不过百来米,两侧全无“鸡犬之声相闻”的住家。前半条弄堂已与两旁的新大厦建筑工地连成一片开阔地,后半条弄堂内,靠左手一侧早已辟为电话局仓库,仓库延至弄堂笃底,便是上海金属品厂的厂门,上面没有门牌。紧挨着厂门的右手一侧,有一幢三层楼的灰色楼房,绿色的爬墙虎攀援而上,爬满了朝西的整面灰墙。灰墙外的一扇铁门上,挂着“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的牌子。一看门牌:“42号”,离99号还远着呢,可此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奈之中,我突然想起,应该去江苏路地段房管所查询一下,99号是否早已被拆除,他们那儿兴许会保存该地段的房屋原始资料。
我二进江苏路地段房管所。一位热情的小伙子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他即找出几张本地段房屋建筑平面图,指给我看,弄堂笃底的上海金属品厂即563弄101号。除此之外,就是弄堂右手一侧的42号了。据他估计99号早被拆除做了电话局的仓库。我又问他能否找到拆除前的99号房屋结构图?他答,对不起,这里没有保存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但他很快又热情地建议我到武夷路234号长宁区房地局资料室,那里可能会有我要找的图纸。我谢过他,原路退出。不知不觉又走进了563弄。既然101号还在,那么99号应当就在它附近!不知为什么,我总不相信99号会凭空消失。凭着一种朦胧的直觉,我感到刘家旧居并没有被拆除,它应该还在人间,我决心走访此弄的知情者。
我走进42号“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传达室,询问有谁熟悉此弄的变迁,传达室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用手一指,示意我上楼直接找学校负责人。我在三楼亭子间找到了一位该校负责人之一(据说是该校的党支部书记)。她是一位和气的中年妇女,听我说明原委,摇摇头说自己刚调来不久,全校数李校长在此工作时间最久,他比较熟悉此地的情况,但很不巧他外出开会去了。我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得告辞而返。
柳暗花明村
谁知这寻找怀正文化社旧址的事情一搁便是一年多。直到1990年10月,我二度应邀赴港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再次拜访刘以鬯先生时,才又重提此话。这次交谈,我证实了自己那种朦胧而执著的直感:怀正文化社的旧址即563弄42号的那幢三层楼房。第一,刘先生说,我在上海的旧居不是两层楼而是三层楼;第二,此住宅在进弄堂的右手一侧而非左手一侧(我回沪后拜访施蛰存教授时,他也证实怀正文化社旧址肯定是在弄堂右侧的三层楼房内)。
于是,临近岁尾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又来到了江苏路563弄42号。这次正巧,在“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传达室遇到一位姓张的老校工。他本早已退休,如今返聘回校,在教务处帮忙。那天正巧他在传达室代人值班。我一提这幢房屋的来历,他如数家珍,细细道来。他说,这里正是你要找的“江苏路559弄99号”原址。我如获至宝,忙向他请教:据说99号有A、B楼,各有大门进出,为何现在只见一扇大门?他解释道:99号其实是两幢建筑结构、式样完全相同的连体三层楼房,中间有平台和过道相连,既互相沟通,又彼此独立,各有一个门房间和汽车间,故有A、B楼之分。他领我沿着楼房的外围走了一圈,一一将原物指给我看。西侧的门房间经扩建后即是现在“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传达室,而东侧的门房间现改成了洗手间。他把我带到B楼宽阔的廊檐下,指着那扇被堵死的大門说,东大门是因为隔壁101号上海金属品厂扩建而被堵死的,因此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里原有两扇大门进出。早先的101号是一家私人老板开的弄堂小厂(作坊),叫做“久成别针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与另一家合成揿钮厂合并,改称“上海金属品厂”。厂房几经扩建,便把99号的东大门堵死了,只留西大门进出。
我们慢慢折回来。楼房前面是一块狭长的水泥平地,显得零乱而又局促。我又问他,听说这里原先是花园洋房,怎么不见花园?他带着惋惜的神情答:是呵,这里从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园内还有假山、水池,很漂亮的,但在“文革”时期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全被推倒填平了。“文革”结束后,该校又在其上面加盖了一幢两层楼的物理实验室。我看了一眼那座大煞风景、毫无美感的新楼,上面挂着一块“上海振宁机械厂”的牌子。他摇着头叹息:弄得天井不像天井,空地不像空地。
说话间他领我上楼,走遍各层楼面。A、B二楼的房屋结构基本上都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是大多数房间摆满了课桌椅,成了传授知识的殿堂。走廊很宽,木扶手上有镂空的花纹,都保留完好。在走廊尽头,正巧遇到了上回未遇见的李校长。他指着玻璃窗下面对我说,这里原先都有烧柴油的暖气热水汀,冬天整幢楼房都暖融融的,后来都被拆掉了。我从A楼走到B楼,又从B楼回到A楼,从各个角度寻找可拍摄的旧物。在A楼的三层楼上,我发现朝南向阳的一间大房间已被装潢一新,这是一个套间,里间摆放着几张写字桌,桌上堆满各种已批改和待批改的作业簿,不用说,这便是教师办公室了。装潢一新的是外间,门框上方挂着“教工之家”的匾额。“教工之家”布置得很整洁,给人以既温馨又亲切的感觉:沿墙摆放着几张沙发。正中有一张长桌,十来张折叠式靠背椅围桌而放,桌上摊开着近日的报纸和新出的杂志。我坐在桌旁环顾四周,竟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坐在怀正文化社那帮年轻的文人中间,听他们围坐在这里谈文论艺。历史与现实,在这幢保留完好的旧址内竟是这样不可思议地连在了一起。
我紧紧地握住李校长和姓张的老校工的手,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想起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想尽快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寄给远在香港的刘以鬯先生——怀正文化社的创办者、这幢楼房的旧主人。不知他见了这些照片,会有怎样的感慨。照片,终究是平面的,我衷心希望,离沪已四十多年的刘先生能回到当年的旧居来亲眼看一看,这里,有他青年时代灿烂的梦想和事业的根基。
这些旧居照片寄去香港不久,就收到了刘以鬯先生的亲笔信,他说看了这些旧居的照片很激动,流下了眼泪。他信中除了表示感谢外还说,一定要回上海来看看。后来他又寄来了他在香港三联书店新出的《刘以鬯卷》,并在扉页上题词签名相赠。《香港文学》1991年五月号上刊发了拙作《为了“拆除”的纪念——怀正文化社旧址寻访记》,同时配上了我在1990年12月寻访旧址时在刘家故居前的留影,以及当时拍摄的旧址照片。
我后来看到了2010年7月27日《东方早报》刊出的刘以鬯先生口述:
十多年前回上海过一次,你说跟过去不同,也可以,你说跟过去很相似,也能说。……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应为忆定盘路,估计可能是记录有误,即今江苏路——笔者注)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十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学校了。
确实,这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寻访到了刘家故居后告诉刘以鬯先生的,有照片和那篇拙作《为了“拆除”的纪念——怀正文化社旧址寻访记》为证。如今,百岁高龄的刘以鬯先生也许真的又回到上海的家了。因为这里,有他青年时代灿烂的梦想和事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