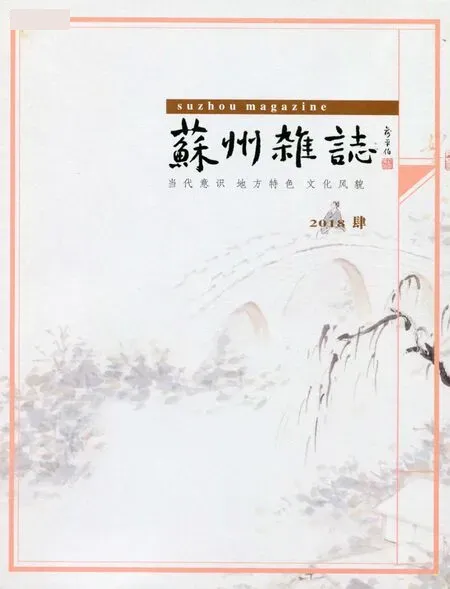戏画记(四)
林继凡 陈未沫
陈:林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好奇,这期开头,就先问问您:您的名字里有个“继”字,但听说您并不是昆曲“继”字辈,这是怎么回事?
林:从62年我开始和比我高了半辈的张继青搭档,那时候就不准唱古装戏了,全部排现代戏,我不是第一正派就是第一反派;后来我就一直和她搭档,林继凡、张继青,名字一直一起出现,所以不少人都以为我是“继”字辈的。实则不然,我和“继”字辈的人差了半辈,他们是55年学戏,我是60年(学戏)了。我只是碰巧名字里有个“继”字,我这个“继”是我们林家的“继”字辈。
陈:结果就这么巧,到了昆剧团,您又学得快、进步快,最后反倒和“继”字辈一起演出了。
林:对。我从61年年底脱颖而出后,就开始和他们合作了,从那个时间到我开始学戏,其实只用了一年半不到一点。然后就开始唱现代戏了,那时还没有样板戏,都是创作一些和生活结合的、英雄人物故事,比如雷锋、王杰。我们当时就排过一出王杰的戏,我演王杰。之后一直到样板戏出来,江苏省苏昆剧团接近要解散,全国昆曲都解散了,江青一道命令,只抓京剧。其实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恨昆曲?她说过一句话:“昆曲是僵尸,昆曲,给它生命也没用。”后来我们了解到,江青小时候学过昆曲的,她家里也有人唱昆曲,谁知道到了文革她突然转变说要“枪毙”昆曲。当时她第一个就把北昆解散了,她把北昆几个好演员弄到《奇袭白虎班(团)》剧组和《沙家浜》剧组。我们剧团当时面临解散了,所有演员集中到南京农学院,省里是重视昆曲的,就想让昆剧团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说试试看,看看有没有观众。用了半个月排了出来,演员选了我,团里找我谈话,说我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好,按道理是没资格演的,但是因为我表现不错,艺术上优秀,现在用人之际考验我,看我能否担当。
陈:您是怎么想的呢?
林:我当然觉得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这等于要背负起整个昆剧团的命运。大冬天哦,冰天雪地的,没日没夜一个礼拜,总算把戏排出来了!结果我就落下个后遗症,失眠。直到现在也是。
陈:时间赶,任务重,身心俱疲,再加上压力这么重,您也是不容易了。
林:我的失眠基本都是因为戏。后来就是不能想到戏,不能想到这些事情,一想就会失眠。像你说的,压力实在太大,排不好戏,剧团就要解散,这是怎样的责任啊?!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拼命。
陈:排的是什么戏?
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男一号——杨子荣。唱出来反响是好的,因为我是武生底子,形象、气质、功夫都是可以的,唱出来,竟比省京剧团几个演员都好,很受喜欢。一天唱两场,很辛苦,但也是一种锻炼。
陈:所以您的行当很宽,武生、小生、老生都能上,可塑性极强。那么这次您把杨子荣唱红以后,剧团是不是就能避免解散了?
林:对啊,不用解散了。然后我就遇到了第二个转折,1968年所有昆剧团都解散了,只有江苏省没解散,对上头总要有交代,于是领导决定让我们下放到苏州。1972年年初春节的时候,剧团安排我们在石路鸭蛋桥那里的人民剧场(表演)。我到石路没几天,一个礼拜不到,石路上的人就全都认识我了。那时候戏少,看戏很闹忙。
陈:那时候的演员,昆剧也好,评弹也好,都相当于现在的明星啊。
林:是啊,很多人都来看,甚至翻墙头也要来看。当时唱的都是现代戏,《风华正茂》《雪山风云》等等,根据歌剧、话剧改编,那些戏都是大火,场场客满。我们唱的都是昆歌,曲子都很好听。后来石路上的店,肉店、鱼店、水果摊、糖果店,只要我去买东西,都不肯收我钱。夸张到去买肉,扔给老板5块钱,他给我一大只蹄髈,还要再找还我10块钱。
陈:卖东西不收钱,还要贴钱给你。
林:为什么呢?就是喜欢你演戏,喜欢你演出的人物啊,要和我交朋友。所以最后流传一句话,叫做“林四亿”,说那时候全国八亿人口,林继凡认识一半。还有一句话:不认识林继凡的人,还没出道呢。那五年里,我确实是不断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那时候昆剧、苏剧我都唱,形势很好。这一段也成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得以陪伴我爷爷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几年,送他终老。
陈:您是真孝子。你们当时住在哪里?是团里统一住宿,还是?
林:我们住在西园新村,那是苏州第一批公房。当时我们团下放苏州,苏州领导算是很重视了,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小户、中户、大户。小户进去两户人家,一间小房子,没有厕所的,要跑到西园上厕所。我分到中户,朝南一间、朝北有一小间,朝北那一小间墨赤黑,只有一点点。厨房间也是一点点。四家人家在楼道里合用一个水龙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来到苏州能住上这样的新房子,已经很满足了。那五年日子过得也很开心。
陈:那段时间除了唱戏还做些什么?
林:那时候我结婚了,生了第一个孩子。但我书画这一块一直没丢,还在写写画画,所以接触到几个先生,费新我、吴木、张辛稼是老相识了,从小就认识,回来也经常有来往。我现在收藏了不少,都是这些老先生给我的画。
陈:说到书画,之前我回去细细翻阅了您先前赠我的两本画册,觉得非常不错。
林:你之前看过我的画作吗?
陈:老实说,并没有。
林:你觉得我的画怎么样?
陈:我是一个外行人,家里虽然有收藏一些字画,自己平时也会看看,但我可能自己不会写不会画,所以还是不太懂,只能凭自己感觉,所以我说的可能不对,您多担待。我看您的画作的最大感觉就是画面流畅和布局精巧。有些笔画给我感觉,我会想到戏服的水袖和舞台上的幕布,有些是飘逸婉转,有些是一垂到底。我认为你的书画是和你的舞台艺术相互渗透的。

和周世宗、周传瑛,1979年,于广州珠影
回过来说您在苏州的这五年,您觉得这五年对您、对整个昆曲的继承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林:全国昆剧(团)解散,只有江苏保留,(省团)和苏州团合并,等于就是保留了一个火种。当时虽然创作了许多现代戏,感觉好像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在共同的创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和成就。这个阶段是把现代与传统结合的阶段,虽然昆剧是一个最古老的剧种,但是昆剧是一个很大全的东西,是文学性、艺术性和表演性的综合,用丰富的手段将这个古老的东西改编到现代中用,实际上比京剧还要有看头。我前面也提到了,京剧是比较程式化的东西,在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和程式上远远不及昆剧。
陈:所以我们说昆剧是“百戏之祖”,是包罗万象的艺术。
林:对!后来在昆曲命运存亡关头,“四人帮”倒掉了。其实在“四人帮”倒掉之前,江青已经做出改变了,她也不是一个笨人,在革命样板戏后期,她又开始着重研究传统剧种,而且她开始抓昆曲了。她去参观大寨的时候,带了几个昆剧演员在身边,在去大寨的途中,一路上就让他们唱昆曲给她听。她把所谓的“革命的旗帜”抓到手、走了一个“左”的路线后,就想要稳固政权,于是还是想到了“百花齐放”。包括毛泽东晚年,他爱听传统京剧、湘剧,江青还给他听老的昆剧。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前)其实已经偷偷地拍了许多昆剧传统剧目。
陈:谁去拍的呢?
林:我们那几个老师,王传淞老师也去拍过。都是拍成了电影给毛主席看的。所以1975年夏天,我们偷偷地组成一个小队,去浙江学习《十五贯》了。那时候,浙江比我们这里还要“左”,对《十五贯》封锁得更厉害。我们到了杭州,瞒着所有人,躲在旅馆房间里,把床都拆了,向老师学这出大戏。
陈:这是不是又是您的一个机遇呢?
林:是的。演正面人物况钟,是老生,所以就不跟王传淞老师(学戏)了,开始跟着周传瑛老师学习。王传淞老师气得要命,说:“蛮好的传瑛,怎么跟我抢学生!”周传瑛老师也很无奈,说那也是没办法,他们团里面派过来的,说我自身条件也可以,团里又正好没人,就让我学况钟了。两天,一出大戏全部学会。
陈:只用了两天?
林:对,两天。前几日周传瑛的儿子儿媳和孙女还来这里看我呢。周传瑛作为昆剧老前辈,改编推出《十五贯》全是他做的,政治、艺术都处理得很好。
陈:《十五贯》之前好像是在北京演出过?
林:是的,当时的待遇很高,总理请他们去中南海紫光阁开座谈会,这个是只有昆剧才有的待遇。当然也有一定的政治需要,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说的就是《十五贯》。56年《十五贯》进京,是陆定一在上海的一个破剧场里看到了这个戏,很惊讶,这么好的戏、这么好的剧种、这么好的演员,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演戏),连饭都吃不饱?他看完很感动,回北京后,立马向周总理汇报,讲昆剧《十五贯》。汇报之后,总理立刻指示进京演出。总理看完戏以后,又介绍给毛主席,再把剧组调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毛主席连看两次《十五贯》。说,这个戏太好了,有人民性、思想性、艺术性,三性统一。所以要开座谈会了。《十五贯》进京演出,因此成了全国戏曲改革的一个里程碑。领导当着周传瑛、王传淞两位老师的面就说:昆曲,中国民族的瑰宝,而你们俩是我们艺术界的国宝,回去之后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好好挖掘昆剧。等到老师们回到杭州,一下就将他们的级别提到了三级(正高里的第三级)。至此,昆曲翻身,各大昆剧团和戏校、昆曲班成立。
陈:那我们回过来继续说75年您学戏。
林:75年我从娄阿鼠变成了况钟,大夏天我又睡不着觉了,在西园新村楼外的过道里每天都在复习、背戏。我知道很快这个戏要搬上舞台。过了一年,“四人帮”粉碎,省委决定把原江苏昆剧团所有人马调回南京,成立江苏省昆剧院。回南京后,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下令马上恢复排练演出,等于调回去一个礼拜,就要把戏拿出来,排练的时候,许家屯更是每天亲临排练现场。
陈:可见重视程度。
林:还不单是重视而已,里面还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陈:但他肯定自己也喜欢昆剧,不然他也不会天天来,会坐不住。
林:对。其实当时浙江就觉得昆剧可以不要了,按理说浙江团应该第一个恢复,因为先生王传淞他们是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是他们原唱,结果浙江省委研究后觉得不能恢复,可能当时还在等中央决定。江苏恐怕和他们就不在一条(政治)线上,所以抢在前面第一个恢复昆剧院和古装戏,涉及到版权先后问题,我们省委还和浙江打招呼了。后来新华社和省报上刊登了恢复演出的消息,正版报纸上都是我的照片。可惜那些报道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陈:演出情况如何?
林:白天黑夜连着来。南京演了四十几场不算,许家屯亲自带着我们的队伍往湖北湖南去,都是省委书记亲自接待。我们在湖北演出,陈丕显也热情接待。
陈:这就是命运啊,是昆曲的命运,也是您的命运。
林:其实老生戏我也没好好学,但是耳濡目染的,除了和王传淞老师学戏以外,其他老师也很喜欢我。我经常请老师们到我家里来玩玩,我也经常去他们家里看望他们,来回跑。
陈:同各个行当的老师学戏探讨,丰富自身,也多了行当傍身。但主要还是因为你喜欢表演,愿意去钻研。
林:平时先学着些,然后当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再拼一拼努力一下,就可以登台了。当然,这样拼命学习的后果也是相当伤身体,直到现在,心脏不好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稍一激动、一紧张,心率就乱跳。
陈:当时排练有种紧迫感,是有使命感的,特别您的家庭出身……
林:我还有个故事,这个事情害我差一点送命。文革的时候,我们团里有个编剧,那个编剧年轻有才华,是江苏教育厅副厅长的儿子,他的出身属于革命的一脉,但是属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他后来派到我们这里来,一开始是我们的文化老师,后来做了编剧。年纪也就比我大几岁,对艺术也充满热情,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探讨,我俩的关系既像师徒又是朋友。后来他卷入了政治斗争中,被关入监牢,后来肺病保外就医才得以出来。他在监牢里还坚持写了两个剧本,出来后我去医院看过他,还给他送过粮票。
陈:是因为和他交往密切摊上事情了?
林:是这样的,当时我有个同行,和我同姓,也是学戏的,但是我(事业)一直在他前面。我那位编剧朋友被关进牛棚以后,这个同行就把他拉出来批斗审讯,打得他鼻青脸肿,然后让他交代。我朋友说没什么好交代的。同行就说:“你交代和林继凡的现行反革命事情。你按照我说的写。”我朋友很茫然,他说:“我和林继凡只是讨论了一些艺术上的事情。”同行怒道:“是关于毛泽东的事情!你们两个人对毛泽东怀有恶毒的仇恨。林继凡有很多毛泽东的像章,你们有一天在某地的角落,拿了剪刀,在像章上毛泽东的脸上乱划,放嘴里咬,在脚底踩!你家人被批斗,他家里被抄,你们两个就是反革命!你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
陈:这个同行倒是编得好像亲临现场、亲眼所见一样。他才应该是去写剧本的人。

与王传淞先生的点滴记录
林:后来我那位朋友被打得没有办法,只好写下来。这种事情写下来还了得吗?马上调动人员,把我抓了关起来,开始审问了。那时候严重起来,根本不需要审判、法院,直接就可以拉出去枪毙了。我甚至亲眼看到过歌舞团有人被拉出去枪毙的。我这种事情要是被冤枉了,肯定也是要枪毙的。还好我一口咬定,没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吓得我人都差点瘫掉,吓得魂都没了。
陈:无中生有,可恶至极,这个人是真坏。
林:嗯,是真坏。后来文革结束以后,这个同行回上海了,还来和我讨饶,跪在地上同我道歉。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了。后知道我在昆剧上出名了,他倒还有面子来找我,想办法(要了号码)打了电话给我,我当时正在排练场教学生戏,一听是他的声音,说要来见见我,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找我呢?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也不会见你。”后来就不知道他怎样了,反正也没来见我。
陈:明的争不过你,就在暗地里使坏,不择手段。
林:就算是相互竞争也不能这么做啊。
唉,接着说恢复昆剧后。我们在武汉的时候,我就提出,《十五贯》我要演回娄阿鼠,因为我还是喜欢丑角老本行。我还记得我那天演出,大热天,文联主席还过来看我,说娄阿鼠演得好啊。虽然况钟我也演得好,但是这个戏还是娄阿鼠来得生动,虽然是个反面人物,但是表演艺术上更深入人心。
陈:所以您又重新回到丑角,有没有什么不适应呢?
林:当然还是有些阻力的,同行还有一些比我大的师兄,肯定希望我不要回去唱,因为我唱了会“吃”了他们的“饭”,所以说我现在蛮好的,风头出尽,不要回来。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和王(传淞)老师学戏。有些人马上说:“就他最肯教你,你就是‘拦路虎’,明明我们都学得比你早!”
陈:这没道理啊,技不如人就说别人“拦路虎”,有本事就舞台上比高低嘛。
林:对啊,哈哈哈。
陈:我查阅您的资料,看到您正式拜王传淞老师是王老师76岁的时候,是他唯一入室弟子。
林:是1982年。和王传淞老师学戏是从1962年就开始学了,一直到82年才正式拜师,这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什么呢?62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鬼头,那时候看了我的《僧尼会》给我指点一二,我只是和王老师学了一点点戏,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年的时间。64年就开始“革命”了,全国文艺改革就开始了,已经不能演古装戏了。然后靠着我从小对电影、音乐的喜爱与积累,就开始了(现代戏)的创作。
陈:王传淞老师对你最大的影响或者启发是什么?
林:其实老先生也没什么文化,但是王传淞老师在我的拜师会上说了一句名言:“不要学我王传淞,学我演剧中人。”所以在他教我的所有戏里,他都在说人物的生活。
陈:就是要投入到人物中去,而不是学死板的一招一式。
林:对。拿娄阿鼠举例,娄阿鼠出场前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肚子饿、没有精气神,整个人萎靡不振,从赌场里出来还输了钱,他出场前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突然之间看到亮光,那他首先就先抬头看看是不是月亮光,这就是生活化的东西。一看,不是月亮光,哦,是那扇门缝里射出来的灯光。再看一下这是谁家的门?是尤葫芦家的。尤葫芦是卖猪的,卖猪的一般都是晚上杀猪的,娄阿鼠方才想到可以去他家里偷点东西吃吃,“赊”点儿肉。
陈:这其实应该是剧本的铺排,但是是非常生活化的铺排,能把剧本文字演活了。非常细腻,而且越是细腻,越能表现出故事亮点。
林:对,细腻到可以把特定的环境生动地介绍出来。包括演员的眼神、动作,绝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流露的。王老师说:表演是要有目的性的,目的性不是天上地里生出来的,而是心理活动出来的,是活东西,是真正生活的心理活动。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一定要往左或者往右。这些程式其实都应该化作生活。娄阿鼠为什么叫娄阿鼠,因为他有一个鼠性,老鼠偷东摸西、老鼠生性多疑。除了娄阿鼠这个人该有的生活状态,还有老鼠该有的生活状态,比如活络。但是也是要有美感的,并不是真的表演一只肮脏的、贼头贼脑的老鼠,在形态中还是需要有雕塑感。
陈:就是说任何一个动作的亮相都是美的,像之前说的丑中见美,生活中提炼艺术,艺术中回归生活。
林:对。因为你随便看一个赌场里走出来的酒鬼,肯定不会好看,但是你把程式化的表演给他加上去,那就是一个艺术塑造的形象了。
陈:就是将这个形象放大化艺术化,而所需放大之处,是有的放矢,有目标地艺术化。
林:就是典型化。娄阿鼠这个就典型在鼠性的动态、特征,但又不能真变成老鼠。这就需要演员拿捏得自然。所以王传淞老师教我的一个演戏的经验就是,我去学戏我首先具备一个基础,就像学木工,所有工具我拿在手里都使得称心了,想劈就劈,想砍就砍,这个时候我就是自由的,再去向老师学戏,老师再同我讲道理,我就能把我的动作化进去,就能把我的功夫装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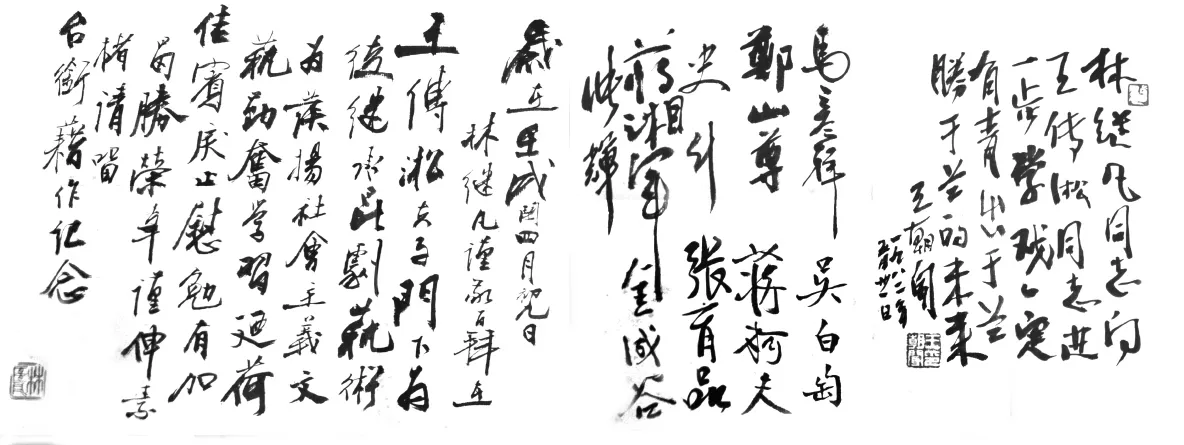
拜师帖内页
陈:除了王传淞老师,我知道您同好几位传字辈老先生都有交往,周传瑛、华传浩、沈传芷、郑传鉴……再和我说说您和其他几个老先生学习交往的事情。
林:那几个老先生都很喜欢我。郑传鉴老师,唱老生的,后来在上海戏曲学校教书了。他喜欢喝酒,扒开眼睛早上就要喝酒,一天要喝三顿酒呢。后来年纪大了,也要两顿酒,总归两到三斤黄酒,喝得多,也慢。就是在他喝酒的时候,你坐下来陪着他,才能听得到东西。他吃得高兴,就会站起来表演给你看。我在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郑老师教我的东西,就是学习传统的东西以后,如何化成自己的、生活的东西。郑老师喉咙其实不好,比较沙,高音又上不去,但是靠动作取胜。他就把这方面的经验教授给我。我经常接他到我家小住,他也喜欢住在我家里,而不住到那些学老生的学生家里。
陈:您很会哄老师开心啊。
林:他不喜欢洗脚,还被王传淞老师等人说过,我就帮他洗,我对他们非常贴近。他从早到晚喝酒,你要陪着他,要有耐心啊,因为他也不是一直在和你说戏,也要讲到点别的。
陈:您孝敬老师的同时,其实也得到了回报。
林:对。郑传鉴是在喝酒的过程中告诉我点点滴滴;沈传芷就是在淴浴(洗澡)的时候,他喜欢淴浴,每天都要洗,午前十点左右或者下午。
陈:你说的淴浴是泡混堂吧?
林:对,泡混堂,那时候南京十点就有的泡了。每天陪他走到混堂也要廿分钟,他的脚那时候已经有些小中风了,要想学本事,就要陪着他。他淴浴的时候,会唱给你听。这个老先生本事可大了,他能在混堂里憋一个半小时,像我是半个小时就要逃出去了。
陈:混堂里头热,又不通风,很闷,是要吃不消的。
林:对,闷得我是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逃出去,过一会儿再进去,他却还在呢。然后你给他说说话擦擦背,他就偶尔给你说说戏。等出了混堂,坐在休息区喝点茶,再和你说说戏。
陈:您就是和这些老先生在生活的相处中学习的。
林:对,不是刻意的,一本正经的。王传淞老师更加了,早上他喜欢喝茶,起床后就泡一壶茶,然后笃悠悠地吃(抽)根香烟,那我也陪他吃,要吃掉十几根香烟呢,连着来的。等喝茶喝饱了,才坐下来给我讲一讲戏。王传淞是跟陆寿卿学戏的,他说自己也不是被手把手带出来的,多数时候是躲在舞台边上看老师演出,偷学几招。陆寿卿吃鸦片,王传淞就每天服侍好他,等陆寿卿开心了,才会念叨几句,基本是不会站起来演示给他看的。
陈:所以你们师徒俩学戏的过程也差不多,都是在和师傅相处的生活中自己有心积累。而且都不是学死板的一招一式,而是稍加点拨,领会精神上的东西。
林:对,都是靠自己去吸收,最好就是看到老师的演出。像王传淞学戏的时候,毕竟昆剧还算是比较高层次的戏剧表演,要看得懂,对观众的鉴赏力和舞台场合都有一定要求。作为那个时代的角儿,陆寿卿偶尔会去露露面,所以王老师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学到点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