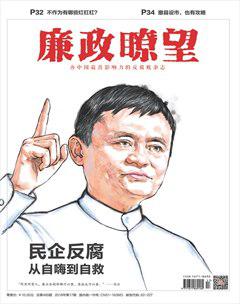支教高原九年纪事
司马迹
又一年开学季,新的学年,老师们往往会问孩子们有什么梦想。对此,藏族姑娘肖芳会告诉你,走出大山,有份稳定的工作;藏族小伙尼玛甲则会说,当兵入伍到军营里锻炼;彝族姑娘马海阿依莫会说,希望将来能考上大学……
被教育改写的命运
对祖祖辈辈放牧种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而言,这些梦想曾经是种奢望,如今都成为能够实现的事情了。而这一切,源于2009年,四川省在藏区探索实施的“9+3”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免费中职教育。这项计划在取得成效后,推广到了四川民族自治地区51个县市。
9年过去了,“9+3”计划改写了不少民族地区孩子、甚至他们背后的家庭的命运。
在成都地铁2号线,地铁女司机肖芳备受关注。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她,是我国首名藏族女性地铁司机,也是四川实施的“9+3”免费教育计划的首批毕业生。
27岁的肖芳出生在甘孜州丹巴县色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在九寨沟风景区一家艺术团跳舞。对未来,她曾充满迷惘:“跳舞吃的是青春饭,或许过几年我会和村里姑娘一样嫁了,一辈子生活在高原,与大山为伴。”令肖芳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在四川藏区实施的“9+3”免费教育计划,改变了包括她在内的一大批藏区青年的命运。
不仅包吃、包住、免费读书,每月还有补助。对家境贫寒的肖芳来说,这一利好政策让她重新走入校园,进入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学习。毕业后,肖芳考入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如今,工作6年的肖芳收获了爱情,并且贷款在成都买了房子,把父母从山里接过来一起住。
这是四川省4万多名“9+3”学生命运转折的一个缩影。而当地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最初群众对这项政策不了解,看到现实版“灰姑娘”们的事例,纷纷主动要求把自家孩子送出大山学习一技之长。
26岁的尼玛德吉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人,他也是“9+3”首届毕业生。尼玛德吉在成都一家汽车4S店做喷漆工,收入从实习期的800元升到了如今的7000多元。
毕业后经学校力荐应聘进入这家企业,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家六口的经济支柱,家里老人看病、哥哥读大学的生活费全靠他。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说,“父母没想到我会这么有出息,一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
如今,已有六届“9+3”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当中,有的进入企业或事业单位;有的参军入伍;有的回乡创业,带动当地乡亲致富。在四川民族地区,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一人成才稳定一个家庭的教育成效正初步显现。
的呷莫是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彝族农村姑娘,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能走出大山。因为州里的“9+3”中职免费教育政策,2014年9月,的呷莫在家人的支持和期盼下来到了成都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就读幼教专业。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费补助,让她没有了后顾之忧。
3年后,的呷莫带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毕业,并在学校组织的用人单位现场招聘会上脱颖而出,被一所学校录用,很快成长为教务主管。
与尼玛德吉一样,的呷莫的故事是凉山“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受惠者的缩影,也是被教育改写命运的孩子的缩影。
壤塘高原上“走不了”的老师们
海拔3200米的壤塘縣城,奔腾的杜柯河穿城而过。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最贫困的县之一,这里曾经的教育问题突出。但是如今,壤塘县的教学质量跃升到全州第三名。而这些,除了政府支持,离不开老师们的付出。
在去年8月建成使用的藏汉双语寄宿制小学壤塘县寄宿小学里,记者遇见了五年级的邓戈老师带着两个班9名没有回家的孩子围在办公室中间的火炉旁复习功课。
邓老师说,“现在的娃娃哦,条件好多了。”以前他上学那会儿学校漏雨漏风,现在新修的学校又漂亮又结实;以前他一学期就只有一套衣服,没有换洗的,现在孩子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以前他中午吃的都是洋芋坨坨,现在食堂里有丰富的饭菜。
邓老师对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如数家珍,德姐和泽真家在中壤塘,离学校40多公里;桑姐家在上壤塘,离学校60多公里;扎木尕家里在牧区,家里三个孩子都在县里上学……邓老师是家里7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一个,也是唯一上了学的一个。在州内念完学,他就留下来成为一名老师,一教就是18年。一年当中除了寒暑假,他的时间几乎都耗在学校。
孩子们手里捧着的教材都是藏语,但是也听得懂汉语,这全靠学校开办的“绵阳班”。
这个班有一名支教老师,叫龚仙彦,被孩子们称为“龚阿爸”。一般州外的老师支教时间都是一两年,但他一待就“走不了”了。
此前,龚仙彦是绵阳游仙区石板镇学校的副校长。5年前,龚老师来到城关小学支教,原本一年后就该返回,但第二年这里设立了一个藏汉语混合教育的“绵阳班”,需要有经验的绵阳籍老师来教学。于是,龚老师自愿留了下来,当了这个“绵阳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
一开始,有二十多年教龄的龚老师面对“绵阳班”有些头疼。因为班里41名学生中40名都是藏族。怎样让他们懂得更多呢?为了让他们听懂汉语,龚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找“翻译”。“找汉语稍好一点的学生,我讲一句,这个娃娃就用藏语翻译给其他学生听。”如今,龚老师执教“绵阳班”已是第五个年头,班里孩子也能渐渐听懂汉语了。
壤塘和绵阳相距600多公里,除寒暑假、“五一”、“十一”假期外,龚老师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藏区。相比绵阳,这里的条件是艰苦的,有不少老师不愿意长待,但他在支教结束后却不回绵阳。问他为什么,他说,2015年底就可以回去了,但看到这些孩子,又舍不得走。因为在这里教书,他自家孩子上高三都没顾上,父亲生病也没顾上。
“那次上课时,家里打电话说我爸爸得了重病,我听到眼泪都出来了。班上娃娃看到我着急,都哭了,我感动得不行!娃娃们都是好娃娃啊!”
2015年,壤塘县藏族考生尕尔王初以高考60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这是该县考出的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
2007年到2017年10年时间,壤塘县考录大中专院校学生628名。
去年,县里出了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
扶贫改变人们的观念
“以前,每到四五月份采挖药草的季节,学校教室、操场都是空荡荡的。县乡干部、村两委成员、学校老师就要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劝学生入校上学,甚至还要赶赴青海去找学生。”
“现在,家长们自觉自愿就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学生数量逐年递增,控辍保学基本达到标准。”壤塘县上杜柯中心校校长王国华称,现在,学校办学理念已从抓学生数量转变为提高教学质量。“现在上学免费、还可以住在学校,只需要周末接送,路也修好了,家长们的观念渐渐变了。孩子上了学有出路,因为有‘9+3政策,还可以去外地上学,学技能,不愁找工作的问题。”
“我们小时候读书,每天要走4个小时的路,翻几座山才能到学校,冬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能到家。现在的孩子上小学就可以住校。变化真的大……”年近60岁的壤塘县双语寄宿制中学教师阿吾感叹壤塘教育发展变迁,以及县域范围内交通的改变,这些都离不开扶贫领域的“给力”支持。
近年来,凉山州深入实施彝区、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每年在彝区10县和木里县招录4800余名初中毕业生到内地优质中职学校就读。对这些中職生,四川省给予免除学费、补助生活费和杂费的资助。
目前,凉山11个深度贫困县共有9444名学生就读于成都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等内地32所省属重点职业学校。为了这近万名学生上好学,凉山还派出了“9+3”驻成都联络组和各校驻校干部84名,帮助学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做好“9+3”毕业生升学和就业工作等。
花大力气狠抓职业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除了异地培养外,凉山还采取自主办学、联合办学等方式发展职业教育。“我们坚持把职业教育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州级财政每年安排职教攻坚经费2000万元,用于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目前,全州中等职业学校达到18所(含两所技工学校),在校学生3.08万人。”凉山州教育局局长游开军说。
技能扶贫,扶助的不仅是代表大凉山未来的孩子们,还有当下的农牧民亟须脱贫的现实。如今,凉山已有越来越多职校、高校参与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来。高山草莓、羊肚菌、西门塔尔牛、农家乐……日子在变好,尝到了知识甜头的农民们,开始自愿自觉地送孩子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