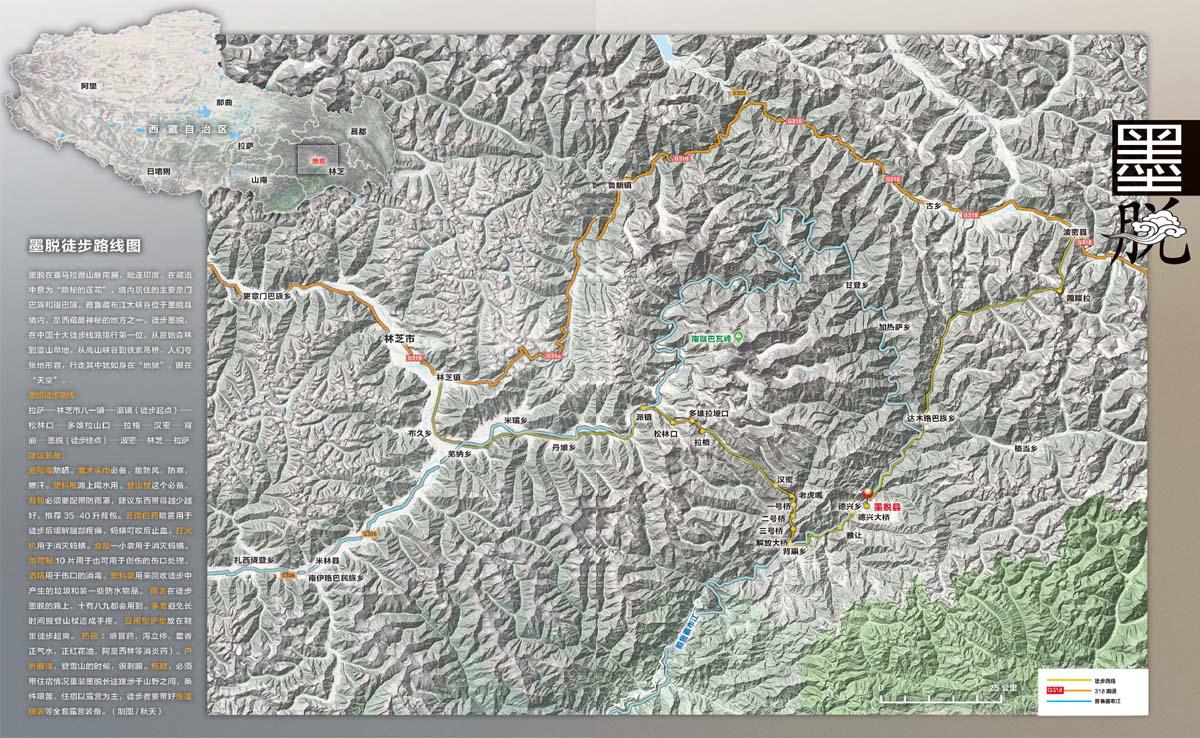门巴人的信仰和世俗生活
罗洪忠
隐居在密林深处
鲁古村地处墨脱县最北端,靠近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深隐在高山密林深处,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就是悬于山腰绝壁之上细如羊肠的小路、数座简易的钢索吊桥以及数十根看上去细如游丝的溜索。这里的门巴、珞巴、藏等民族长期居于深山。
冀文正先生曾是国内首批进入鲁古村的两名汉族同志之一。从他的记述中得知,鲁古村人在高山陡壁上建起一座座凌空悬挂的木屋、木楼,一家一户接连不断,木屋三面悬空,一面对着崖壁,形成一串阶梯式民居组成的村庄,家家户户开门见山,走出门到山泉边接水,就要经过几乎所有人的家门口。从下面往上看,那一座座倾斜的悬空木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城市游乐园里的摩天轮。

村庄附近植被很好,茂密高大的云杉、冷杉、松杉、白桦树自然生长,偶尔还能看到珍贵的红豆杉。村民种地,是在山坡上开垦一片梯田,粗放耕种,冀文正当年在该村看到门巴人新开的刀耕火种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一年收两季,开垦的刀耕火种地多了,粮食就打得多。
过去,因为背出山外成本太高,村民收获的粮食只能自己吃,多余的粮食则用来喂猪。那时候,鲁古人没有禁猎概念,小口径收了,自制火枪还有。冀文正曾在附近的岗玉村见到一把古老的长枪,上面印着“道光二十九年左管造”。据拥有这把长枪的村民介绍说:这把枪来自清军赵尔丰的部队,几经易主,最后落到达瓦喇嘛手中,在波密皮龙贡寺庙底埋藏了3年。有一次,达瓦喇嘛将此枪同人交换,换回50斤食盐和一头牛。几经辗转,这把枪最终落到墨脱岗玉村顿珠父亲手中,他就这样成为了岗玉村最后的“枪手”。
鲁古人打野猪、野牛、野鸡,运气好的话还能打到狗熊什么的。他们把猎物运到山外公路边卖,熊掌、熊皮可值钱了。但这种世外桃源般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我曾到甘登乡做客门巴家,一家除3间吊脚楼房,几乎空无一物。
后来,政府将他们搬迁到米林县西嘎门巴村,这里紧靠林芝机场,公路通到村里,每家4间南向水泥砖房,大门大窗,200多平方米的院落,院墻也全是水泥实心砖砌成,院中栽的苹果树早已吐蕊,几乎每家有小块菜地,绿油油惹人爱。政府还分给每人2亩地和相应的牧场。
我在同次达村长交流时发现,让世居深山的门巴人远离故土、放弃散漫的隐居生活,一下子进入现代化的村镇,这种跨越式生活方式和观念不会在一夜间发生质的变化。有的村民刚过来时,称没有火塘,不习惯住这样的水泥房,甚至偷偷地跑回鲁古村;有的村民称,原来的山地撒上种子不用管,一年收两季,现在在这里担心长不出粮食;以前家里喂10多头牛,10多头猪,可这里海拔高出上千米,担心养不出猪来。如今,鲁古村人已习惯这里的生活。

我来到36岁的尼玛措家,她特地换上门巴族服饰,坐在火塘边,一边烧着水,一边告诉我:“我们那边的海拔要低一些,农作物一年可以种三季,这里只能种一季,我们都担心搬出来后种的粮食不够吃。后来特地跑下来观察。看到政府为我们盖的新房子和分给我们的地,我们放心了。”
57岁的次仁顿珠是第二批从大峡谷搬出来的门巴人。据他介绍,在大峡谷时,村民们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经济来源单一,仅限于狩猎、农业和为探险者当背夫,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只有500元。在深山野林中,他们住的是用树叶遮雨的简易房,吃的是用野菜和鸡爪谷熬煮的稀糊糊。2003年整个村子从大峡谷搬出来以后,村民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他自豪地说:“现在靠跑出租、采药材、打工,我家每年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林芝地区的建设项目很多,下一步我想买建筑机械去搞承包,挣更多的钱!”
狩猎禁忌多达10余种
我来到墨脱县背崩乡阿仓村次达家中时,已看不到弓箭,也见不到猎枪。这让我想起18年前在墨脱县背崩村采风时见到的情景。
有一天,我到村长家做客,他家平时吃饭,要么糌粑酥油茶,要么米饭就辣椒拌蒜。今天照常吃红米饭,可菜肴令人惊异,一竹盘熏羚牛肉,一大碗用石锅炖的熊肉。我没有想到,那些奔驰于深山的羚牛、藏匿于密林的黑熊,此刻竟都成了盘中餐。看到我们惊奇的样子,村长赶紧解释说,这都不是他猎来的,是村中狩猎高手们猎来分给他的,快过望果节了,请我们尝尝野味。
据村长介绍,那时候,门巴族猎手常用自制的箭、弩、套绳及设陷阱狩猎,还有人使用从藏族邻居手中交换来的火药枪打猎。黑熊和羚牛都是大野兽,捕获后需要全村人帮助才能运回。猎人事先与村长约好,打到大猎物后点火为号,村里人见火光就进山。他们当场就把庞大猎物剥皮肢解,分割成条状烧烤烟熏,这样既减轻了重量便于携带,又经过加工易于保存。回到村里后进行分配,每人平均配一份,猎人的特殊待遇就是外加猎物的头、皮和四蹄,基本保持氏族社会分配制度的遗风。

我多次进入门巴族地区采风,想弄清“毒”的配方和制作,可是说法不一。上了年纪的门巴妇女对我讲,放毒有热毒和凉毒两种,中热毒之人,很快就会倒毙;而中凉毒的人,则慢慢黑瘦,最后死去。据传门巴女人使用的凉毒,一般用毒果或毒树根晾干磨成粉末,也有将毒蛇胆汁滴进鸡蛋里,窖入粪堆使之发酵制成毒粉。放毒人将毒粉藏在自己长长的指甲内,当向客人敬酒时,有意把酒灌得很满,让指甲浸入酒内。客人饮用这些有毒的酒后,近则一旬半月,远则一年半载,定会死亡。
我有次去墨脱县背崩村,喝得微醉时,村民特地提醒村里就有一家人,专门在酒中下毒,当地人都不愿去他家喝酒。他还说,背崩村一位健壮的村民,前不久路经东布村时,喝了当地人送的酒,回家6天就患病,13天后死了,死时牙齿发黑,上身浮肿,且有不少鸡蛋大小的水泡,就是被毒死的。这种制毒技术是母传女,母亲临死时,只要接触到女儿的肢体,这毒就传了下去,如此代代相传。这种毒一旦喝下去,便无可救药,连下毒人也解不了。可也有人说,绿松石可解此毒,吞下去后拉出来,再吞进去再拉出来,如此9次方能解毒。但民间认为,放毒乃少数妇女所为,母亲年老了,才把制毒秘方传给她选定的唯一女儿,随后母女相继,代代相传。
我進一步询问,他称这种毒是饲养毒虫,下毒的人会受毒虫控制,毒虫咝咝地叫,这种声音别人听不见,只有下毒的人能听得见,会很难受。他们一边说,还一边做动作:坐立不安,神情恍惚,手脚痉挛,像毒瘾发作的那样,样子相当诡异。我对此半信半疑,他顿时急了,还说家中有的亲人,就是喝门巴人的酒给毒死的。称死的时候全身都是黑的,肚子里全部烂掉,淌黑水。他们清楚谁家有下毒习俗,平时也不来往。可这种毒下的时候,让人不能觉察,是一种慢性毒,有时一个星期发作,有时一年后发作,毒发作后就没的救了。
不少门巴村寨,都视在酒里放毒的家庭为毒玛(放毒之家),将他们当作魔鬼,凡经过他家门口,必加快步伐。我起初走进陌生的门巴族人家,凡看见女主人斟酒时神色有点异样,或指甲过长而且浸泡在酒里,心里就七上八下,硬着头皮将它喝下。

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区墨脱县,气候炎热,食物极易腐烂,突发性的疾病较多,有的人由于食物中毒或急症死去,而他恰恰在某家喝了酒,这家人就被怀疑为“放毒者”,一下子在全村甚至整个地区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去他的木楼喝酒聊天,也没有人再敢与他们家结亲交友,甚至被全村人驱赶、流离失所。听说有的“放毒者”,还被全村人用牛皮包裹扔进江河急流之中,制造了冤假错案。
冀文正曾在墨脱县工作10多年,曾接到不少门巴人“投毒”方面的报案,可他带着医生去解剖尸体后发现,这些所谓喝酒中毒离奇的死亡者,都是因为吃不洁食品,或因为其他疾病而死。据他介绍说:“在门巴人的心目中,我的福气最好,我喝了那么多门巴人家的酒,可没见谁在我的酒里下毒。这些所谓的放毒习俗,实际上是一种莫须有的传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迷信的放毒说法,现在已越来越没人相信了。”

生殖崇拜辟邪镇妖和人丁兴旺
我们通往喇嘛寺门的小径,转过一个弯就是寺门,在一对彩绘的石狮子两边,忽见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个硕大的男性生殖器和一个女性生殖器,木质的雕像原始、粗犷、逼真,男性下半身通体刷成铁锈红,还绑了块黑色的羊皮,我看到喇嘛、尼姑,老人按顺时针沿着寺庙转经,双手合十,那平静的神情似乎告诉我:生命馈赠我们无数,倘若不能正视,又怎堪谈敬畏?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生殖器崇拜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对生殖器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女阴的崇拜。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随之而来的便是男性生殖器崇拜,人类社会便进人了一个性炫耀的时期。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认为,藏传佛教寺院供奉生殖器,与西藏苯教崇拜自然有很大关系,后来兴盛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宗吸收了苯教的部分教义,将铜、木制的男性生殖器供奉在寺院,以辟邪和镇伏妖魔。
我在墨脱县门巴族村寨看到,在巫师请神驱鬼的巫术仪式和藏传佛教的祭奠上,都有生殖崇拜的活动内容。门巴人在每年2月进行刀耕火种前,各村寨要请巫师主持集体祭祀仪式。仪式所需粮、酒、肉等食物由村民平均负担,仪式后由全体村民集体会餐。仪式的内容一是杀牲献祭鬼灵,一是插放木制男性生殖器,请求鬼灵和生殖大神护佑庄稼不受虫灾,风调雨顺,获得好收成。巫师为人治病时,在跳神驱鬼后,要在病人家的门外楼梯旁插一根木质男性生殖器,将灾病和邪祟挡在屋外。
冀文正当年最早到门巴族村寨时,正遇上一家村民房屋竣工仪式,这是他当时目睹的情景:
“第二天上午,太阳刚升上山头,我们有幸参加了门巴村民顿珠家的房屋竣工仪式,一名妇女拿着非常逼真的“卡让欣”(木质男性生殖器)。没过多久,顿珠和帮工们在喇嘛带领下,手持木质男性生殖器,围绕新房从左向右转3圈。我不解其故,陪同的村长次成说,村寨周围遍地皆是鬼神,会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而来。神从东门而入属上等,神从西门进来属最坏。当转完3圈后,喇嘛当即认定,神从南方而来,他带领大家走到新房的南面,深挖一坑,里放9种粮、绸缎布条、金属碎片和一碗牛奶,将木质男性生殖器直插坑底,填土踩实,寺庙喇嘛终于开口:“我看见天神、地神、树神、家神、灶神、粮神、兽神排成很长一行从南门进了新房,它们给主人带来了福气、财气,我们要好好祭祀诸神。”
在门巴人眼里,竣工酒不仅要喝,也最为隆重。大家有秩序地进“三道门”,更显示家人对房屋落成的重视。进第二道门时,一个人手持小木质男性生殖器时说:“我给你送宝子圣女而来,右边是男,左边是女。”家中妇女站成一排,他用木质男性生殖器从妇女背后往裤裆里连戳3次,惹得大家捧腹大笑。进第三道门时,一个持大“卡让欣”的人讲话了:“现在前来谒见喇嘛,我是从天界来的……”寺庙喇嘛将一束白线挂在木质男性生殖器上,双手合十地说:“祈你赐给人间更多的福气。”
每年岁末,墨脱门巴人举行大法会,主要活动有念经、跳神、演出宗教戏剧等,历时10至15天。法会的第一天,第一个活动就是跳生殖舞。跳此舞时需开道僧人5名,鼓钹伴奏僧若干名,舞者仅1人。跳生殖舞的人,必须是寺庙中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一般由领经喇嘛或执事喇嘛担任。跳神舞前,舞者需熏烟沐浴,然后头戴木雕面具,上体赤裸,用木炭在胸部、背部和胳膊上画纹饰。下体穿短裤,阴部拴挂一根小木质男性生殖器,用颜料涂抹成深红色。跳舞者在1名维护僧纪的僧人、2名手举芸香的僧人和2名吹法号的僧人引导下,缓缓登场。在场中,舞者先摸摸木制男性生殖器,又摸摸自己的鼻子,踏着鼓钹的节奏开始起舞。舞者先抬右腳,身体往左侧摆动;放下右脚抬左脚,身体往右侧摆动。接着向左旋转约180度,又向右旋转180度,又由左至右旋转360度转圈,同时做各种象征性的动作,围绕广场跳一周。跳生殖舞时,气氛严肃,观众不得喧哗嬉闹,全场静穆,只听得鼓钹声和舞者的脚步声。跳生殖舞的目的,就是驱赶邪祟,确保祥和安泰和法会的顺利进行。生殖舞跳毕,再晴朗的天也会转阴,若生殖舞跳完后天气没有变化,还得重跳一遍。


门巴族寺庙竣工时,要举行隆重的迎请生殖大神的仪式。仪式由活佛主持。僧人用“波尔巴”树制作形象逼真的男子性器,经念经祈祷后,男子性器分别插放于通往寺庙必经之路的两旁。一般门巴族民居建筑只插挂男性生殖器,很少插挂女性生殖器,而寺庙男女性器均插,有时还放阴阳合体的生殖器偶像。神佛还需生殖大神保驾护佑,这可谓是门巴族地区佛教寺院的一大特色。
墨脱地区还流行跳“中索羌”:当小孩被鸷鸟击昏,父母请来一喇嘛做法事救孩子。可喇嘛以需要取法器为由,支走男人后与孩子母亲调情,两人做出男女交合的象征动作,最后以孩子苏醒结束全剧。这出戏本是一出宗教戏剧,主题是宣传喇嘛的法力无边,但表演时却主要演喇嘛同女子调情做爱,令人难以理解。这出戏的核心内容,是对“性”的模仿与关注:交合——生殖——复苏,这正是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的形象展示。

仁青崩寺门巴族的首座寺庙
在喇嘛岭寺睹寺思物,将我带到18年时前考察仁青崩寺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从墨脱县城出发,站在开满各种鲜花的小道上,俯看巴日村一幢幢吊脚楼,风景如美丽的画卷变得开阔,远处如洁白哈达般的云雾缭绕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上空,近处不知名的小鸟在清脆地鸣啼,眼前不时地有村民牵着牛上下。在巴日村通往寺庙的4公里内,海拔不断地抬升,空气也愈加湿润,闷热的天气也变得凉快起来。当我们从一段清新蜿蜒的水泥路拾级而上,最终到达墨脱县第一座寺庙——仁青崩寺。
这座寺庙座落在墨脱村南侧马拉山上,由村民负责日常经堂打扫和点酥油灯。1780年,八世达赖强白嘉措时期,工布(今林芝)地区的藏族宁玛派喇嘛干布巴来到墨脱村附近修建喇嘛寺,受到门巴人的欢迎和支持,却遇到珞巴人的坚决反对。门巴族多次派代表与珞巴族协商均达不成协议,便又提出在仁青崩建寺,仍然遭到珞巴族的极力反对。后来门巴人只好向珞巴人送了许多财礼,才获得了修建寺庙的土地。干布巴将寺庙建在风景优美的仁青崩,而住持寺庙者既有格鲁派的势力,也有波密土王宁玛派的势力。一向以“受命于天”自居的波密土王抢在前面支持门巴族,让宁玛派吉色任寺庙活佛,将格鲁派挤出墨脱。
据寺庙管理人员介绍,仁青崩寺等墨脱寺庙多为云游僧所建,相互无隶属关系。一年中要举行多次全宗教性活动,大都和农业生产活动相关联,这些宗教活动多集中在春播后、收割后冬季比如开春的2月,夏收的6月和秋收的11月,人们扶老携幼,带上美味佳肴,远行数日踊跃参加这难得的宗教盛典。
1911年6月,贝利从卡布村沿雅鲁藏布江下行3天后,曾在仁青崩寺住了两夜。在贝利眼里,“仁青崩寺适宜地座落在环形山谷中间的草坡上,山谷中心的地上长满了青草和灯芯草,四周环绕着丛林。寺庙顶端有一部分镀了金,我们走出森林时,看到庙宇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每到一定季节,香客们成群结队来转圣山,寺庙周围因此而群集着香客为临时留宿而搭建的棚子”。
据最早到达墨脱县做门巴族群众工作的冀文正老先生介绍,墨脱寺庙中当属仁青崩寺最为宏伟,由三层楼组成,据说有12个屋檐角,该寺喇嘛约有30人,最多时达到40人,大部分喇嘛不住寺,真正住寺喇嘛有4至5人,曾毁于1950年8月15日的墨脱大地震。
在墨脱县寺庙中,还有几座闻名藏区的宁玛派寺庙。罗帮寺由干布巴活佛之子德金林巴所建,他随父亲干布巴和另一名喇嘛,分别创建了仁青崩、罗帮和马日邦三个寺。随着迁徙人口越来越多,门巴人先后又在墨脱县建起了德尔工寺、格林寺、巴日寺等。
我到墨脱调查时,发现在墨脱门巴族的婚丧嫁娶中,喇嘛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大小事务都要请喇嘛,喇嘛在墨脱门巴族心目当中是最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在门巴族的家庭中只要有婚事,就必须请喇嘛算卦看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婚配,而且在哪个日子哪个时辰适合结婚都得听取喇嘛的安排,如果不按照喇嘛的安排去做,结婚的人家就不吉祥。如果喇嘛认为双方结婚不吉利时,就要为男女双方念经化解,这种社会现象在墨脱地区很普遍。在墨脱门巴族家中如有人死亡,首先要请的人也是喇嘛,如果村里没有喇嘛的,就要通过电话或者其它方式联系喇嘛求请指令。在得不到喇嘛的指令之前,是不能随便处理遗体的,如果谁家违反了这种习俗,家里就会有人得重病或者再出现死人。

门巴族喇嘛还充任巫师的驱鬼职能。在墨脱村有一户人家总是有人生病,他们认为有“鬼”有作乱,于是请来喇嘛驱鬼。在做法事的这一天,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能外出,都在家里等待喇嘛的到来,喇嘛来到之后,家里人就要为他敬酒,喇嘛喝完酒之后就安排这一家人做一些祭品和准备好一些作法过程中要用的东西,如大米,酥油灯等。一切准备好之后,喇嘛就开始反复地念经,经文是藏文,念经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声音到最点高时就摇动手中的法器。喇嘛念经反复不少于100遍,念的时间越长越好。在念经过程中,喇嘛认为到了驱鬼的时间,就把这一家叫到他跟前,跪在地上,喇嘛拿起碗里的大米用力的往病人身上摔,摔得越重越好,摔重了鬼就离开病人,边摔边喊叫:“该吃的您吃,该喝的您喝,请不要骚扰病人,请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法事活动完了之后,病人的家里就要点上一盏酥油灯,至少3天,这3天不灭就会显灵。
在墨脱,每一个门巴族人对喇嘛都十分敬重。我在墨脱德兴村调查时,就遇见这样一种情况:在德兴村有一户人家为死者作49天的法事活动请来了喇嘛,喇嘛作完法事活动之后在德兴村暂住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德兴村的其他村民就到喇嘛暂住的地方排队宴请喇嘛去家里做客。究其原因,他们告诉我:喇嘛去谁家做客,谁的家里就会平安吉祥。他们认为喇嘛就是吉祥和幸福的神,能把喇嘛请到家里,就是等于请来了保护神,可见喇嘛在门巴族人心中的地位。

“鬼人”之家消失的陋习
记得4年前,我到西嘎门巴村考察“鬼人”习俗是否从村里消失,可当地人却对我说:“江边就有一家,大家都不愿去他家。他在墨脱县甘登乡鲁古村时,就是村里有名的‘鬼人,喜欢在酒里下毒。”
“鬼人”习俗影响之深,这让我想起18年前的一次墨脱行。我们沿着某条沟谷往下走,在芭蕉叶包围中,隐约可见一栋吊脚竹楼,向导指着这栋竹楼说:“这就是村里鬼人次仁的家。”我们刚走到家门口时,向导却停下了脚步。
这家木屋非常破旧,也显得很窄小,门前树桩上挂着一串鸡蛋壳。我不解其意,门巴族向导说:“这家男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经常做‘射穿闲话的仪式,并将那些用过的鸡蛋壳串起来挂在门口,以示流言早已过去。尽管他每年都要做多次,但还是没有人相信他家。”
这家男主人次仁得知来了个汉族人,从农活地里跑回来。他听说汉族人不嫌弃自己,给我们敬献黄酒,我们都爽快地接受了。我用门巴话跟他说:“我今天喝你家的酒,若没有中毒,称你家是‘鬼人和放毒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我刚说完,这位40多岁的门巴族汉子,委屈地流泪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激动地说:“你们这次来到我家,说明那些谎话闲言不存在,我家不再是人们说的‘鬼人了。”
据最早到墨脱做门巴族工作的冀文正介绍,他们到地东村后,竟发现有4户“鬼人”家庭,村民们处处歧视“鬼人”家庭,不同“鬼人”家往来,连他们的儿女成婚也是个大问题。
在门巴人的心目中,“鬼人”是鬼附在人的身上变成的。一旦成为“鬼人”,就会世代相传,受到无端的歧视。有人肚子痛了,他并不认为自己吃了不洁的食物或受了風寒,而是认为是“鬼人”使他患病;有的人酿酒发酸了,他并不觉得是自己的技术不精或酿具不洁,而是责备某日造酒时被“鬼人”看见;某家的牛病了,习惯是放血治疗,若刀口溃烂不愈,他并不认为是细菌侵入而是责备“鬼人”加害。凡此种种,他们都认为是“鬼人”所害,致使被认定为鬼人的家庭,蒙受诸多不白之冤。
那些自认为被“鬼人”残害的家庭,通常也有一套自认为有效的应对仪式,祈请“鬼人”的灵魂不再害他们:即到了晚上,待“鬼人”全家熟睡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米饭、鸡蛋和酒肉,来到鬼人家门前,默默祈祷说:“××××,请你吃吧,我给你送米饭、鸡蛋和酒肉来了,不要再让我家里的人肚子痛吧!”说完,就往地上撒带来的食物,随后悄悄离去。若第二天,病人有所好转,自认为昨晚的祈请有效。若不见效,再进行第二次祈请,并在散发食物后,一位事先有意藏匿的人突然冲出来,朝散出的食物上乱打,意思是惩治那些领了食物,仍在继续害人的“鬼人”灵魂。
門巴族习俗里,为什么会有“鬼人”?我拜访地东村喇嘛次仁降珠老人。据他讲,早在门巴人迁入墨脱前,在朱隅(不丹)就存在一种称为“康日(骨头)”的制度。“康日”将人分为3等,一等为“康日宁布(第一)”,即“好的骨头”;二等为“康日巴策”,意为“中等的骨头”;三等为“康日独宾”,意为“坏骨头”。最受歧视的“骨头”,自然是“康日独宾”,即“坏骨头”的等级。在朱巴人眼里,“坏骨头”等级又被称为“顿”。有关“顿”的来源,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在主隅地方有间房子长期空着,无人敢进去居住,说里边有鬼。有一天,有个人大着胆子进入了这间房子,但很快就被女鬼迷住了。他同女鬼结了婚,生下的子孙就是那些被称为“顿”的人。因而,“顿”又被称为“鬼人”。
有关好坏骨头的来源,说法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古时候,地上没有人,当上天把人送到地上时,用了3根不同的绳子,一条是金绳,一条是银绳,第三条是棕绳。从金绳下来的人是好骨头,从银绳下来的人为中等骨头,从棕绳下来的入成为坏骨头。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宗教徒的牵强附会,却也说明一个道理,即等级制度的产生,与财产的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财产决定了人们的地位。
门巴族“鬼人”本身,同其他门巴人没什么两样,所谓的鬼人一说,来自于宗教的荒诞解释,说他(她)们是某种动物鬼或植物鬼变的。这本是愚昧落后的旧社会强加在人身上的锁链,然而一旦带上这精神枷锁,就自然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从此和邪恶、黑暗为伴,终生不得解脱。好骨头的人是高贵的,他们可以当活佛、喇嘛;中等骨头的人,可以当低级的僧人;坏骨头的人,不仅不能当僧人,而且在社会上备受歧视,“鬼人”就属这一类。
门巴族骨头的好坏,依据血统而定,世代相传。同属一个骨头等级的人,可以通婚,若骨头等级不同即严禁结婚。在门巴族的历史上,他们严禁与坏骨头的人通婚,如若通婚,他们所生的子女,全为坏骨头。
尽管“鬼人”习俗曾经根深蒂固,可也有改变的时候。但地东村曾被称为“鬼人”的江措,他的长子西绕成了墨脱县的干部,长媳央宗是藏族,亦在县里工作。次子晋美旺杰是边防部队的副连长,次媳布次是背崩区卫生员。女儿泽仁措姆是地东村的卫生员。现在地东村的村民,再也不把他们视作是害人的“鬼人”了,这无疑是门巴人观念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