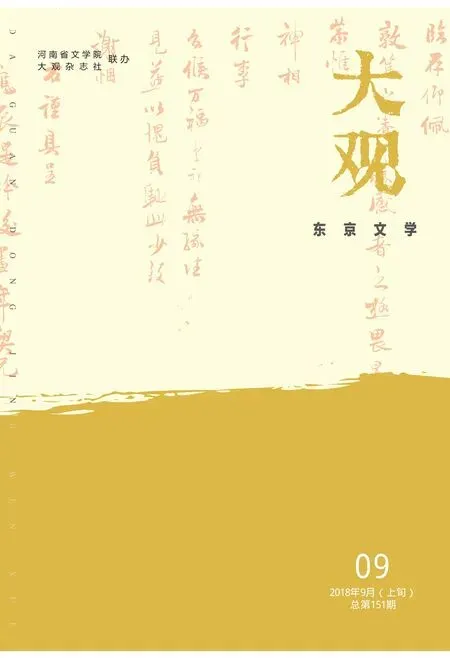滴水观音
一
我和先生是中学同学,又先后回到同一个小镇参加工作,再加上双方父母多年故知,经老师牵线自然走到了一起,并很快怀上了妞妞。就业,恋爱,结婚,生子。别人眼里的马拉松对于我们就是百米赛,不到两年匆匆搞定。速度太快了,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拉着向前奔跑,一下子就到了终点。
我们还没享受二人世界,就毫无防备地挤进来一个“第三者”,就像两个正在偷食蜜糖的孩子突然间被抓了个正着,茫然而不知所措。
我的朋友们还一个个蝴蝶一样轻盈自由,我却要一天比一天笨拙丑陋。更可恼的是,我进修的美术课程还没到一半,假期还要去河南大学参加学习考试。腆着个大肚子,在那么多熟人面前晃来转去?我根本就没法儿出门。羞恼!生气!却又不知该向谁发火。怎么办?先生说听我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找妈妈哭闹。她一流泪,我心软了。反正早晚都是要有孩子的,那就要吧。
摸着自己的小腹一点点鼓起来,并慢慢感觉到她的蠕动。做B超的医生指着电脑的屏幕,说着“小手儿”“小脚儿”“小屁股”“小脑袋”……一样样指给先生看。我躺在那里,看见先生的眼眸比任何时候都亮,眼神比任何时候都温柔。他微笑着,我却有种想哭的冲动。
那一天,我们知道了她是个女孩儿。我又开始期待。开始叫她妞妞。开始主动喝“保灵孕宝”,努力克服妊娠反应,即使吐出来也得硬着头皮吃下去。
到了后期,身子格外“笨”,人没到肚子就先到了。如果偶尔不注意使外物触碰到她,她便来回翻腾几下以示不满,很好玩儿。我抚摸着她,甚至在她安睡的时候故意加大力度逗她,她便会用力踢我两下,或者不耐烦地来回拧身。
小时候,爷爷在瓜棚下睡觉,我偷偷拔一根茅草,轻手轻脚地来到他的身边,似碰非碰地触他的鼻子或脸。他在朦胧中以为是苍蝇或别的什么,晃两下脑袋或干脆用手去打,我便嬉笑着跑开了。想不到,很多年之后,我还会用这样顽劣的方式和自己的孩子相处。
四周静极了,我常听见自己的心跳,“腾——腾——腾——”,比钟表上秒针的步伐要快一些。我数着时间,感觉到她蜷在我的身体里,贴紧我的五脏六腑,在我的体内听见各种隆隆的声响。她的到来,就像上帝事先给我包好了礼物,到跟前一股脑塞进我的怀里。短暂的惊慌之后,忐忑着慢慢打开,发现她是最珍贵的。
因为身体状况不太好,我一早就请了假。先生上班早出晚归,我便有大把的时间和妞妞独处。先学着给她做了几个小褥子,又偷偷买来纯棉的花布给她缝制小衣服。朋友过来看我们,为她织了带着小尾巴的连体毛衣。摊开放在床上,像一张完整的小老虎皮。帽子上有鼻子有眼儿,有嘴巴有耳朵,可爱极了。我能想象出来,她穿上这些衣服是什么样子。
院子长满了花草,是已故的夫家爷爷种下的。他是一位离休的老教师,生前一直住在这里,虽然在我们结婚时做了修整,还是有很多地方保留他的痕迹。月季已高过了窗棂,铺散开茁壮的枝叶,碗口大的花朵泛着深红丝绒的质感。墙角的竹子长得很快,就连院子的中央也会时不时拱出三两个竹笋来。后来,妞妞在这丛竹竿里攀扶着学会了走路,还拍了打着红灯笼的相片。这个爱花爱画的孩子,没有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老人对生活的爱和情趣祥云一样笼罩着。
门口,搭了一个很大的葡萄架。我关上院门,坐在下面听各种儿歌,偶尔写几句诗,看着一串串小米粒儿大的葡萄一天天膨大起来。先是青涩,明明猜得到它们的味道,却忍不住想尝,酸得龇牙咧嘴口水直流。下一次,还是忍不住。每天晚上,我以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她给我带来的欣喜和变化。到了葡萄发紫成熟的时候,那种甜蜜黏稠的汁液能把我的手指粘在一起。经过一天两夜死去活来的折腾,她真真切切地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做梦一样。
二
第一眼看见她时,她正在努力睁开眼睛。大概过了三两分钟,左眼已经自如。右眼可能受到了挤压,大半晌才慢慢露出乌溜溜的眼珠来。不知道,她是否看清了我的模样。
已近深秋,连绵的细雨下了好几天。这个安静的孩子不哭也不闹。我躺在床上,看着院子的人来往穿梭。——他们都在庆祝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我的内心却莫名其妙地长满了荒草。
满屋熥窝儿的尿骚味儿(那时农村没有“尿不湿”,用一二十个小棉垫儿替换着),和我买来不满一年的组合音响很不相称。婆婆的话是圣旨(妈妈也这样交代过)。她不让我在晚上睡觉前洗脸,也不让早起刷牙,还得喝只加了点儿盐的鱼汤鸡汤。在她的面前,我没有自由,也没有身体的隐私。又因为右边乳头有点塌陷,里外不通透,婆婆说一定要多吃这个,否则便会“回奶”,将来双乳还会大小悬殊。妞妞饿了,我在婆婆的指导下让她先吃右乳。孩子很费力,也很辛苦。实在着急的时候,就干脆放声大哭。而我,每一次把乳头塞进她的嘴里,都需要咬紧牙关,直到被吮吸得血肉模糊。
吃吃停停,停停再吃。她哭,我也哭。十来天后,我们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就像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打了第一场胜仗。
天越来越冷,这个原本安静的孩子越来越“精”。她知道躺那儿晃着和抱着坐起来不一样,坐起来抱着和站在地上也不一样。因为天冷,先生夜里需随时待命而不敢脱衣服,等她哭时就直接抱着站在床上转几圈儿,省了穿鞋。这小东西竟知道了站在床上和站在地上也不一样,还得不停地晃着唱歌。他白天还要上班,实在熬不上了就放下一会儿。没多久,她又学会了看着我的脸儿哭,叫人不忍。
很快,我就该上班了。我们带着孩子自立门户,住进了单位的一间小破屋儿。屋顶长着榆树苗儿,两面墙上各有一个不足一平方的小窗户,室内地面新墁了红砖,墙上刚刷了涂料。搬去的第三天夜里下雨,雨水和着涂料顺着墙角往床上流,加上换了新环境孩子哭闹,折腾了大半夜。五点半,又起床去上早自习。
记不清那时是不是有暑假,反正小屋里很热,只有一个台扇放在带屉桌上。不知是电扇质量太差还是桌子中空的缘故,一打开就嗡嗡哄哄地响。在静寂的夜里,像劣质的抽油烟机无所顾忌地轰鸣……
学校里年轻人多,正值一个生育高峰,和女儿上下不差半岁的孩子就有十几个。工资都低,都不找保姆,也确实没条件找。要么夫妻二人轮换着上课,要么请家里的老人出来帮忙。我们属于特殊情况:先生不在教育上工作,自然无法轮流照管孩子,他又是长子,婆婆还要忙于其他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出不来。先是妈妈来了几天,姑姑知道了心疼她,就主动提出来可以在我们两个人错不开的时候来带孩子(姑姑家住在学校附近)。
就这样,我早上到教室看学生,先生一边做饭一边照管孩子,还要急赶着时间上班。我呢?下了早自习就着急忙慌地吃饭、喂饭,等姑姑来带妞妞,再准备上课。白天要上课、洗涮、照顾孩子,根本就没时间备课改作业,都得放到晚上来做。晚饭后,收拾好七零八碎,等孩子睡着再爬起来干活儿。夜里十二点之前很少睡觉,一天到晚都像打仗。
妈妈说分开家会穷三年。结婚时爸爸给我“拜礼”钱,说明其中有一千八是用来买电子琴的,我早已没了要弹琴的心。那时候,每月工资还不足三百元,发放又不及时,我盘算着用这笔钱买孩子需要的东西。
妞妞小时候挑食,体质差爱生病,常手头紧张工作紧迫。“穷急”“忙急”,两样都占。我们也会抱怨,不满,甚至争吵。但住在门挨门的大杂院里,哪家改善了生活、孩子买了什么样的玩具,甚至夫妻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邻居的耳目。想要发作,又碍于面子。
有时候,整个人就像一直充气的气球,憋着憋着就忍不住了……先生生气时偶尔会大吼,但过一会儿就没事儿了。而我,只是一个看起来脾性比较好的人,会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故意装作不屑,或者用若无其事的冷淡触他之怒。他有时会转身离去,但不忘记抱着女儿。这两三岁的小人儿,能感觉到空气的凝重。她一声不吭地睁大了眼睛,趴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着我,渐渐走远……
有一回,在我抬头的一瞬正好和她那双眼睛相对,那种无奈惊恐又满带惶惑的眼神,一下子击中了我。我转过身来,泪流面满。在众人的眼睛里,我的运气不错,一切平顺。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脆弱狼狈琐碎不幸福,也不能让自己放下姿态主动与先生和解,更不懂得怎样与生活握手言和。关键是,我那颗虚荣的心,不能不光鲜。
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她的手里拿着新买的玩具或零食。无论经济多么紧张,妞妞的玩具和服饰都在孩子群中领先。我们暗自默认了用这样的方法来补偿她的惊恐,并试图以此获得更多的自我安慰。
妞妞好像很快就忘记了我们给她带来的伤害,跳在地上,像个男孩一样奔跑,不甘人后。
三
那时候,我喜欢刀郎的歌。“就算生活,给了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也依然感觉幸福更多……”常常不自觉地唱出这声嘶力竭的一句。
没有幼儿园,妞妞经常和一群孩子在校园里疯跑。我在楼上上课,她在操场游戏玩耍。在众多的孩子之中,我能准确地辨别出的她的笑声,像露珠一样在荷叶上滚动着,透亮圆润。整个校园的空气,也因她如雨后的清晨一样,更加清新。
妞妞爱美。每天早起主动要求洗脸,再抹香香。若有人在她跟前吸着鼻子说,真香啊!她便觉得自己的香气少了几分,不高兴地嘟着嘴不理人家。只允许我一个人在她脸上猛吸两口,然后咯咯地笑。不到两岁时,给她穿上婆婆做的小布鞋,不一会儿就蹬搓着掉下来了。再后来,只要看见我拿小布鞋她就踢腾着双腿不让穿,嘴里嘟囔着:“呃——呃——不,奶奶做——”我们知道她是说不穿奶奶做的鞋,连同事在逗她玩儿的时候,也故意说:“走——给妞妞去穿‘奶奶做’……”她就笑着跑开了。
那时候,夫家的弟妹都没有成家,一家八口只有这一个孩子。放假回家,像个小宠物一样被逗着玩。她很活泼,从这个怀里跳到那个怀里,或者被一个人抱着好几人在后面追着跑,要么围成一个圈儿看着她在中间做各种“表演”,快活极了。我给她穿上小裙子,她扭捏着咿咿呀呀地唱,学着电视上天线宝宝稚憨的样子,跳着数:“一——二——三——”
她像一个天使,舞动着翅膀来到我的面前。买了吃物儿先举到我的嘴边,买了玩具先拉起我的手……于是,我不再惦念那些花蝴蝶一样自由美丽的朋友。
妞妞四岁半的时候,上了学前班。从偏远的校园跑到镇中的小学,大概有二里半的路程。我当了班主任,每天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室看学生,妞妞上学送了几次,就让她自己跑了。当时十几个一般大的孩子,只有她和一个同事家的男孩儿不接送,作着伴儿早去晚回。
有一次,上课半晌了俩人竟没有到校。老师先是觉得小孩子磨蹭,没在意,第二节下课就着急了!都没有电话,因为姑姑家学校近,就先通知了她。她一听更是着急,一面喊着“妞妞”,一面一溜小跑儿通知我。我心里一惊!赶紧找!心急火燎!找了好几个常玩儿的地方都没有。吓得腿软,脑子一片空白。最后,姑姑在村外的大沙坑里找到了他俩,满身满脸沙土正玩得起劲,滑滑梯一样地从上面滑下来再爬上去,再滑下来……
我们的学校在慈周寨(《滑县志》载:隋大业七年春,翟让起兵于东郡瓦岗寨时,曾在瓦岗寨东北四公里的地方设济贫处,赈济饥民,后发展为村镇,名“慈周寨”。取慈善苍生,周济天下之意)的东寨外,四周都是荒沙地,这两个孩子玩耍的沙坑在学校的东北,附近村民长期取土所致。此处少有人来,又临一条僻远小路,如果真遇见坏人……心有余悸!
回到家,躲在没人处抱紧了她,流出泪来。不仅是因为这次有惊无险的“失而复得”,大概还有些别的。我二十岁还是个学生,二十二岁就结了婚,二十三岁又生了她。在此之前,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需要钱时只需要叫一声“妈”,不高兴时还可以耍个小脾气儿。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所有人眼里的“大人”:像模像样儿的“老师”、有模有样儿的“家长”,回到婆家还得是个装模作样儿的“好媳妇儿”。——这些都不是我,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孤独骄傲的小女孩。妈妈非要给我钱的时候,我也必定会推辞半天,直到她有些生气地说出一句:“这是给妞妞的!”
有时候,和妞妞在一起特别容易露出自己的脆弱,就像一个大孩子抱着一个小孩子,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之后相依为命的感觉。
这个在大杂院里成长的孩子,上三岁下两岁都能玩在一起。一边耍刀弄枪,又一边给芭比娃娃缝衣服,玩奥特曼也抱毛绒玩具。像男孩子一样淘气机灵,又像女孩子那样敏感细腻。有一回,我一边扫地一边叹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唉——”了一声,她竟马上接过来:“妈妈,人生如梦吧?”——“人生如梦”,这大概是我平时感叹之余常常随口说的四个字,让一个三五岁的孩子熟记在心。
我需要调整自己。在生活面前,摆出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姿态,无所畏惧。
四
妞妞五岁半时准备上一年级,和家里人商量让她在县城有名的向阳小学借读。除了那里的条件和教学质量更好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我又怀孕了。
那天,我和先生把她送到学校,还要急着赶回六七十里外的老家。到了门口,她主动要我们回去,还认真交代不要回头看她。我同意了。却没忍住。她挥着手,一边转身一边往前走。我发现,她的“丸子头”上有两个小卡子歪到了一边儿。——她平时紧张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摸自己的头发。——她在陌生的环境里害怕了,但没有说。
我心里一酸,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淹没在人群中,就像一条细流汇入了大海,不见了。
她穿着白色连衣裙。上身罩了一件黄色的半截袖外搭儿,两襟上绣着淡蓝浅白的花朵,和浅蓝色的小皮鞋上下呼应。我着力把她打扮成“城里的孩子”,希望她在陌生的环境里不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然而,她那十几个一起玩大的伙伴儿,忽然间就从生活中消失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放学后回到叔叔婶婶的家里,会不会想念爸爸妈妈和她的大杂院?这些,我都想过。
最终,还是把她交给了婆婆、小姑、弟媳妇儿,由她们帮忙照管。
当时计划生育很紧。即使是农民多生孩子也必须东躲西藏,作为公职人员更是小心。我请过假,换了手机号码,从此失踪。打游击一样住在道口弟弟家里、老家妈妈家里,轮换着潜伏。有时候实在闷得很了,先生就在冬夜九点之后陪着我去田野里转一圈。
夜很静,月光格外明亮,天地间一片茫茫。有时候,我们走出好远,拉着手,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
每个周末,先生都会搭车把妞妞接到我的身边,周一早起再送过去。有一回,他下班后没赶上进城的公共汽车,想到妞妞漫漫一周急切的盼望,我坐卧不安——似乎为着这一个孩子却舍下了另一个孩子。后来,干脆趴在床上大哭。先生找来他的朋友,开了一辆大巴,空着车专门为此跑了一趟,直到深夜才回来。
妞妞来到我怀里时,已经睡着了。
后来提起这段经历。妞妞说,刚入班时,暂时没有课桌,就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挤在一起。就像蹭了别人的宴席,坐在那儿尽量缩小自己,怎么做都觉得不合适。拘谨着,像端了一碗热汤,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下的地方。圣诞节到了,老师说偷偷在枕头底下放一只袜子,圣诞老人就会给每个孩子送来喜爱的礼物。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照着做了。第二天起床,袜子里空空如也。她不死心,在床上来回翻了几遍都一无所获。沮丧极了!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孩子,连最公平的圣诞老人都不喜欢她。到了学校,她的同桌——那个白天鹅一样高傲的女孩儿,不光收到了礼物,还收到了圣诞老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老师让大家说说收到礼物的感受,她低着头,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活泼开朗的大女孩依然泛出了泪光。为什么不说呢?每个周末见到我,她总是很高兴,趴在床上给肚子里的弟弟讲故事、唱歌,给他取“亮亮”“光光”一类的名字,幻想着他像只小老鼠一样在被窝里钻来钻去,给他编各种各样的笑话逗得自己哈哈大笑,没讲完就笑完了……
因为工作调动,妞妞跟着我们来回辗转搬家,小学六年换了四所学校,并且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上大学后,是一个学期。
我一直都认为,她是个令人放心的孩子。
五
妞妞住校后,七八年的时光就像一列疾驰的火车,一晃就过去了。
我忙着工作,忙着虚荣,忙着浪费,忙着照顾那个比她更小的孩子。试图搜索记忆中那些柔软的区域,然而往事就像一张张受潮的底片,所能想到的都是大片大片模糊的轮廓。我和她相处的琐事或细节,不再像她小时候那样清晰而具体。
初中阶段,她由入校时的中等生成为班内的前两名(很少得第二)。记得每次出席家长会,她的名字就像我头顶的花冠,就算我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别人也能透过花朵的芬芳与鲜艳发现我的存在。老师微笑着同我打招呼,家长们向我投来羡艳的目光。
到了高中,成绩不再那么突出,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之后日趋平稳。除了每次放假的接送和基本的衣食供给之外,我不曾特意为她做过什么。看到别的家长额外给孩子补课,隔三差五前去探望,甚至租了房子陪读,偶尔我也会心血来潮。她只是说没事儿,看好弟弟就行了。这个让人放心的孩子,从没让我失望过。
转眼就是高考,她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本来已经不错了,但是看到一起长大的两个伙伴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更好的学校,她犹豫了。这些年,老师所给她的一贯评价是“活泼聪明”,我却认为潜台词是“不够努力”,所以更倾向于复读。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是怎么说的,反正最后总不忘再加上一句“你自己看着吧”。
她选择了复读。我也对她报了更高的期望。
这一年,她在高手如林的“尖刀班”里艰难跋涉,翻山越岭,确实付出了很多。出分前,她反复盘算着分数,想着想着就怕了。拉着我,手心湿漉漉的,跟在我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我说没关系,考多少都行。“多少”是多“少”呢?结果超出了我们设想的“少”的范围。之前所做的最坏的打算,也成了飘在空中遥不可及的神话。
考前一个月,她告诉我“紧张”。我为了减轻她的压力,只是故作轻松地说“正常”,并没有和她深入交流。我在高考前的第三个星期天,还凑着热闹去了苏州。——我对这个孩子太放心了。我像一个昏庸的君主,只看到了四海升平的表象,没有用心来体察她的内心变化。平时模拟,她也有考得不好的时候,但是没有和我说,我也没有问;生活中,她或许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伤感,只是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发现孩子身上暗藏的危机。
一夜无眠,我躺在她的身边无法安慰,不敢动也睡不着。作为妈妈,我不能说失职,但还是做得不够。我很惭愧,更多的还是心疼。经过一年鏖战,这个本来瘦弱的孩子体重减了近十斤。抱在怀里,她那突兀冷硬的肩膀硌痛了我的心……
晨起,一拉窗帘,阳光灿烂。平静得和以往的每个日出没什么两样。先生说,又来过一遍,不管结果是啥都不后悔了,好好挑个学校吧。之前所有的准备都没用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们按自己的分数及位次,查看了往年的录取情况,经过多方面斟酌权衡,选择了河南工业大学并被顺利录取。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更好。但我不能否认,在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仍然包含了自己虚荣的成分。包括妞妞复读。
六
妞妞要上大学,我和先生去送她。
初秋的阳光还没挥洒尽夏日的热情,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花生油一样金黄透亮。我们并排走在她即将生活四年的工大校园里,踩着青石板上斑驳的树影,我有一种时光逆转的感受。
真快啊!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孩,已经长成了亭亭如荷的大学生。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花儿来看我们,和她谈起这些年育儿的感受。她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实那个看起来懂事让人放心的孩子,才更需要关怀。妞妞说,小时候最喜欢输液,因为那样我就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一心一意地陪着她了。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时需要抱着我的一件衣服,闻着洗衣液里薰衣草的清香。太孤单的时候,甚至盼望着生病。——这些,我都不知道。
曾经自以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就连我的青春也因此潦草狼狈地画上了句号,事实上还是她给我的更多。
记得1999年春天,妞妞还没有断奶。我在先生的陪同下,带着她参加普通话测试,测试点刚好在我的母校。离开四年,再回来,一个变仨,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我老远看见一个同学,前后座儿,一直保持着比较亲密的来往。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就像有人猛然擦亮了火柴,一闪眼,熄灭了。拖家带口的我,有一种羞于见人的感觉。赶紧钻进一家小卖部里,从后门逃掉了。怕什么呢?现在想来,年少如飞蓬飘在空中,一旦落地便觉得世俗而不光彩。还有,我生育后发胖走形的身材,恐怕也是不愿再见故人的原因吧?
有三五年的时间,我除了工作就是她,几乎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妞妞长大之后,我渐渐喜欢上侍弄花草。即使是发芽的土豆、长出几片细叶的红萝卜头儿,或者是带着一两个嫩芽的白菜根儿,也会随手埋在花盆碗钵里舍不得丢弃。我喜欢这些细碎而柔软的生命,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安静生长。
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坐在宽大的沙发里,看见朋友送我的滴水观音,在向阳的窗下招展着叶片,像杂技演员手中高高擎起的托盘,扎根泥土的生活恬淡而从容。有时,也和妞妞说起她的童年,内心有些亏欠。妞妞就笑了。这有啥呀?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有爸爸妈妈又有弟弟,咱自力更生成绩还不错。关键是妈妈还那么漂亮!哈哈!
这个懂事的孩子,你让我怎么说呢?
毕业十五年,我和当年的室友相聚。席间,玲还记得我当年的口味,像照顾小孩子一样不断给我夹菜,利隔着两个人先把一杯饮料递到我的手里。离座时,梅帮我收起来搭在椅子上的围巾,娇里替我拿起放在餐桌边儿上的水杯……一个人在付出之后,才更懂得惜福。她们依然以当年的眼光待我,我却不能再如当年一样安享她们的“好”。羞愧与感激交织着,无法平静。
校园里的花架上爬满了紫藤,自上而下倒垂着,如帘,如瀑。我们坐下来,拉起手,细说各自的生活。我翻出手机里妞妞的照片。她们说,笑起来的样子和你真像啊。又提到这些年的变化,丽满是感慨: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说话的语调却变了,想不到我们的“小顽皮”也能长大。
是啊,她们的“好”就像田地里长出的庄稼,粒粒皆是“苦心”。过去,哪里懂得?
一天清晨,我蹲在花盆边刷牙。看见滴水观音的叶边渗出了水珠,眼泪一样滴落在一卷娇嫩的叶芽里。走近看时,却发现这卷新叶正从生长的叶柄肋下破腹而出(我一直以为,滴水观音的新芽和大多数植物一样,是从根、茎中间直接生发出来的)。心里一惊!就像看见一个孩子刚从母腹中抱出来。
第一眼见到妞妞的情形,犹在眼前。那些曾经流过的眼泪,化作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在心中荡漾着。原来,是她的陪伴成就了我,以往那些令人落泪的疼痛,不过是生活的庸常。说到底,还是她给我的更多!
“夷门书法人物志”系列漫画连载之六
4
邵瑞彭(1887—1937),字次公,书法得褚遂良三昧。
早些年,次公是个闻名天下的斗士。那时候,他还在京城,头上顶着一顶众议院参议员的桂冠,1923年深秋,曹锟贿选总统,他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了这场丑闻。曹锟的部下威胁他说:“花钱买选票,总比拿枪顶着你的脑袋让你投票强吧!”次公愤怒了,把曹锟贿选给他的五千银元支票拍照后寄给京沪各大报纸,把贿选事件搅了个满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