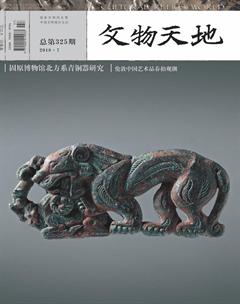记“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大展
周至伟



“在昔有殷秉金气,吉金创制尊彝良。”作为中国早期艺术的灵魂所在,青铜器上承自新石器时代的日用陶器,却不仅仅止于简单的烹炊食饮。对先民们来说,青铜器是与未知世界沟通的媒介,是能够上通天地鬼神的宗教礼器,亦是受命于天的神圣象征。历朝历代的君王将青铜器视作国之重器,而金石收藏与研究自宋代以来就成为了文人社会的重要传统。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大展用一部恢弘的青铜器收藏史,穿越数千年沧海桑田,带我们回到那个辉煌迷人的青铜时代。
2018年2月25日至5月13日,“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大展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隆重举行。这场亮相于密歇根湖畔的青铜大展历经数年筹备,精心荟萃了180余件珍品。其中不仅包含了来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美国其他各大博物馆与私人藏家的珍藏,更重要的是此次与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合作,汇集了一批远渡重洋的国宝级文物。正如展览标题中“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所言,“吉金鉴古”并非是一场单纯的器物陈列与介绍,而是旨在勾勒出一部贯穿千年的青铜器收藏史。
本次展览的成功归功于中美双方的通力合作。“吉金鉴古”中的清代皇家旧藏大多来自故宫博物院。清中期是皇室青铜器收藏的一个高峰。此次展览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清官青铜器旧藏与宫廷仿青铜器型造办的文玩器皿,还展出有由乾隆皇帝亲自发起编纂的重要金石学著录《西清古鉴》原本。除皇室收藏之外,本次展览也着重展现了文人一脉的青铜器收藏。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对青铜器的著录和发表整理作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如晚清收藏家潘祖荫在《说文古籀补叙》中所自述:“以所得奉入尽以购彝器及书……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大量展品就展现了一批重要的文人青铜器收藏和珍贵的学术资料。《吴大潋愙斋集古图》长卷正是晚清文人士大夫金石研究的重要体现。长卷辑录了收藏家吴大潋数十件青铜器的全形拓印,在展厅中一字排开,蔚为壮观,引人驻足。
在一间单独的展厅中,陈列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柉禁组器和故宫博物院的“天下第一鬲”师趁鬲,而展厅背景则是一张巨幅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摄于1907年,当时的著名金石学家、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在得到出土于陕西斗鸡台的柉禁组器后,为柉禁组器与师趁鬲留下了一张合影。时局动荡,波云诡谲,端方遗族后来通过美国收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之手,将柉禁组器出售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整整百年后的今天,这两件承载风云的传奇青铜器终于再一次重聚芝加哥,使得身处其中的观众们得以亲身参与历史,见证这一段佳话。
古人将青铜器称作“吉金”。对于现代观众来说,以吉金来鉴古,既是一个深刻而壮阔的主题,又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伴随着礼乐制度的日渐成熟,青铜器承载起道德标准、政治秩序,成为了社会制度的具象化身。人们对青铜器的钟爱与研究一脉相承至今,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精魂中。现代华人的文字、艺术、道德准则,都与上古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展厅中就选取了一段来自《仪礼》复原项目的短片,结合文献资料和新媒体技术,直观地再现了先民们在仪式中使用青铜礼器的场景。除古代文物外,这次展览亦涵盖有一系列当代艺术作品,均来自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的重要中国艺术家,积极探索了青铜文化在今天的表达。
“吉金鉴古”展览本身也着重开辟了别具匠心的互动活动。在展览的出口处,馆方特设了一间青铜纹饰拓印的体验工作坊。这些纹饰撷选自“吉金鉴古”的展品与其他馆藏青铜器,借助现代的激光切割技术对纹样进行了高精度复原。观众们被邀请使用纸笔在纹饰上摩挲,动手来制作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拓片,进而得以对展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使观众与展品之间得以互动与对话。这一深受欢迎的体验活动正是博物馆在新时代展览模式中的勇敢尝试。
为了对这场展览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邀请到“吉金鉴古”展览的总策展人、著名学者、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普瑞兹克专席主任汪涛博士,从策展人的角度深入解读此次青铜大展。
问:“吉金鉴古”展品的年代跨度很大,从商周、唐宋、明清一直到当代,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艺术史。在选择展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标准?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
汪涛: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收藏史。商周时期,青铜器多与祭祀有关,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到了汉代,人们则把古代青铜器视作吉兆和祥瑞,认为获得青铜礼器即象征着得到天命。自宋代起情况有所改变。一方面,宋徽宗开始用青铜器为他的新政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来说,宋代的文人诸如吕大临、李公麟等开始以金石学的角度来看待青铜器,把青铜器作为历史研究的物证。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叫“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因为这两条脉络贯穿了青铜文化与收藏史。我们这次选择文物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在皇室收藏和文人收藏中具有代表性或曾起到过转折作用。实际上皇室、文人收藏这两条脉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皇帝可能会将他的收藏赐予臣民,而原本属于皇家的青铜器也会在特殊时期流人民间。譬如我们这次展品中有几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潘祖荫旧藏,它们原先也是见诸《西清古鉴》的皇室收藏。大体上说,清代皇室和民间的收藏互动性比较强;而像宋徽宗则倾向于由皇室垄断青铜礼器,所以那时很多民间青铜器反而都成为了宫廷藏品。
问: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有着悠久的亚洲艺术收藏历史,尤其它的青铜器收藏在欧美是负有盛名的,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芝加哥与中国青铜器的渊源呢?
汪涛:芝加哥藝术博物馆的青铜器很有意思,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的话,可以读一读曾任我馆东方艺术部主任的查尔斯·法本斯·凯莱(Charles Fabens Kelley)与中国著名学者陈梦家于1946年合撰的《白金汉藏中国青铜器图录》。这本书近年也已经出了中文版,很有参考价值。20世纪初期,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有一位重要捐赠人凯特·白金汉(Kate S.Buckingham)女士,她为我馆捐献了大量重要藏品。白金汉女士的收藏顾问是当时美国的知名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博士。劳费尔博士一生研究亚洲文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最早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员,后来到了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也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担任客座馆员。劳费尔博士帮助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青铜器馆藏。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在20世纪初就成为了美国最早开始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博物馆。从今天的角度回顾验证,劳费尔博士的眼光独到而准确。他为白金汉女士挑选的藏品几乎全都是精品,非常令人佩服。
问:这次展览中数件展品曾被收录在您十年前的著作《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中。从今天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青铜器研究在欧美的发展与现状?
汪涛:这次展览中有很多展品来自美国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20世纪初中国局势动荡,无论是皇室还是文人的收藏都受到了一定冲击。两者相比之下,皇室收藏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当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大多数的收藏受到了保护;但私人收藏在那个年代就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很多收藏家的经济状况都出现了问题,许多文物不得不被拿出来变卖,而当时国外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也确实愿意出很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文物。因此有许多精品,譬如潘祖荫家族的很多青铜器旧藏,就在那个时候流散到了海外。正因为这一历史背景,青铜器收藏从20世纪初期起渐渐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所以我们也有意地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这些和我们主题相关的海外青铜器。这对于阐述本次的展览主线“青铜器收藏史”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吉金鉴古”大展收录了几件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您能否作一下简单的介绍?您怎么看待传统艺术,尤其是青铜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表达?
汪涛:青铜器文化在当代是有传承的。时至今日,青铜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的纪念碑,譬如北京的中华世纪钟,都会用青铜礼器的题材来做一个母体或者借用许多青铜器的纹样。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当代艺术家会对原来的创作方式做一些突破和嬗变。“吉金鉴古”选取了泰祥洲、洪浩、徐震等人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在运用古代的题材的同时,把当代的因素加入其中。作为当代人,我们在欣赏、研究古代青铜器时,自然会得到“理解”与“不理解”,甚至错位的“理解”。作为一场展览,非常重要的是能引发观众的思考,让展品本身来说话。我们希望在展览中加入这些当代的观念,让观众思考后再回过头来看古代的青铜器,可以解读出很多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
问: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长期规划中将亚洲艺术和当代艺术列为博物馆未来发展的两个重要领域。我们看到“吉金鉴古”的展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这也是近年来中美两国博物馆的一次重大合作,您能否谈谈这样的合作在全球化语境下会带给博物馆什么样的可能?
汪涛: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现在正在和许多中国博物馆展开合作。我们和故宫博物院已经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我们和上海博物馆也有很多交流,特别是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借了很多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展览的成功也是多方合作的具体成果,从筹展、布展到开展,故宫和上博的专家都亲身参与,解决了许多学术上和陈列上的问题。2018年9月我们也会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与Terra基金会收藏的美国现代艺术精品送到上海博物馆来展出,会把美国最重要的一批现代作品带给上海的观众。从全球化的语境下看,相比于十几年前的情况,现在随着中国博物馆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机构正在越来越多地引進国外的展览。随着展览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中国博物馆的主动性也越来越强。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和国外的博物馆都在互相提升自己的定位。所以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也是全球化合作的产物。
“吉金鉴古”展览作为一场成功的海外中国艺术展览,昭示着中国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正日趋上升,也映射出近年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得到的热忱支持。在这个蓬勃发展又不断变革的新时代中,青铜器文化乃至中国艺术该如何在现当代艺术的大潮中依然保持强盛的生命力?这无疑是一个宏大又令人振奋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