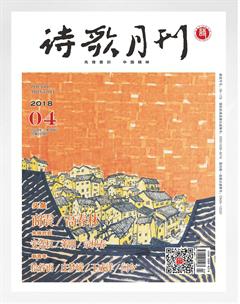山阶(组诗)
宾歌
第一次跟父亲进山
父亲在前面带路
他要去祭奠一个亡人
山势陡峭,头顶上,天似乎只有一线
偶尔听到几声鸟叫,在身前
或在身后,不可捉摸
父亲走得很疾,背影越来越小
我害怕他撇下我
走过了很多坟地,他牵着我说
不要畏惧死者,他们把骨肉交给泥土
喂养了草木
以后,我每次进山都觉得释然
倒是在山下,常怀警惕之心
河里站着废弃的桥墩
它们与河岸的几枝残荷对视
站在水里。被冬日的暖阳挽留
一对白鹭捎来田野的消息:水正在消逝
青苔铺盖,迟暮的桥墩变得柔软
那些曾经渡过的人们不知所踪
两岸生长出高楼,透过行道树看到
江面支离破碎。黄昏漩涡一般运动
每一帧画面的血色迅速地趋于饱和
仿佛那些留守老人,用几根残骨
消磨着流水。一条河流短暂的撕裂之痛
我的老母亲,在失去她的男人之后
坚持站在河里,截留来自上游的记忆
弧光
打开光。一粒果实的收藏
沿着她的弧度,找到肌肤里的黑暗
火焰与水需要一个容器,一朵花
携带着它们慢慢结痴
她先是经过了春风,轻手轻脚
用一根火柴,点燃
藤蔓上那些灿烂的欲念
她选择做彩虹的邻居,完成一次盛开
现在。她知道不是每一朵花
都可以与时间达成契约
田野里也会有一些空壳。现在
她留住弧光,强电流的爱
让一滴雨水琥珀般包裹
美得透明而持久
山阶
空山新雨,山阶上青苔显得寂静
秋风最先送走一片叶子
果实,隔着一截枯枝
抛弃了语言,在光芒和雨水中隐身
一个山民手持弯刀走进深山
砍去路过的荆棘、杂草
站在高处,他不仰望云朵
愈发怜爱低处的炊烟
被山神供奉,坠落是每一粒种子
向生的欢喜
而他仅用一个伸手的姿态
就捕获了一株植物羞于言说的
朴素之心
在草原看到十亩葵花
风吹瘦了草原。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
近看,它们美得咄咄逼人
一条狗追着落日向远方奔去
另一个方向,赤裸上身拔草的妇人
从容伸直腰身
不慌不忙地走向蒙古包
她穿上衣服出来
在门口立起一个稻草人
她宽大的袍子里
十万粒葵花籽正在灌桨
黑夜铺展开来
葵花地里,许多星星不停地摇摆
她吹灭烛火,周身都是月光
端午节,江水不会放慢脚步
风从来没有真正闯进水里
脚步太轻,一个人抱石投江
水在楚国停顿了一瞬
源头有人唱《离骚》,路漫漫兮
在魏晋、在民国。有风来吹
在2017年端午,江水急于归海
时光蓄积起来
近尾洲水很深,云朵很浅
从草木出发,采一束艾条插于门楣
我有偏头痛,这是楚国的顽疾
夕阳下,一条鱼噗嗤一声
鳞片上的光芒照亮了我
旷野
草棚、守渔塘的人,都老了
乌云在上,风雨走得更急
低处是水里的鱼
草棚压垮老人的时候
我十岁,正在田里插秧
没去参加他的葬礼
他抱过我,用胡须扎过我
带我扯光了菜地的野草
他告诉我,世上没有累死的人
憋足一口气就能多活一阵子
我去过他坟头上两次
旷野中,黄土包憋足了一口气
风吹我
风吹断了枯枝,吹不断流水
作为一场暴动的武器
它是公平的,绝不会吹破江山
我可以随风,也可不随
只要我有足夠的定力
风吹到花上,带走一滴蜜露
但会留下果实。在刀刃上
风也会提心吊胆,使用分身术
风是一条善良的法规,驾驭雨水
洗刷蒙垢的草木,让它们配得上生命
风从贫寒处来,吹向繁华
却不沾染一点颜色。风吹我
如同吹过一条河流的漏洞
我在风中迁徙
一块礁石成了我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