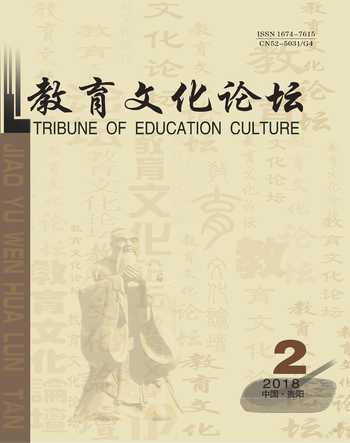论王阳明“身心之学”成立的根据、问题及启示
方英敏
摘要:从身心关系的角度看,王阳明“身心之学”建立在身心同一性的预设之上。这一预设既是“身心之学”成立的内在理据,又为之留下了并不严密的理论缝隙。由于在身心关系迷失了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思考,这使王阳明“身心之学”弱于身心贯通的工夫进路的客观性、公共性建设,进而导致其主观初衷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免于空虚、猖狂之态。因而,恰当理解身心关系,将是王阳明“身心之学”超越自身局限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王阳明;身心之学;身心关系;同一与差异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2-0007-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2.002
與“口耳之学”相对的“身心之学”在王阳明哲学中是一个醒目的议题,也为学界所重。学者对王阳明倡导“身心之学”的初衷及“身心之学”的内涵都已做精当论述。[1]从初衷看,王阳明“身心之学”远承儒家传统崇尚“为己之学”“成圣”的终极价值追求,近反朱子理学执着“口耳之学”、别求知与成圣为二事的立场。“从内涵上看,所谓身心之学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与入乎耳出乎口不同,它以身体力行为自悟的前提,将心体之悟,理解为实践过程中的体认(表现为“体”与“履”的统一);其二,体与履的目标,是化本体(心体)为内在的人格,并使之与个体的存在合而为一。”[2]在此基础上,继续就“身心之学”成立的根据、问题及启示予以追问,则有助于对此议题更为深入、全面的把握。
一
从杨国荣对王阳明“身心之学”的内涵概括来看,所谓“身心之学”是指“体之于身”“以身体之”的“身—体”哲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身而心的“体知”,由“身明”上升为“心悟”,此即阳明所谓“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己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身明”是“心悟”的前提与基础,譬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3]4,只有奠基于一己之“身”的“自痛”“自寒”“自饥”的切身体验之上,才能真正在“心”的层面上获具“知痛”“知寒”“知饥”之意。二是由心而身的“体之”,由“心明”落实为“身履”,化“心体”为“身体”,当“心体”化为个体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行为时,它就有了“与个体的存在合而为一”的感性确证了。王阳明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为例说明,知孝弟的“心明”只有落实为行孝弟的“身履”,则孝弟才由良知化为明觉。如果上述对“身心之学”的内涵分析成立,那么“身心之学”成立的根据便了然起来,此即:王阳明论“身心之学”,预设了身心关系,建立在或者说绕不开对身心关系的认知,因为无论是由身而心的“体知”还是由心而身的“体之”,“体知”“体之”所沟通的两端便是身与心。从逻辑上讲,身心之间只有是统一的,“体知”“体之”之发生才有可能,若身与心截然两立,身心之间的贯通便无可能。
从文献看,王阳明并未就身心关系予以专题论述,而是在讨论相关问题时论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行关系。身心关系与知行关系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如果说“知”是“心”之“知”,“行”是“身”在“行”,那么知行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身心关系。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就在于“知行合一”是“身心之学”的内在要求,无论是由“身体”而“心明”,还是由“心明”而“身履”之贯通无碍,说到底就是“知行合一”。对于知行关系,王阳明有一段经典表述: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凭的便罢。”[3]3
在这段话中,王阳明实际上把知行关系描述为三个层面:一是在本体(本来如此之谓)层面上,“知行本一”,所谓“知行的本体”,就是本来如此的知行关系;二是在现象层面上,“知行两立”,因私欲隔断,出现知孝弟而不行孝弟的分裂现象;三是在理想、目标层面上,“知行合一”,所谓“复那本体”。这三个层面是关联着的。“知行合一”之必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然出现了“知行两立”的现象;“知行合一”之可能,是因为在本体层面上“知行本一”,若知行本来不一,那么无论怎么“复那本体”便复不回去。
王阳明倡知行合一之教,是一件接受起来较为费劲的事情。从文献看,王阳明的学生如徐爱、九川等接受起来都觉吃力,所以就此问题曾往复请教于先生。知与行为什么是二而一的关系?王阳明除了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3]1124“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3]37等知与行互训的思辨方式解释外,还最擅于从身心关系上晓喻知行本一之理。他曾以《大学》所谓“好好色,恶恶臭”为喻说明“知行本一”。在这一解释中,王阳明所隐藏的逻辑是,如果说见好色、闻恶臭是知,好好色、恶恶臭是行,那么逻辑上只有在身心统一、贯通无碍的情况下,从见好色、闻恶臭之知到好好色、恶恶臭之行的同时发生才有可能。因之,只要懂得“身心一体”的道理,“知行本一”便是再也明白不过的道理。王阳明在与九川、希颜论学时循循善诱,最后使九川“一言而悟”“知行本一”的“一言”正是身心同一之理:“惜哉!此可一言而悟!……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3]79-80这里王阳明明确肯定了身、心之间的统一关系。
以对身心统一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王阳明论“身心之学”往往都落脚在身心关系上。这一点,在他与萧惠的论学中看得更为明白。萧惠从“身心之学”之要求,“一心要做好人”,但总觉身与心之间难以贯通,“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已,不曾为个真己”[3]31。王阳明认为,萧惠于“身心之学”不得要领的症结在于陷入身心两立的状态之中,未曾领受心对身的主宰作用,“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乐,所以不能克”,而滞留于“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的声色货利之境。萧惠茫然于以躯壳为己,这无异于认贼作子,而“真己”乃是“身心一体”之己:“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3]32,若把身、心判为二事,则学者在身心上践履一遇刀割针刺,便忍耐不过去。这就是说,学者只有领受身心同一之事态,才能真正挺立“真己”,达到身心交养的为己目标。
然而,王阳明认为身、心虽然在本体层面是统一的,然而在现实层面由于声色货利的私欲隔断又常存分裂现象。于是,就有了徐爱所看到的知孝弟而不行孝弟的情况,也有了萧惠治学仅仅“在躯壳上起念”的现象。身与心,在本体上是统一的,在现实上又是分裂的,这构成王阳明对身心关系的认知的复杂形式,也是倡导“身心之学”的前提依据。所谓“身心之学”,就是从身心两立的分裂状态导向身心统一的本来如此的理想状态。从本来如此的层面看,身心是统一的,因而它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从现实层面看,因习心、私欲的阻隔,身、心齟龉,因而贯通身心,导向身心自由的状态又极为必要。如何扫除习心、私欲的阻隔,贯通身心?王阳明极为看重工夫的作用。在与德洪论学中,德洪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3]103王阳明“然其言”,指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3]103在王阳明看来,心体原本明莹无滞、无善无恶,但因习心、私欲影响受到蒙蔽,又有善恶在,此乃心体之存在常态,然当格、致、诚、正、修等“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3]103。一番番功夫后,心体重回明莹无滞状态,也就是它流布周身,形于颜色,扩充四体,发于事业之时。
二
王阳明“身心之学”的成立根据如斯,从效果看,遵循此学是否实现了为己、成圣的目标?王阳明本人或许是极好的象征,他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足以令学者对“身心之学”的积极效果有足够的想象空间。然而,从消极描述看,它的问题亦是存在的。黄宗羲在肯定阳明学“以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4]7的同时,亦指出阳明后学最后终“浸流入猖狂一路”[4]8。王阳明论学之本旨原本在于“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的凌空蹈虚之病,而阳明后学却非但未能于此成就,还恰恰落入猖狂、玄虚之旧弊中,这不免令人深思。从原因看,阳明后学之问题,固然与后学本身有关,但与阳明“身心之学”本身固有的理论缺陷脱离不了干系。正是阳明学本身不够严密的理论缝隙,为后学见缝插针的随意发挥准备了理论温床。
阳明“身心之学”不够严密的理论缝隙的现象表征就在于身心贯通的工夫之路缺乏客观性、公共性。面对世俗“记诵辞章”“言之太详”“析之太精”的“繁琐”的治学之路,阳明崇尚“简易”,屡言治学“只是一个工夫”,“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然而,简则简矣,其流弊在于使学者治学的工夫次第陷入无所遵循之境。本无硬性遵循,也就可以随意发挥。
对于“身心之学”的工夫,王阳明谈论最多的是两种:一是静坐,二是事上磨炼。王阳明“因厌泛滥之学”,首倡“静坐”,“屏息念虑”,并亲身实践,后鉴于静坐可能陷入虚寂之弊,又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3]81。但是,“静坐”“事上磨炼”的工夫次第是什么?我们很难从阳明的论述中梳理出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流程。从文献看,王阳明谈论工夫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思辨意义上的本体与工夫之辩,于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儒家之共识,即:“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二是论工夫的重要性,劝勉学子为学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为学之要,只在著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在身心上理会。切忌轻自表暴,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3]117“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3]118,敦敦教诲近乎咬牙切齿;三是工夫的效果描述,如德洪“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3]180。王阳明对工夫有如上方方面面的谈论,但对工夫次第未有言之凿凿的明晰表述。与此相应,王阳明把工夫的操作性交付给学子当下即得的心灵体验: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3]83
学者读书,只要归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著句,拘拘解释,定要求个执定道理,恐多不通。盖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于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归在良知上体会方得。[3]968
吾契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得知。今却只是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3]176
在“于心上体验”“当下便自得知”“解心”与“泥文著句”“执定道理”二端,王阳明态度鲜明,喜前者而厌后者,似乎并不认为工夫可以“泥文著句”“定要求个执定道理”地按图示操作。王阳明不信任言说,认为“古人之言”的作用仅仅是“示之向往”,即示人之理想之境,至于怎样达到这种理想之境则在于个体自身的“体会”。否定工夫的可言说性质,这实际上是把工夫理解为一种“运用之妙全乎一心”的主观、个人的心灵体验,自失于工夫的客观性、公共性。一种工夫若不能言说,言之凿凿地标示其次第、步骤,它必定是主观的、个人的,进而它的可重复性,以及普遍有效性都得不到检验,要之,就是工夫的客观性、公共性得不到保障。
在阳明“身心之学”中,工夫的主观、个人的体验性质,有别于按繁琐的戒律、流程操作,在形式上看当然给人以“简易”之感,但没有规则约束的工夫同时就意味着随意性。在阳明后学中,穿凿附会、随兴立论也就在所难免。如王龙溪把王阳明所谓“心体上著不得一念留滞”理解为“任良知流行”,结果是良知未能朗显,倒是私欲披着良知的外衣肆意流行而不自知。又如罗汝芳曲解阳明“良知即是个未发之中”之义,大谈不学即知。刘宗周曾批评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4]1572自以为是的学子对良知随意发挥、涂抹,“猖狂者”与“超洁者”眼中的良知的面目各各不同,且又都落入玄虚、放肆之境。阳明学的乱象并未表现在阳明本人身上,但症结却内蕴于王阳明所创立的学问之中。由于弱于工夫的客观性、公共性建设,失此保障,良知与致良知的身心之学也就有了滑入空虚、师心自用的面目全非之机。
三
王阳明在世时,阳明后学所表现出的凌空蹈虚、放言高论的现象即已显现。他曾自陈:“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3]1014王阳明看到自己倡导的“身心之学”在现实效果上走样,南辕北辙,当然后悔而已。悔则悔矣,然而王阳明是否找到了个中原因,却是存疑。这个原因,就在于工夫的客观性、公共性之虚弱,进而使学者的为学之路失却遵循与约束。对“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之现象,王阳明强调“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3]36王阳明看到了病症,但开出的方子却仍然是虚晃一枪,强调“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但“次第”具体到底“是什么”,如何“积累”的问题仍不甚了了。这说明,王阳明并未看到自家学问弱于工夫的客观性、公共性建设之弊。
与阳明学工夫次第论建设的消极、空疏相比,朱子学一系于此要显得积极得多。譬如静坐之工夫次第,受到朱子学影响较深的一系的学者贡献颇多,如颜山农对“七日闭关开心孔昭”的闭关静坐法的描述:
收拾各人身子,以绢缚两目,昼夜不开;绵塞两耳,不纵外听;紧闭唇齿,不出一言;擎拳两手,不动一指;趺咖两足,不纵伸缩;直耸肩背,不肆惰慢;垂头若寻,回光内照。如此各各自加严束,此之谓闭关。夫然后又从而引发各各内照之功,将鼻中吸收满口阳气,津液漱噀,咽吞直送,下灌丹田,自运旋滚几转,即又吸噀津液,如样吞灌,百千轮转不停,二日三日,不自巳已。如此自竭辛力作为,虽有汗流如洗,不许吩咐展拭,或至骨节疼痛,不许欠伸喘息。各各如此,忍捱咽吞,不能堪用,方许告知,解此缠缚,倒身鼾睡,任意自醒,或至沉睡,竟日夜尤好。醒后不许开口言笑,任意长卧七日,听我时到各人耳边密语安置,曰:各人此时此段精神,正叫清明在躬,形爽气顺,皆尔连日苦辛中得来,即是道体黜聪,脱胎换骨景象。须自辗转,一意内顾深用,滋味精神,默识天性,造次不违不乱,必尽七日之静卧,无思无虑,如不识,如不知,如三月之运用,不忍轻自散涣。如此安恬周保,七日后方许起身,梳洗衣冠,礼拜天地、皇上、父母、孔孟、师尊之生育传教,直犹再造此生。[5]
高攀龙之《复七规》:
复七者,取大易七日来复之义也。 凡应物稍疲,即当静定七日以济之,所以休养气体,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匮者也。先一日,放意缓形,欲睡即睡,务令畅悦,昏倦刷濯。然后入室,炷香趺坐。凡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精神自然凝复,不待安排。勿着方所,勿思效验。初入静者,不知摄持之法,惟体贴圣贤切要之言,自有入处。静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后,尤宜警策,勿令懒散。饭后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浊。卧不得解衣,欲睡则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则精神充溢,诸疾不作矣。[6]
又《山居课程》:
五皷拥衾起坐,叩齿凝神,澹然自摄。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潄毕,活火焚香,黙坐玩易。晨食后,徐行百步。课儿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读书。午食后,散步舒啸。觉有昏气,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至日昃而止,趺坐,尽线香一炷。落日衔山,出望云物,课园丁秇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灯随意渉猎,兴尽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寝。[6]
与阳明学对工夫次第论的闪烁其词、难得其详相比,这些对静坐工夫次第的描述已经技术化了很多,已然具有了可复制、普及的课程教学意义,尽管后者若与印度教之身心训练法的技术化水平相比也仍然有限。此种已然仪式化、操作化的静坐之功,明显与朱子学强调“渐修”“道问学”的为学之路契合,与阳明学所谓发明本心、当下便是的工夫进路神离。
从原因看,身心训练的工夫进路的“精细”与“简易”之别,也仍是表象,其根由在于朱子学与阳明学处理身心关系之别。在身心关系上,王阳明持“身心同一”论,认为无身则无心,无心则无身。这一论断,似乎很是“辩证”,也符合人的日常经验。但它所内含的问题,如果与朱熹的看法相较,便显示出来了: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第九)
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慎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朱学语类》卷第十四)
与王阳明一样,朱熹论身心关系也是与知行关系耦合在一起的,因为知行关系实质上是身心关系。学者常以为“知行合一”论乃王阳明的专利,其实朱熹也持此论。但与王阳明不同,朱熹认为知行合一乃是认知行两立的差异为前提的,知与行,如同身体之目与足,是独立相异、无可互相取代的两元,且“须先知得,方行得”,因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一个把知落实于行的现实实践过程。朱熹“知行合一”论,在王阳明看来,是把知行分为两截。然而,其实,只有朱熹的“知行合一”论才符合形式逻辑,此乃同一与差异的辩证:言同一,以差异为前提;言差异,着眼于同一。合一乃是同一,言知行合一,若不以知行两立的区分性为前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若知即行、行即知,知行本一,那么知与行还要合个什么。这在道理上讲不过去。正是在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上,王阳明迷失了,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3]84。所谓“一念发动处”作为“知”是一种主观意向性,属于脑海中的观念活动,以此为行,这实质上是模糊了精神与实践的界限,把心理与行为混为一谈,取消了行。
逻辑上,只有建立在知行两立的二元紧张关系基础之上,知行合一的工夫才有着落。若知行本一,则去做知行的“合”的工夫便无必要。在此,王阳明学生的徐爱的理解是对的:“古人说知行分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3]4倒是,王阳明认为徐爱的理解“失了古人宗旨”,有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味道。朱熹就反复劝诫学者:“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当然,王阳明也说过好多强调过工夫重要性的话,但同时其学理本身又内涵着工夫取消论,因为既然知与行都不过是“一念发动”的心理活动,那么知行合一在观念里完成就可以了,亲身实践的做的工夫已无必要。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学及其后学滑入夸夸其谈的空虚之弊,有着阳明学内蕴的因果逻辑。王阳明倡导“身心之学”之初衷乃是成圣。按儒学,所谓成圣,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亦即以指向天下有道的亲身实践为成圣的最高境界。然而,王阳明大力倡导“身心之学”的初衷与其最终效果上的相左关系,不能不令人有所思。
從儒学的渊源来看,王阳明“身心之学”直承先秦思孟学派重体验一脉。孟子讲“养浩然之气”,也是诉诸于心理上的道德意志的凝聚,至于“怎么养”的工夫次第亦是难得其详。阳明学“从朱子古典理性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外在性的立场转向主观性、内在性、主体性、内心经验”[7],接续了思孟学派精神,但也在这一转变中未能领会朱熹理学重思辨、分析的知识论的合理内核,结果乃是以“身心同一”的名义取消了对身心关系之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思考。因而,这意味着恰当理解身心关系乃是王阳明“身心之学”超越自身局限的关键环节,甚而言之,可能也是进入身体哲学、美学研究难以绕开的节目。
参考文献:
[1]朱晓鹏.论王阳明的“身心之学”[J].哲学研究,2013(1).
[2]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2015:219.
[3](明)王守仁,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明)颜钧,黄宣民点校.颜钧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8.
[6](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58.
[7]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责任编辑:赵广示)
Abstract: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Wang Yangmings “Body-Mind Study” is based on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identity of body and mind. This presupposition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body and mind”, but leaves a rigorous theoretical gap. The lost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makes Wang Yangmings “Body-Mind Study” weaker than the objectivity and publicity constructed through strenuous efforts of study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ody and mind, which leads to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objective effect, unable to avoid the state of emptiness and rampancy. Therefore,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will be the key link for Wang Yangmings “Body-Mind Study” to go beyond his own limitations.
Key words:Wang Yangming; “Body-Mind Study”; body-mind relationship; identity and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