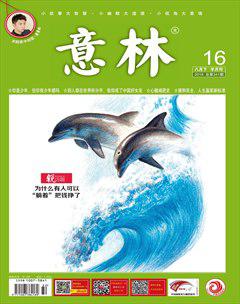真正的痛苦不可描述
阿滚
五六岁大的时候,1984或者 1985年一个初冬傍晚,我跟爸爸两个人在家吃晚饭。饭刚盛了一半,就听窗外传来荒腔走板一段二胡,紧接着就是一个带哭腔的男声操着方言的乞讨。
我和爸爸探头去看,是一老一小的两个外乡人,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穿着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身背布包,拽着不知道是她爸爸还是爷爷的衣角。
人都散得差不多了,那男人回过头来,视线刚巧跟我撞上,那个男人一张苍老扭曲的脸藏在一顶破帽子下面,肩上一前一后搭了两个又大又脏的旅行袋,那样子实实在在把我吓得缩进窗里。一转身,发现爸爸早不在窗边,正拿着一口“钢钟锅”把一桌饭菜挨个往里倒。 我急了,那是我们全部的晚饭,给他们了我们吃啥?更何况,外面多冷啊……
爸爸掏出五块钱放在锅盖上,大声重复了一次:快点!给他们送去!
合作社大门口挂着军绿的夹棉门挡,那个爸爸扯起一角,正在给女儿挡风。 我把饭菜和那张皱巴巴的五块钱递过去的时候,他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拉扯闺女非要给我鞠躬,我几乎是逃命般地转身飞奔离去,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充满了胸膛。
即便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那种被灼烧的剧痛依旧没有半分消退,还有那个男人像鹿一样湿漉漉亮晶晶的眼睛,花白的胡茬和从破帽子下露出的头发,那个跟我一般大的女孩棉袄里褪了色的血红毛衣……
我就这样一路大哭着跑进家门,看到爸爸坐在光秃秃的餐桌边,既没有问我是否完成任务,也没问我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
落地台灯照亮他半边好看的脸,我知道他心里和我有着一模一样的难过。

我的爸爸自小失去母親,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因此幼时生活异常艰苦,我曾听妈妈和外婆讲起当年他们同为邻居时,爸爸常年怎样地挨饿受冻,有时靠同情他的邻居,比如外婆,给省口吃的或给添件衣物,更多时候就只有默默忍耐,后来还因此落下了终身重病。
他一生每天都过得异常艰辛,因此每每见到他人落难受苦,就绝不能坐视不理。
我小时候好奇心极重,常尾随别的大人和孩子去商店,看玻璃柜台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有时一看就是半天。
我还记得那些上发条会跳的油绿色青蛙,敲起来叮当作响的钢片琴,或是晶莹剔透的玻璃跳棋。
我从没有钱买过其中任何一件,但也不觉得难受憋闷,就是站在一边看别的孩子挑挑拣拣地摆弄,也觉得十分快乐有趣。
我虽然淘气顽劣,心里却没有半点阴霾,都因爸爸对我异常强烈的影响。
他从没跟我说过半句大道理,我只是跟在他身后,学会以他的方式打量世界和感受生活。
对爸爸来说,那时的贫穷比起他年少时的经历已宛若天堂,好得怎么看都看不够,怎么爱都不过分,对别人的生活自然没有半点羡慕和兴趣。
我至今所能想起的,永远是我绕在他身边蹦蹦跳跳,仰头便能见他一张似笑非笑的年轻脸庞,不论白天黑夜,都像被阳光照耀般闪亮好看。
唯有在那个冬夜,爸爸陷入长久的沉默中,唇边的烟头一亮一熄闪着猩红,他把烟灰点进空碗里,我们一直没有吃饭,也没有再讲过任何与那对父女有关的一句话。
我好像自然就明白了,生活真正的苦闷就是这样的沉默不可言述。
一餐饭能起到的作用就只有一个晚上,比起同情,首先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无可回避的切身疼痛,我当然知道那对父女夜晚要在冷冬里露宿,明天还要为了一餐饭乞讨哀求,这样的日子要怎样继续,怎么结束?用我小小的五岁头脑,都能明白,我来回这一通奔波,为此还挨了一夜的饿,结果却什么也不能改变。
我为自己的无力感到难过,也因对方的感激而充满愧疚。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到深切的悲伤,相比日后亲身经历的那些所谓“刻骨铭心”的伤痛都要强烈得多。
我几乎从未跟人说起过这段记忆,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在回想的同时忍住哭泣。我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那种至今依然的悲伤也不是伤感或愁绪。
人生在贫困之下还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而又束手无策的磨难,对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是那样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即便如此,正因如此,我们仍可尽力去做。
我的爸爸一定也是因为他人曾经的良善,才保住他始终映在脸上的那一点笑容,我也才有幸在清苦贫穷中拥有记忆中那般明媚清朗的童年。
想到我后来上学,自小学到高中,总不断有老师跟我妈妈感叹: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没见过像你女儿那种浑身有那么多缺点,但就是对自己满意得不得了的小孩。
怎么能不满意呢?相比这世上已知和未知的不幸,我的人生就像老舍说的——永远年轻轻的,生命像花那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