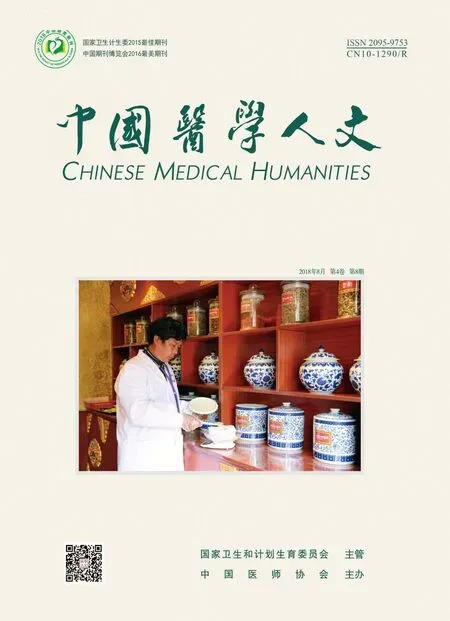默 守
文 /靳 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摄影/迟 辉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姥姥姥爷相继去世。
我的姥姥死于帕金森,那时的我还没有学医,不知道帕金森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更不能以医学生的视角评估症状与痛苦,现在的我也不忍逐一细想。
我的姥姥姥爷是农民,淳朴善良,育有五女一男,年龄差距很大。妈妈在女儿中排行四,因小姨不能生育我是姥姥家孙儿辈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备受宠爱,姥姥除了将姨妈舅舅每周送给她的好吃的存起来等到周末我去了全部拿出来给我吃外,还会亲自下厨给我生火烙饼,彼时我的姥姥已经耄耋之年,白内障术后戴着厚厚的眼镜视物不甚清晰,而且已经患有帕金森,双手已有静止震颤,稍一停顿,便会无法抑制的抖动,夹住的菜会掉,碗里的粥会洒。
我的姥爷是那个年代罕有独生子,因他的母亲年轻时守寡,母子相依为命,我的姥爷沉默寡言,顶天立地,但不失柔情,他会在田间地头辟出一方土地种些西瓜、甜瓜等孩子们爱吃的水果。
那年我10岁,姥姥的病情日益加重,肌张力高到已经无法行走,即使卧床肢体也不是舒展的,蜷曲着,呈一个痛苦的角度,需要有人每天帮忙翻身、擦洗。起初我的姥爷什么都不说,自己默默地承担这一切,但是他比姥姥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迅速地,成了一根竹竿,三餐全是清水面条,连个鸡蛋都懒得下给自己。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姥姥的床旁,照顾她,更多的是倾听。
姥姥是个话多的人,没生病之前,就爱唠唠叨叨,饭桌上最常见的画面就是姥爷慢慢悠悠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喝酒,吃花生米;姥姥则喋喋不休的说着自己的担心:担心姥爷喝酒抽烟身体不好,担心大姨和大姨夫天天吵架夫妻感情不和,担心姐姐老大不小了还不结婚,担心哥哥工作不好娶不到老婆,担心妈妈一人照顾我太累,担心小姨无子后半生凄苦……她心细如发,老伴和孩子们的一丢丢风吹草动她都会琢磨再三,辗转难眠;但她也很心大,无论是白内障手术,还是帕金森卧床,她从不担心自己。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还能行走时坚持每周礼拜,即使卧床她仍天天祈祷仁慈万能的主将她孩子们要承受的苦都转移到她的身上。姥爷总是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帮姥姥翻身,大小便。姥姥睡着了他会坐到门槛上抽一根烟,烟雾升腾里他的眼神不复从前那般轻松。
姥爷消瘦得太快,三餐都吃不了一碗面条,抽烟确是一日多过一日,很快的他失去了抱起姥姥的力气。天气渐凉,他咳嗽加剧。姨妈舅舅们开始一人三天轮流照顾姥姥,给姥爷做饭。姥爷虽然“被解放”,但他完全没有放松的自觉,丰盛的饭菜也吃不了两口,仍是痴痴的守在姥姥的床前。即使是在院子里理发,眼神仍锁住晒太阳的姥姥。
姥姥的神志也慢慢出现了问题,她出现了谵妄的症状,清醒的时间很少,大部分的时间她挥动双手,用充满惊惧的声音大喊着“撒旦别过来,快走快走!”镇静催眠药并不能改善,姨妈舅舅们虽然不至于迷信到真有魔鬼,但是姥姥的这种癫狂,总让人有一种濒死的回光返照的不良预感,他们紧锁眉头,语调低沉。我的姥爷紧紧地握着姥姥的手,不眠不休,神态平和,仿若这还是那个喋喋不休关心他人的姥姥,他的发妻。
姥姥“发狂”了三天后,去世了,没有遗言,也许是身前关心的太多,说的太多,她倦了。姥爷仍是不发一言,只是喝酒。姨妈舅舅们尝试着将姥爷接到自己家里照顾,但他哪里都不愿意去,日日待在这所和姥姥有共同回忆的小院。姨妈舅舅们隔日会去看看他,做做饭,洗洗衣服,聊聊天,他仍是不说话。
姥姥去世后半年,姥爷在睡梦中平静的去世了。没有任何预兆。
姥姥姥爷用生死给我启蒙了:质朴的爱情,你说我听,不嫌你烦。有你在时,世间才有一个家。姥爷没有说过任何甜言蜜语,但是他用瘦弱的身板撑起了这个家,即使文革饥荒,他的妻子孩子从未挨过饿。妻子的唠叨让儿女们闻之心怯,但于他这仿若是世间最美味的下酒菜,幸福生活不可缺失的美妙韵律。就是这样,死亡不再是洪水猛兽,撒旦再恶,击垮不了人心。疾病会使你容颜枯槁,但在爱你的人心中,你一如初见模样。
(选自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李飞主编《叙事医学》课程教学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