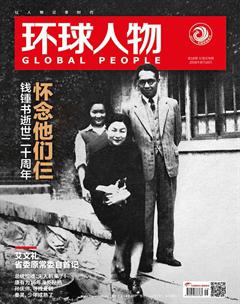孙庆伟,寻找夏朝
宫梓铭
他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认为当今仍需走出疑古时代,倡导研究者重建古史
孙庆伟

江西上饶人,生于197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参加山西曲沃晋侯墓地、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2018年5月出版新作《鼏宅禹迹》。
三皇五帝是历史还是传说?夏商周的夏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华夏文明的星火是怎样聚拢起来的?这些问题距离普罗大众有些遥远,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责任,更是梦想。
前不久,一本学术著作在社会上引起讨论,也让中国文明源头的历史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就是这本《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鼏,音同密)的作者。记者第一次见到孙庆伟教授时,他正站在陕西周原遗址的一个发掘探方里,在关中层积的历史地层中,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
我们的访谈,就是从长期被视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代开始。
用文化比较法重建夏代信史
环球人物:您新書的副标题是“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这涉及对夏朝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认知问题,既包括时空范围,也包括文化互动。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这一概念的?
孙庆伟:要讨论夏文化,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夏代是否信史,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寻找夏文化。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无疑义。上世纪20年代,少数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夏代的真实性,尽管应者寥寥,但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本书副标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主张。夏代的信史地位不是不能质疑,但怀疑要有理有据,要“拿证据来”。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我把这句话放在了书的扉页上,既表明我对邹衡先生观点的认同,更是想以此警醒广大读者。
书中基本沿用考古学前辈徐旭生、邹衡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大范围文化比较的方法“挤出”夏文化,特别是结合夏代的具体史实,尽可能地给出夏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环球人物:那么您用什么方法确定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呢?

孙庆伟:对于夏文化的上限,本书主要是依据“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来确定的。“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渐,特别是对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替代。而“禹锡玄圭”则是指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开始自中原向四裔广布。换言之,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礼仪符号(玄圭)开始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我们认为这种迹象的历史动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将夏文化的上限确定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有关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学上惯称的夏商分界,是一个充满纷争的学术问题,我在另一本小书《追迹三代》中曾有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现在夏商分界的讨论主要是从陶器文化的变迁上着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是每次王朝更迭都有特定的考古遗存,且这类遗存又恰恰被考古学家发现。我在书中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大区域的文化变迁,二是这一时期郑洛地区的城市建设的异动现象。最终,得出夏商分界应该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的结论。
环球人物:有人说,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的,比如《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哈佛中国史》则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这可能是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孙庆伟:西方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原因是多方面的。欧美考古学者比较偏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世界范围内看,文献史学发达地区,容易产生文化历史考古学,而文献贫乏地区,则容易催生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就愈加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两位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就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我认为这是很公允的看法。
“疑古”是构建“信史”的工具
环球人物:很多人认为,神话传说并不靠谱,甚至认为“三皇五帝”也不过是传说而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乃至与历史的关系呢?
孙庆伟:上古史中确实有不少神话和传说的成分。徐旭生先生曾分析过神话和传说产生的原因,因为初期文字的寡少,无法普遍使用,所以各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随着文字的使用越广泛,所发现的传说就越丰富,最后才会有人把它们搜集、整理、记录。如何面对这些材料,前贤早有思考。如徐旭生先生就指出,因为有人“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所以才极端疑古。他认为,这些传说与考古材料同等重要,因为“唯有靠了这些‘传说,我们才可能把这一段有文字以前的历史模拟想象出它的十分或百分之一二的真相,才可能把完全茫昧(不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先史文化时期,与有真实记载的历史时期,互相联系起来”。
环球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上古的传说中,发现一些“信史”的线索?
孙庆伟:应该说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禹征三苗”,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暂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战争。它背后其实是黄河流域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夷夏联盟与长江流域苗蛮集团的持续冲突,由此我们才可以洞察诸如帝舜“道死苍梧”、大禹“崩于会稽”等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
环球人物:您曾批评过当下的一些“历史怀疑论者”,他们是不是当初疑古派的余脉?
孙庆伟:实际上,现在很多“历史怀疑论者”并不是真正的疑古派,其别有二。其一,学术史上的疑古派,如顾颉刚先生,都是在系统论证的基础上,谨慎地、有理有据地疑古。而现在的怀疑论者通常只有怀疑之心。其二,真正的疑古派,“疑”只是手段,“信”才是目的,“疑古”只是用以构建“信史”的工具。
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历史对一个国家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对于大众的历史认知负有重要责任,不能轻言其无、轻言其伪。一些人今天否定夏代的存在,明天否定屈原的存在,这让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该从哪里入手建构自己的历史观呢?怀疑的时代,更需要考古学者的坚定与担当。
环球人物: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可能更需要通过“疑古”确立“信古”的过程。
孙庆伟:是的。上世纪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写过一篇《走出疑古时代》的宏文,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场大讨论,至今仍有余绪。我作为断代工程的工作人员目睹了工程始末,感受過中国史学界弄清自己历史源流的决心。最深刻的印象是1996年工程启动时,两院院士宋健同志那篇《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讲话,见地、眼界、水平都很高。讲到中国学术界对于三代年代学的纷扰时,那句“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让人真切感受到社会对于考古学的迫切期盼。
冯友兰先生把民国史家分为信古者、释古者和疑古者,此“三分法”在当下也有现实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民国史家还是当代学人,很多人都同时兼有“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面相,我们不必刻意把自己或他人归属于某一派。现代历史研究者理应融会贯通这三种史家所具有的先进性,一边批判、一边建设,既注重对传世文献的运用,更借重考古材料的史料价值,这或许才是最有效的古史重建之方法。
中国考古学界的“焦虑”
环球人物:近年来您一方面倡导考古学者重建古史,一方面呼吁让考古学更为大众所熟知,这里面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孙庆伟:有关这个问题,我愿意转引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两段话来解释。
对于重建古史的意义,尤其是重建上古史的价值,张先生曾说:“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显然是关键性的一段:中国文字记载的信史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始的,中国这个国家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形成的……我们甚至很可以说,许多人会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史学最大的贡献应该在三代。”
张光直先生还曾明确指出:“中国上古史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
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有不少人无视张先生上述认知,说到底,这是学术研究上的不自信。这种现状倘不改变,就难以在精神上构建起我们泱泱古国的历史大厦。
环球人物:您对“重建古史”的强调,让我想起了您曾提到过的张忠培先生。您说他一生走过的路,一生所说的话,一生所著的书,都是在思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焦虑”中为学科立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焦虑”是什么呢?
孙庆伟:中国考古学的“焦虑”可以从傅斯年说起,当年他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要追求“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与西方汉学争胜。当然,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学的使命已趋于具体化,可以用苏秉琦先生的“六十年圆一梦”概括,即“修国史,写续篇”。所谓“修国史”,是指以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所谓“写续篇”,就是指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中国续篇。这样庞大的任务和遥远的路途,自然使得中国考古学界充满了焦虑,也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自觉与自立。到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及其学生俞伟超、张忠培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仍是我们当今考古人思考的问题。
环球人物:您刚刚履新,执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大旗,在给2018年学院毕业生的致辞中,您呼吁同学们传承百年北大考古的“心传”。能否说说您如何理解这个“心传”?如何看待当代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的使命?
孙庆伟:既然是“心传”,必然不可言状。这是一种氛围、一种感悟。任何一个北大考古学子,当他直面“考古学思想家”苏秉琦、“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宿白、“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诗的考古学家”俞伟超等师长时,内心一定会有某种感触,荡起某种涟漪。
1988年,我从一所县级中学误打误撞走进北大考古系。邹衡先生是我的祖师爷,他曾反复对我强调,“做学问不是一天用功,一年用功,是一辈子要用功”。我的研究生导师李伯谦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总括这些先辈的功绩,其要有三:即李老师曾说过的“研究一流的问题,做一流的学问,当一流的老师”。一代代学人见贤思齐,薪火相传,缔造北大考古学科永远的荣光,这就是北大考古人的“心传”。
考古学是一门“为往圣继绝学,为民族立根基”的学科。前不久我提出北大考古学科人才培养的愿景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这也是我对当代中国考古学者使命的理解,那就是保护好文化遗产、解释好文明特征、传播好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