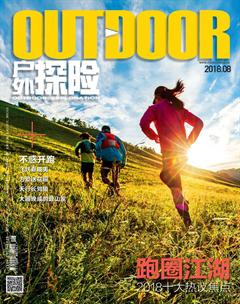环保斗士还是伪君子
欧阳凯
关键词:环保
关键词出处:2018年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跑比赛,获得第三名的团队中一名队员,被拍到在赛道多次随地乱丢垃圾,被举报投诉、取消赴美参赛的奖励名额。
赛道上丢失的水壶

我愣住了,脱口而出一串脏话。海拔4000米之上,40公里已经被我留在身后,我痛苦地回望上方,那奇形怪状的石头在我跑过的崎岖碎石路上摇摇欲坠。我的一个水壶从跑步背包的前袋中掉出来丢了,而前方还有一段难度未知的攀爬等着我。爬升20米还是100米?沉思片刻,看了一眼手表:6小时40分钟,目前仍保持着排名第二。
刹那间,我疲惫不堪的思绪给出一个最佳选择:管他呢,还有一瓶水支撑接下来的25公里,你能行的。此外,排名第三的选手大概已经追上来了。我转头向山下看去,检查了另一個水壶仍是满的。出发!
我往下坡跃了一步,接着刹车止步。不,我忽然想到,两天前自己不是还给参赛跑者做了一番关于环境保护的演讲吗?如果我把那个水壶留在那儿,不就变得彻底虚伪了吗?我发出了一声不情愿的呻吟。好吧,就这么做。转过身,双手轻压膝盖,一步步往上爬,倒回去寻我丢失的水壶。
两天前,在丽江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的说明会上,我作为一名精英选手站在几百名跑者面前演讲。组委会给我报销了机票、住宿以及报名费,就是为了让我来讲一番话。我满怀责任心地给跑者们分享自己对山野的热爱、环境伦理的理念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它。最终,我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从山里寻回了丢失的水壶,还带回9个黏糊糊令人恶心的能量胶包装袋,一起带回了终点。这样就是环保主义吗?
“伪环保”有什么意义

最近,“环保”这个词在中国的每个领域和行业频频出现,从超市的塑料购物袋到矿泉水瓶身上都印着“环保”字样,事实上,这些难道不是伪环保的表现吗?塑料袋令海洋和水道阻塞,生产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背后却要消耗3升水,这是巨大的浪费,使得本已有限的资源无法持续使用。尽管如此,整个行业都在往自己的产品上面贴“环保”标签而且毫无约束力,这种趋势下,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那些公司不想错过良机。“环保”这个词很潮、很先进、很西方,是符合消费者期待的一种主张,企业当然乐意提供这样一种期待。
同样地,在中国呈爆发式增长的跑步圈,也正在冒着脱离了意义谈环保的危险。
“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保护这个词。” 马德民,Vibram香港100推广者、环四姑娘山超级越野赛总监,他跟我说过这句话。如果人人都宣称“环保”而实际上缺乏一定标准,那么,很快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别做标题党,马德民说,“如果你真正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家,就不会去肆意在家里扔垃圾或者搞破坏。” 行动胜于空言。那么,中国的跑步圈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在丽江演讲之后,我返回去调查该赛事网站上组委会对环境保护做出的以下承诺:
“环保:禁止随意丢弃垃圾,请使用垃圾袋带走所有个人垃圾。请勿惊扰沿途的野生动物或破坏野生植物。另外,组委会在比赛组织过程中将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可复用材料以减少资源浪费(电池、纸杯、塑料等)。比赛结束后,组委会将立即对赛道上布置的路标和垃圾进行清理。”
这第一句话体现出了“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的理念,这个理念来自西方,正广泛应用于户外运动活动中,但在其他领域仍有缺失。接下来的这句话表现出组委会的责任感,他们保证要做一些事情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些条款正在中国的许多赛事中变成一项标准,然而,对于穹景体育—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宁海越野挑战赛、宁海越野跑节、西湖越野跑节的赛事运营公司—的CEO大宝来说,只有LNT还不够。
“我的理解,LNT仅仅是户外环保基本标准,因为越野跑比赛往往是大人流、大物流的活动,有些LNT细则适用,但远远不够全面。”大宝在我演讲之后跟我聊起来,他认为像玉龙雪山这样的比赛需要引入比“无痕山林”更加深入的环保细则,而且“比赛中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改进环保细节,包括教育参与者”。
关于人们本就该在户外活动中的行为表现,LNT原则提供了最基本且理想化的指导。简单地说就是,教导人们在亲近大自然时应该保持它的原样。捡起赛道垃圾、收回赛道路标,都是一场比赛中理应执行的最基本的标准。如VIBRAM香港100、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的组委会要求参赛者自带可复用折叠水杯、不提供一次性纸杯的做法,也是可取的。大宝的宁海越野挑战赛可能将走得更深远一些,在下一届比赛时将规定:禁止携带和使用手杖,以保护赛道沿路重要的植物物种。
然而,这些行动并不会让一个地方变得更好。在这个被环境问题困扰得比以往更紧迫的时代,改善环境—不只是不去伤害—才是最需要的。
环境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环境教育,是朝着改善现状努力的一个途径,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大宝和马德民们均认同这一点。马德民说:“不单纯教会人们认识花鸟鱼虫,我们还需要有环境公民意识,重视和监控我们生活的环境。雾霾指数监测和发布不就是公众争取来的吗? ”自然教育的必要性将高于单纯的知识教育,教育和团结人们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
我在丽江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前的演讲不过是小试牛刀,赛事组织者们试图在提高环保意识与教育这件事上成为更加积极的角色,但他们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需要环保组织的专业协助和具体指导。” 双廊越野跑比赛的赛事协调员黎明说道,“我们计划与相关环保组织合作,在赛道沿途的村庄等处,对相关环保理念和做法进行宣讲。”
今年6月,双廊越野跑比赛和大理当地的环保组织云山保护(研究以长臂猿为主的云南生物多样性)合作,尝试将环保理念延伸到他们的比赛中。这也是云山保护第一次在越野赛现场做活动,展出他们的工作成果、和不同的参赛者交谈。“不过,我觉得传播效果还不太够,”来自云山保护的镜羽说道,“其实越野跑选手对长臂猿的兴趣并没有很高,这可能和展板不够吸引人有关。我们仍希望能够和越野跑爱好者们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再来做宣传。”
未基于战略意识与策划、也未带来任何实际行动的教育,除了唤起教育者的愧疚心和娱乐观众之外,达不到什么实质目的。我们本该怎样怎样,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真心想保护环境的赛事,需要有战略意识统一的后续合作跟进,与当地那些有具体行动的环保组织一起,给它们提供支持,落到实处地改善当地情况。至于那些打着“环保”的幌子只是为了宣传品牌形象的赛事组织,是不道德的。像云山保护与双廊越野跑比赛这样的合作,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也仅仅是跑步团体迈向有意义的环保的第一步。
鉴于此,国内越野跑圈需要实施战略性的“三步走”,才能有效地支持和保护给跑者们带来快乐的大自然,那就是:教育,外延,行动。
“三步走”之教育
教给大众一些他们以前未意识到的问题,使他们相信个人与这些问题之间存在关联,是发生改变的重要课题。

“我们因为热爱山野才有越野跑。”大宝说,“环保涉及到我们这个行业是否能健康发展,涉及到是否能让更多人参加户外运动,涉及到社会是否能尊重户外体育行业。”为了让更多的赛事组织者和跑者加入环境保护,展示他们自己与保护之间的关联是重要的第一步,也能构建可持续的赛事体系与文化氛围。既然有许多跑者已经从那些被保护得不错的越野赛举办地(比如亚丁、高黎贡、雅拉雪山、香港等)获得了愉悦的体验,那么向他们宣讲大自然如何令户外运动受益就不会很困难。
2017宁海越野挑战赛举办前后,穹景体育联合Way To Crest发布了一系列介绍宁海当地动植物的文章。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把参赛者与他们跑过的赛道环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更进一步想,教育跑者不仅包括“什么是被保护的”,还应包括“谁在保护”,以及“为什么确保可持续保护更加重要”。
为了做到这些,赛事组织方应该找出与举办地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如果说云山保护与双廊越野跑比赛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那它与高黎贡超级山顶赛就应更加深入,因为该赛事举办地正是云山保护致力于保护的新命名物种——天行长臂猿的栖息地。这样一来,高黎贡超级山顶赛其实可以在赛事期间同时举办大量相关推广活动,给赛事带入一层“环保”意义,云山保护也得以通过该赛事接触到大众跑者。
公平地讲,这并非新鲜理念。今年3月,一位云山保护的志愿者(网名agirlfromeastlake)自费来到高黎贡超级山顶赛现场。由于她没有在赛会展示区获得官方的展位,只能靠分发小册子和收集选手签名来宣传和支持天行长臂猿保护项目。当然,效果不尽如人意,没有组织方的背书或支持,“仅仅靠分发小册子改变跑者的行为和理念,实际上可能性比较小。”教育要做好,需要赛事组织方的官方支持和合作。
“三步走”之外延
教育之后,便是外延。教育达到的最好效果是,通过越野赛事接受到环境教育的跑者,能成为推广环保理念的潜在代言人。正如黎明说的那样,“尽可能地带动周围的人一起来参与环保, 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带动村民、游客一起来参与环保。”赛事组织方若有意成为环境友好型赛事,大可想出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让参赛选手传播正面且必要的环保信息。比如,推一推当地环保组织拍摄制作的短片怎么样?跑者们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分享,之后获得赛事主办方的奖励,比如一件纪念T恤。几乎每个赛事都能找出相关的话题加以创造性地发挥。
回到高黎贡超级山顶赛,他们目前的LOGO和T恤的图案是一个山峰轮廓,没什么特别的,看过就忘的那种,如果改成一只天行长臂猿的形象就不同了,那會兼具独特性和纪念意义,同时推广了与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紧密相关的极危物种的大众认知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存150只),它们亟须受到关注与保护。要别人改LOGO似乎是一件大事,不过一个独特而有辨识度的、与目的地密切关联的LOGO,其价值将超过改变所付出的成本。
另一场比赛,龙腾亚丁越野跑的LOGO,也有一个山的轮廓,它体现出赛道所处的位置,还有点道理。青藏高原上的气候变化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快3倍。在亚丁,气候变化让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山的冰川融化,不知赛事组织方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带出这个新闻呢? 如果不能,可不可以拿出一小部分经费赞助一年冰川调查呢?假如山上的冰川不复存在,人们是否还会来到亚丁?越野赛事通过大量跑者和过往的合作伙伴所形成的力量与资源,在做外延方面比那些环保组织要强得多。
“三步走”之行动
最后,在教育和外延之后,赛事与跑者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善他们享受这项运动的地方。一方面,积极与环境保护NGO组织达成合作,作为正式的公益合作伙伴去帮助他们筹集善款。另一方面,便是要求参赛跑者们拾起赛道上遗留的垃圾,甚至可以专门组织一些以净化山林为目的的比赛,以捡拾垃圾的量为评判标准而不是速度。另一种方式,就像马德民在2018 VIBRAM野性祁连越野跑系列赛的做法那样,把赛事产生的垃圾分为可生物降解和不可生物降解,最后运到有能力处理和回收垃圾的地方。当然,这些解决方案所产生的短期效应,在越野赛本身创造的最严重、最紧急的问题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越野赛固有地要求大部分参赛者从住所飞到遥远的目的地来比赛,虽然并不常被提及,但航空交通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一大因素,在全球变暖中起到5%的作用。那些受欢迎的越野跑赛事,依赖的就是壮丽的雪山美景,吸引大都市的跑者来参赛。这是越野赛与环境保护之间最大的不言而喻的悖论之一。
这里有个算法。根据最新的世界银行数据,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为7.5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如果一位身在上海的跑者一年跑两场比赛,比如一场在丽江一场在亚丁,那么,他/她每年就要多增加1.4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现实,对于每一个试图宣称“环境友好型赛事”的组织方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不过,有一种正在快速发展的解决方法:碳抵消(carbon offsets)。能够帮助人们减少对气候带来影响的碳抵消体系已在崛起,简单来说就是,你要为自己排进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买单。举个例子,捐钱给云南的植被恢复项目或者给甘肃的防风林建造工程,用来抵消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国际上开始涌现出许多机构,专门计算和抵消旅行者的排放量:去一趟丽江和亚丁所产生的排放量,支付78元人民币(或者再多一点)就可抵消了。在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被认可的系统来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也将会有。我们正在进行着。
再小的行动都值得
中国户外运动中,越野跑是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值得欣慰的是,创造这样的增长背后的组织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行业应该对环境报以尊重和保护。然而,为了让“环保”一词不再只是一句口号,组织者们需要一系列以教育、外延和行动为目标的前瞻性的战略合作。“一旦失去环保,”黎明跟我说, “越野跑也将失去它本该有的存在意义。”
说回丽江那场越野赛,在往回爬了大约20米之后,我找回了那个丢失的水壶。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比赛中最可怕的错误之一,但是值得。如果我把它留在那儿,我不仅成了一个伪君子,还会后悔终生。此外,我的害怕也证明是杞人忧天:我保住了排名第二的位置。把越野跑照进现实来看,创造积极的环境影响看似艰难,但抓住每一次行动的机会却是值得挑战的。其结果不仅对这项运动,还有我们地球的生存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