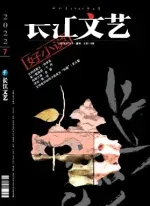在街上行走
□范小青
收旧货的那个人,戴着一副眼镜,穿得也比较干净,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大家这么说的时候,他总是笑笑,然后说,我什么知识分子,我小学毕业,初中只念了半年。
他脾气温和,举止也文雅,他总是将收来的旧货,认真地分门别类,然后小心地捆扎好,地下如果留下了杂物,他会借一把笤帚来,顺手替人家打扫一下,然后就把旧货扛出来,搁在停在门外的黄鱼车上,搁得平平整整,他说,放整齐了,可以多放一点货。
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收旧货,然后将收来的旧货卖到废品收购站,慢慢地,时间长了,他也知道有些旧货可以不卖到收购站,它们虽然是旧货,但还不是废品,可以不到废品站去论斤论两,可以找一点其他的买主,比如一些开在小街上的旧书店,当他带着些旧书进去的时候,老板的眼睛亮起来,精神也振奋了,这时候灰暗的小书店里,就会发出一点光彩来,还有一些晚上沿街摆旧书摊的人,对有些尚有价值的旧杂志和旧书,也一样愿意按本论价,不过他们的眼光,肯定不如书店的老板,他们开的价格,也是相当低的,当然,这总比按斤论价要强一些,做过几次交易以后,他就学乖了一点,当然后来他又更乖了一点,因为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摆书摊的人一转手,就赚了钱,所以以后他就自己来摆地摊,白天收旧货,晚上设摊,这样他抢了原来摆书摊的人的饭碗,那个人很生气,他自己也觉得这样不大好,就挪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晚上摆摊的事情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因为经常有城管的人或者其他执法的人来查处,常常偷鸡不着蚀把米,给罚了钱。碰到风声紧的时候,干脆就不敢摆出去了。
或者是在雨季,夜里总是阴雨绵绵,摊子摆出去,是得不偿失的,书刊被淋湿了,也不会有人在雨夜里去街头买旧书旧杂志的,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租住的小屋里,整理那些收购来的旧货,他没有电视,也不订报纸,漫长的雨夜,他可以看看旧书旧杂志。
还有一些是学生用过的旧课本、旧作业本,他有兴致的时候,也会翻开作业本看看,看到学生做的练习题和老师批的分数,还有一个学生写道:某某是王八蛋,老师也没有批出来,估计是最后本子用完了不再交上去的时候才写的,他不知道这个“某某”是这个学生的同学还是他的老师,他想如果是老师的话,就很好笑了,他将课本和练习本精心地挑出来,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以后都用得着的,他这么想着。后来有一天,他收购到一大堆旧笔记本,这是一个人写的日记,他起先也没有怎么在意,因为他觉得这对他的孩子以后读书没什么用的,他将这些旧笔记本置到另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当旧书旧杂志卖,只能到废品收购站将它们称了。
可是第二天他来到废品收购站的时候,收购站的秤坏了,正在修理,他就坐在一边等待修理,他那时候没事可做,就把手边的旧笔记本抽出一本来翻一翻,浏览一下,看了其中的一段日记,但是看了看后,他想,这叫什么日记,他有些不以为然,便不想看了。他将笔记本重新塞好,就坐在那里看修秤,后来秤修好了,他却有些疑虑,这么快就修好了,你的秤准不准啊?他问道。收购员说,不准你不要来卖好了。其实他平时也是经常遭到别人的质问的,怀疑的口气和他自己今天说话的口气是一样的,所以他也体会收购员的心情,也没有计较,就将一捆捆扎着的笔记本提到秤上,一称,九斤。收购员说,喂,这只能算你废纸啊,他有些不服气,这怎么是废纸呢,这一本一本的,应该算是书吧。收购员说,你懂不懂什么叫书啊。他觉得收购员今天火气特别大,但是让他把笔记本当废纸卖,他觉得亏了,我不卖了,他说,收购员就一屁股坐下来,说,不卖拉倒。
他将这些废品重新又置到黄鱼车上,他可以再换一家废品收购站试试,要是运气好,说不定有人会当旧书收购他的,他的黄鱼车经过红绿灯的时候,躲躲闪闪地避进一条小街,因为有个交警站在那里,像他这样的黄鱼车,虽然是有牌照的,但上下班时间规定是不许走大路的,他平时也是知道的,但今天因为卖旧货不太顺利,这时候他有点分心,就走到交警的眼皮底下来了,幸好正是高峰时间,交警正在忙着,没有来得及注意到他,他就拐到小街上去了。
小街上有一个旧书店,刚刚开门,店主就看到一个收旧货的人骑着黄鱼车过来了。店主看了看他的脸,似熟非熟,但店主还是微笑了一下,说,师傅,今天早嘛,今天有什么货?
他摇了摇头,就是一些笔记本,他说。
笔记本吗,店主说,什么笔记本?
好像是一个人的日记,他说。
他是有些无精打采的,但是店主的精神却渐渐地起来了,日记?他问道,写的什么日记呢?
什么呀,他说,就是一些流水账,早上几点起来,起来了洗脸刷牙也要写,水太凉牙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也要写,坐马桶坐多长时间也要写,早饭吃的什么也要写,早饭以后喝茶,是什么茶,哪里买来的,多少钱一斤,都写在上面,然后是什么,是来了一个送信的,送来一封信,他看了这封信,后来,有一个什么人也要看,他不给看,那个人生气了,反正,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
店主有一种天生的职业的敏感,他的鼻子已经嗅到了历史的气息,他已经不再矜持,甚至有点急迫地说,能让我看看吗?
他就从一扎笔记本中抽出一本给店主看,他说,本来我已经到收购站了,他要当废纸收,我说这不是一张一张的,这是一本一本的,应该算是旧书,他不肯,我也不肯,又带出来了,再去试试其他收购站。
店主的心思早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他只是应付着他,是吗,啊啊,这么应付了两句,店主已经看过了一段日记,他知道笔记本里的内容,至少是六七十年前的生活了,店主决定把它们买下来。
他惊讶地看着店主将一叠钱交到他的手上,这是给我的吗,他差一点问,但毕竟没有问出来,当然是给他的,当然是因为这一扎笔记本,肯定店主喜欢这些笔记本,或者这些笔记本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但他并不贪心,废品站的人,只肯给他几斤废纸的钱,现在他拿到这么多,他已经够满足了,至于店主可能会转手卖出多少,他无法想象,他也不再去想象,他知道那不是他的事情,他不懂这里边的规矩,也不懂行情,那钱不该他赚,所以他拿了店主付给他的钱,就可以走了。
但是店主转手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些日记没头没脑,既没有写日记这个人的姓名和其他情况,他在日记中偶而提到一些人名,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也无从考查起的,如果是名人的话,那就好办多了,时间再长,也总会有人知道的。后来店主又看出来,这些日记,是这个人许多日记中的一部分,是1936年至1939年这三年中的日记,那么这个人到底记过多少年的日记,从他的三年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记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日记,而且从1939年往后,还会继续记下去的,那么他的更多的日记在哪里呢,等等,都是待解的谜。
店主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考证,去寻找些什么,甚至还跑到外地去,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店主重新又想起了收旧货卖笔记本的这个人,店主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他说,我这真是守着和尚找和尚,指着赵洲问赵洲,舍近而求远了,于是他哪里也不去了,就守在店里等待收旧货的人再次出现。
不断有收旧货的人上门来问他收不收旧书,但是他始终没有等到卖笔记本给他的那个人。有时候他已经看到他进来了,但是经过一番盘问,才又知道这个人不是他要等的那个人。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卖旧货的来了,他坚信这就是他要等的那个人,他还记得他的身形和基本的长相。他问他,师傅,你来过这里卖旧书吧。但是那个师傅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来过,今天是头一回。
以至于后来他连那个人的长相都已经淡忘了,甚至模糊了,他一会记得他是瘦瘦高高的,一会又记得他是矮矮胖胖的。
晚报上,有一天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寻找一个收旧货的外地人。登启事的这家人家,老保姆将不应该卖掉的笔记本卖掉了,是被一个外地口音收旧货的人收去的,现在他们寻找这个人,希望能够追回不应该卖掉的东西。
有不少人看到了这条启事,但是与他们无关,他们并没有往心上去。店主那天也看了晚报,但是寻人启事是夹在报纸中缝里的,他没有注意到,后来偶而听人说起,但是谁也不记得那是哪一天的晚报,也记不清到底说的什么事,只记得是有人卖了不应该卖的东西,想找回来。店主再想去找那张晚报也找不到了,过了期的报纸,被收旧货的收走了,卖到废品收购站,然后又运到造纸厂,打成纸浆,再又变成新的纸头出来了。
现在卖错东西的事情多得很,有人将存折藏在旧鞋里,鞋被卖掉了,存折还到哪里去找啊,也有人把金银首饰放在旧衣服的口袋里,或者把情书夹在废纸里,这都是最怕丢失的东西,但是最怕丢失的又恰恰丢失了,而且都是很难再找回来的。所以,大家常说,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
店主的念头后来也渐渐地淡下去了,但他知道,这仍然是他的一桩心事。后来他生了病,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他还是把这桩心事交代给了自己的孩子,他希望孩子继续开旧书店,他说,只要书店仍然开着,就会有希望,那个人会回来的。
但是他的孩子觉得开旧书店没有意思,辛辛苦苦,又不能赚钱,他的女朋友也和他有一样的想法,他们商量了一阵,不久以后,他便将旧书店关闭了,开了个服装店,这是听他女朋友的主意开的,他们一起到浙江去进货,回来后就一起守在店里卖服装。后来他们渐渐地熟了,来来去去的路线熟了,事情该怎么做也都知道了,和那边批发市场里的批发商也认识了,有了交往,所以,有时候店里人手紧的时候,就不必两个人一起去进货了,而是他一个人去,也有的时候他有事情走不开,就他的女朋友一个人去。
但是服装店的生意也不好做,做了半年,一结账,除去开销,也没有多少盈余的,他的女朋友说,这样做到猴年马月我们才能结婚。他们坚持了一年,他的女朋友就走了,她说这个地方发展不起来,她要到浙江那边去发展。
女朋友走了以后,他也不再开服装店了,他将店面转租给别人做房产中介,他坐收房租,比父亲在的时候日子还好过。
做房产中介的人,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他的眼线耳目比较多,这是做中介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许多人都在有意无意中为他提供线索,这个人的朋友搬家了,老房子要出租,那个人的亲戚买了新房子,老房子要出手还新房子的贷款,或者谁家来了个外地亲戚,家里住不下,要租房子,等等等等,这其中有许多线索是有价值的。在别人听来,只是一般的家长里短聊聊天,或者最多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息而已,而到了房产中介人那里,一般的聊天,普通的消息,就变成了利润。
他租了这个店面以后,很快又和街上的左邻右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闲着的时候,总是在说话聊天,别人也知道他这一套,他们说,我们说话是白说,嚼白蛆,他不一样,他说话能够来钱的。当然,话虽这么说,但他那一套,他们看得见,学却是学不会的,有一次他只是听到一个人说某某街某某号有两室一厅,其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但是过了三天以后,他就拿到了下家的定金,又过了十来天,他就转手赚了两万。
其实不仅仅是说说话就能挣钱,他还要用脑子,他还要有水平,他还要有相当的思想境界。水平和思想境界从哪里来呢,锻炼出来,还有,可以从书上学来,所以他是很喜欢读书的,不管什么书,他拿到手都要看,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他觉得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
有一次他读到一个人的日记,这是正式出版的日记,一套有几十本,这个写日记的人,他并不知道是谁,因为他不是个名人,他的日记也是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小辈为了了却心愿,凑钱替他出的。在小辈写的后记里,说了这样一件遗憾的事,就是这些日记,是他们的爷爷二十岁至四十岁的日记,四十岁以后,爷爷就再也没有写过日记,遗憾的是,其中缺少了三年的内容,1936年至1939年的日记,被当年伺候爷爷的老保姆当废品卖了。小辈曾经费了很大的周折,但始终没有找到,所以现在出版出来的日记,是不完整不齐全的日记。
他心里也替他惋惜着,他也曾想象过,那个遗失了的三年,这位老人的生活中曾经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还想象,这丢失的三年日记,现在到底在哪里。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三年的日记,就在他的公司里边的那间小屋里,有一扇小门,拿一把大铁锁锁着,那是房主封闭隔开的,据房主说,是他的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是一些旧书,留着也没有用,丢又舍不得丢,放在家里又放不下,反而使整洁的房间变得杂乱,所以在店堂靠里的角落,隔出一小间,存放着。
因为隔掉这一小间,他收的房租就要少收一些,从前他的女朋友曾经劝他不要隔,可以使店堂的面积大一点,多派点用场,但是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隔出来了。
这些日子,这条老街上原先的店面都纷纷地在改换门庭,过不多久,就是旧貌换新颜了,街也兴旺热闹起来,收旧货的人有一次经过,都认不出来了,他还在房产中介公司门口站了一会,也没有想起这就是从前的旧书店。他毕竟不是这个城市的人,而且这个城市这样的老街小巷很多,在他看起来,这一条和那一条也都差不多,他只是感叹,怎么旧书店越来越难找,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他的利益。
但是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收旧货的人并不知道。那一次他得到一笔意外的收获,非常高兴,他十分庆幸自己在各种艰苦的工作中确定了做收旧货的工作,现在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收旧货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种意外的收获。当然,他不会傻傻地坐等意外好运的到来,他仍然每天辛辛苦苦地挨家挨户上门收旧货,再送到废品站去卖掉,有时候一天只能赚很少的钱,有时候还分文无收,或者被人骗了,还要倒贴掉一点,比如有一回收了一箱旧铜丝,送到废品站时,才发现只有面上是一团铜丝,下面的都是泥巴砖块,他就白白地贴了一百多元给骗子。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始终坚信自己的钱会积少成多的,有了这样的信念,他就能够不辞劳苦,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有一天他骑着黄鱼车在街上经过,有一个人挡住了他,问他有没有收过一叠旧笔记本,他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他告诉他,他几乎天天收到笔记本,有小孩的练习本,也有人家家庭的记账本,甚至还有好多年前的记账本,上面写着,山芋粉两斤,共一角,他当时还觉得奇怪,城里人怎么也吃山芋粉,而且城里的山芋粉怎么这么便宜,后来他才发现,那是二十几年前的记账本。那个问他话的人,后来就失望地走了。
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在一些无事可做的雨夜,他偶而也会想到这个人,这个寻找旧笔记本的人,是谁呢?他肯定不是来寻找小孩的练习本的,这样他就依稀回忆起有关日记本的一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情节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是有一些日记本,他还读过其中的一段,写的什么,忘记了,拿到哪里去卖了,也忘记了。反正,不是废品收购站,就是街头的书摊,或者旧书店,这些日记本是从哪里收购来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在哪条街巷里,他记不得了。这个人为什么要把笔记本卖掉,是有意卖掉的,还是无意卖掉的,如果是弄错了,他一定很后悔,日记是不能随便给人家看的,他虽然是个乡下人,但这个道理他懂,难怪那个寻找笔记本的人,一脸的焦急。如果他是记的和从前的女朋友的事情,流失出去,万一给现在的女朋友看见了,那就麻烦了。
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他从遥远的贫困的家乡来到这里,他也干过其他的一些活,后来觉得还是收旧货比较适合他,他就干定了这一行,慢慢地,有耐心地积累着资金,等积得多一些了,他就到邮局去汇款,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在家里等着他汇钱回去,他的老婆将他寄回去的钱藏起来,准备以后造房子用,两个孩子以后还要念书呢,他希望他们都能考上大学。
到邮局汇过款后,他怀揣着收据往回走的时候,经过洗头房,他就进去了,珠珠也知道他这几天该来了,他来的时候,珠珠说,来啦,如果她正闲着,她就会站起来说,走吧,如果她手里有客人在洗头,她就说,你等一等。
他总觉得珠珠对他和对别人不一样,有一些特殊的感情,珠珠却不这样想,珠珠说,哪里呀,我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只是那一回有些不同,因为卖了日记本,他发了一笔财,提前来了,那天珠珠看到他进来,奇怪地说,咦,你前天才来过嘛。
不过这件事情也和记着日记的笔记本一样,他已经记不清了。
选自《上海文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