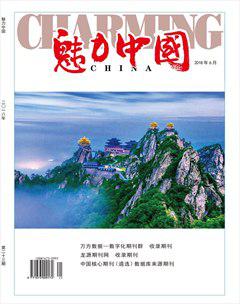“半悲剧”电影中的女性视角
敬霁晴
提及《小城之春》,除了钟阿城的小说原著,还有1948年由费穆导演执導,以及2002年由田壮壮导演执导的同名电影。两部《小城之春》因为年代、拍摄手法、主创人员等各种条件因素的不同而存在诸多差异,导演费穆对中国古典戏曲和话剧都有涉猎和研究,因此在他的电影中不难看出戏曲和话剧元素的运用。同时,他善于发现演员的本色,并且要求演员利用自身特点发挥演技。例如,他发现饰演周玉纹的韦伟在平日生活中喜欢用围巾与人开玩笑、打闹,因此,1948年的小城之春,在一场与男主角章志忱的对手戏中,费穆导演让韦伟利用纱巾当作道具,虽然台词“言有尽”,而演员却利用纱巾演出了“意无穷”。章志忱对周玉纹说“答应我,以后别再瞒著礼言见我了”,而玉纹却并不回答,只说“我有话问你”,对话的内容竟是玉纹质问志忱与妹妹戴秀的关系进展,言辞之间无不透露著浓浓的“醋意”。玉纹时而用手不断揉搓把玩纱巾,表面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内心暗潮汹涌,时而纱巾掩面,只露出眼睛的部分。“眼睛最易暴露一个人的情感”,因此纱巾挡住口部,表现出玉纹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娇羞、隐忍与无奈,然而眼底秋波流转却无法隐藏,类似戏曲表演中旦角常用的手绢,将女性情意表现得恰如其分。
另外,电影一大令人热衷讨论的特色是旁白的设置。类似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旁白多为第一人称与限知视角,或第三人称与全知视角的固定搭配,而费穆导演却打破传统,将女主角的独白作为旁白。很难界定她文学体的,独白式的旁白属于限知视角或全知视角,因为其中既包含实时描述,也加入了许多非现实的想象描述。例如,章志忱出场的画面,配合周玉纹的一系列描述性独白,彷彿她亲眼目睹并全程参与,然而这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因此可解释为周玉纹后期回忆中的想象,也恰好传达了周玉纹内心情感的反复流转。
许多以女性为视角的影视作品都多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旁白,为电影加入解释性信息的同时,增添了许多柔和细腻的气息。然而田壮壮导演2002年的《小城之春》却舍去了旁白的设置,他在纪录片的采访中做出生动比喻,说如果费穆导演的镜头距离演员“三米”,他则多用中全景,去掉女主角梦呓口吻的旁白,将镜头和演员保持“八米”的距离。田壮壮导演希望透过更加客观的视角讲述属于自己的《小城之春》。台湾摄影师李屏宾是2002《小城之春》,以及电影《花样年华》的摄像,他用洗练沉稳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两段无果而终的婚外情。《花样年华》中,女主角苏丽珍的丈夫和男主角周慕云的妻子自始至终都没有以真面目示人,电影透过特别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巧妙避开了次要角色,着重于描绘苏周二人的感情纠葛。
在导演的场面调度、摄像的拍摄安排和演员不同层次的表演之下,电影会在一个画面中讲述不同的故事。因此将电影的画面分割开来看,往往会得到不同的故事进展部分。例如中国大陆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就有“十六字诀”——“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即拍摄时,将敌人设置于画面的远处、暗处,用俯角拍摄等手法表现其阴险狡诈、人格渺小。同样的,费穆导演在拍摄时也用镜头语言加入了主观色彩,在拍摄周玉纹时,多为仰角和中近景,表现其女性形象在家庭、婚姻、爱情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然而在拍摄戴礼言时,则多选取俯角,或将其设置在画面的角落,所佔面积不大,以此表现其生理和心理的病态及弱小。
同样经典的,还有郊外泛舟的戏份。费穆导演选取的合唱曲目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悠扬婉转,当唱到“人们走过了她的账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一句时,镜头特写周玉纹回头看身后的章志忱。利用分镜头表达细节,或四人同画,却各怀心思。田壮壮导演则选择了曲调更加欢快的《蓝色多瑙河》,歌词在歌唱春天,不断重复“春天来了”,仅利用一个长镜头表达。
在妹妹戴秀生日后的戏份中,田壮壮导演则使用了更多的笔墨。“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章志忱对周玉纹唱起了歌剧,几番挑逗之下,才被妹妹劝离。戴礼言看到妻子和旧友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相谈甚欢,不禁有所顿悟。一人默默离开房间,竟兀自哭了起来。田壮壮导演安排这场哭戏,更加直白地展现一名体弱多病、性格古怪的中年男子,在看到一向冷漠待人的妻子枯木逢春般的举动后的无助与无奈。
在2002年的版本中饰演戴礼言的演员吴军曾和周迅合作出演了电影《生死劫》,饰演一位不断欺骗年轻女孩,使其怀孕产子然后转手出卖亲生骨肉的恶毒男人,电影全程穿插周迅的旁白,是完全以女主角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这部电影是李少红导演执导的,她也是2002年《小城之春》的监制,因此田壮壮导演的《小城之春》,不论是演员、画面、配乐,整体风格都带有明显的李少红寂寞冷静、细腻婉转、含蓄古典的色彩。李少红导演非常擅长拍摄女性题材的影视剧,例如电视剧《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以及新版《红楼梦》。《大明宫词》和《红楼梦》都有设置旁白,其中《大明宫词》是女主角太平公主的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红楼梦》则是第三人称客观性叙述。《橘子红了》的原著以秀娟为第一人称,讲述女主角秀芬和六叔的爱情故事,而电视剧则改为直接以客观视角讲述秀荷(即书中秀芬)的一生,婉晴(即书中秀娟)是一位个性活泼、未经世事、纯真无邪、家境优渥的年轻女学生,她与《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以及《小城之春》中的妹妹戴秀,甚至《城南旧事》中的英子都有著异曲同工之妙。以此类由孩童时期向成熟女性过度的少女为旁观者的无邪视角来叙述悲剧,则又添了几分朦胧却又清醒的同情与无奈。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你看,但周玉纹和章志忱之间的悲剧又似乎并无美好,亦无毁灭,他们都有机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战争将两人分离,命运使他们重逢,但最终阻挡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他们自身内心的道德谴责。因此我称这类没有发生死亡与激烈矛盾的故事为“半悲剧”,电影的开始一切平静却又沉郁压抑,男主角章志忱的闯入打破固有循环,吹皱一池春水,然而短短的几天内发生了许多事,最终却又只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了无痕迹。这种圆环式的叙事结构,始于平静,又归于平静,费穆导演以周玉纹戴礼言夫妇在城墙上的和解为结尾,而田壮壮导演则让周玉纹如第一次得到有客来访的消息时一样,继续在楼上的窗边绣花。面对波澜,无法掀起巨浪,只能重归风平浪静。田壮壮导演曾说:“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红楼梦》里的颓废也是此意味,虽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却也是在一片繁华过后才归于虚空。《花样年华》中周慕云的那句经典提问“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和章志忱的“假如现在,我叫你跟我一块走,你也说随便我吗”异曲同工,假设之中透露著深深的无奈。然而,在一个个爱情夭折的遗憾故事中,也存在大胆的提问,例如电影《海角七号》中男主角阿嘉的那句“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就是打破悲剧固定循环的创举。
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的对话常常简单几句,草草带过,丈夫内心其实是有交流渴望,试图唤起妻子内心的爱意,所以主动要和她谈谈,然而却只换来妻子一次又一次“尽责的敷衍”。越是生活起居的尽责,就越是心理距离的疏远,即越是敷衍。然而妻子却对访客章志忱有满腹柔情,即使答非所问,依旧心照不宣。这种交流常常出现在暧昧对象之间,周玉纹还有放不下的一段情,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周芝若对张无忌冷笑道:“咱们从前曾有婚姻之约,我丈夫此刻却是命在垂危,加之今日我没伤你性命,旁人定然说我对你旧情犹存。若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水性杨花。”张无忌急道:“咱们只须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作甚?”周芝若道:“倘若我问心有愧呢?”张无忌一呆,接不上口,只道:“你……你……”周玉纹亦是“问心有愧”,因此周玉纹“不甘”,而章志忱却“不敢”。“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周玉纹有勇气戳破这层纱,章志忱却被高山所阻,“不甘”和“不敢”的矛盾造就了这一出“半悲剧”。虽然讲的都是悲剧,但电影始终是导人向善,给人希望的,不管是揭露黑暗,还是歌颂美好,都是令观者珍惜自己的生活,因此《小城之春》虽充满悲剧意味,却在最终给予观众春之希望。正如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也塑造了坚强勇敢的女性角色,虽然内容沉重,但电影名称却道出希望的主题。
费穆导演说“没有比喻,就没有艺术”,因此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直白塑造强势女性角色的电影不同,《小城之春》《太阳照常升起》,以及上文提到的《橘子红了》《生死劫》等影视作品,极具艺术美感,这些婉转迂迴的故事即使虚妄,也都在虚妄过后,仍旧给人希望。这种带有小资情调的中国式半悲剧,仍旧以其温柔隽永的独特魅力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透著东方文化神韵的温情画卷——从小城之春看中国人文电影》 钮绮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一种守望 两种意象——新旧小城之春比较研究》 冯宜萍 冯皓 《保山师专学报》2007年7月 第26卷 第4期
[3]《电影小城之春的诗化风格探析》 刘一瑾 《语文知识》 2009年第4期
[4]纪录片《电影传奇》之《小城之春》 2004年4月3日CCTV1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