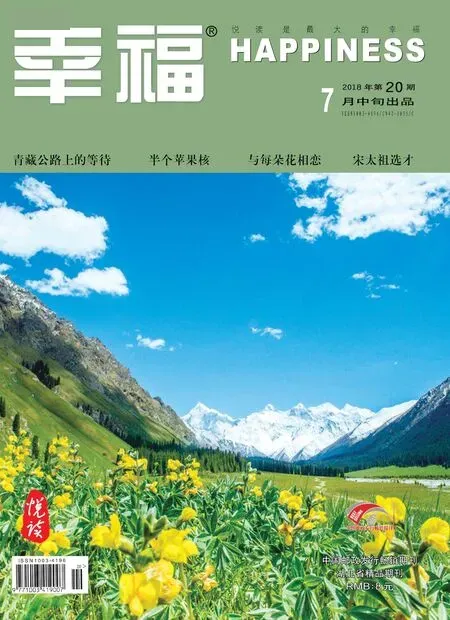老碾子
文/尹贻坤

记得年少时候,家家都很穷。村里没有电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石碾。用石头支起直径三米左右的石制碾盘,中间竖起一根铁质或木质的轴,一个直径和长度都约一米的石柱,称为碾砣,外面装上碾框,连在轴上,便做成了一个石碾。村民家的谷物,都要到石碾上磨成粉,然后过了筛子,细的留用,颗粒大一点的,继续在石碾上磨,然后再筛,如此周而复始。想来这石碾,便是改进了的舂米工具--石臼与石杵。
农闲时节,正是石碾最忙的时候。家家都要带着新鲜的谷物,一把扫米的小笤帚,两根木棍,陆陆续续来石碾磨面。因为石碾少,碾米的人多,所以要排队等候。若家里有事等不得,便将谷物放在碾旁,然后回家做事,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再回来排队等碾。或是提前差了小孩子来碾边看看,如果碾闲着,孩子就跑回家告诉大人,说“有碾”,于是赶紧带了谷物去磨;倘有人在碾谷物,便回家告诉大人说“没碾”,于是再等再看。
村里有一对夫妻,男人已近而立之年,女人要年长些,大了五六岁。所谓“女大五,赛老母”,女人大度,总是处处让着男人,疼着男人,如待儿子一般。小男人却持宠而娇,淘气得很,总也长不大。女人有时被男人气得急了,就顺手拿了扫碾的笤帚,对着男人屁股打下去--其实哪里是真的要打,不过做了样子,吓吓而已。男人便佯装害怕的样子,掉头跑出去。日子一久,街坊邻居都晓得了,常作笑谈。某日,男人又惹女人生气了,于是女人又拿了扫碾的笤帚,将男人追出门去。适值门外有诸多乘凉者,都看在眼里。男人觉得失了颜面,女人也觉得尴尬。为难之际,男人陡然灵机一动,回首对着女人喊道:没碾,你回去吧。女人会意,乐得顺水推船,应声答道:噢,没碾啊?那我回去了。随即回身踱进自家院里。男人也笑着跟了进去。乡村的生活,家常的日子,虽然清苦些,却过得有滋有味,明明艳艳,如天边的七彩虹霞,本是平平常常的水滴,因了阳光,亦变得多姿多彩。
石碾好像专为女人而设的。来磨面的人家,十之八九必有女人。印象中仿佛每次路过石碾,都会看见女人在推碾磨面。记得有一首诗,不知何人所作:“清晨起来过山庄,谁家女子碾高粱。汗渗粉面花含露,糠扑峨眉柳带霜。”农家小女娇美可人的模样。想来若有佳人相伴,纵然推碾辛苦些,也情甘意愿了。记得我们那时上小学,散学回来,倘看到邻家大娘或是奶奶在碾米,就会将书包丢在一旁,跑过去帮着推碾。这时大娘或奶奶便会嘻嘻笑着,夸道:这娃懂事,比小狗强多了,没白疼。说着话,眉眼儿满满的爱意,心里也是欢喜的。我们也会愈加卖力,以证实确比狗儿强了许多。那时的天总是那么蓝,水那么绿,清贫的生活却简单而美丽。
有时推碾的也会只有男人。村里有一刘姓男人,幼时干活伤了腿,残疾了,走路一跛一跛的,人都称他“刘二瘸子”,快四十岁了,无妻,跟着哥嫂过日子。另有一老者,姓张,亦是瘸了腿,走路如刘二瘸子一样,至耳顺之年,却丧了妻,独居生活。某日,刘二瘸子独自在石碾上磨玉米面,恰好张翁路过,见了,径直走上前来帮着推碾。两个残疾人,一瘸一拐地推碾,如两条相濡以沫的鱼,半是凄凉半是暖。如这早春,乍暖还寒,却已甘霖脉脉,润物细无声。有路过的人见了,先同年长的张翁打招呼,张翁逗乐道:你看我学刘二瘸子走路,像不像?周围人听了,皆忍俊不禁。彼时早有人已上前帮着推碾了。那时人们的心里都明明朗朗,澄澄澈澈,无一点尘埃,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老碾,如时光的河,流过那些难忘的岁月。从前推碾磨面的日子,仍历历在目,人们都不慌不忙,慢慢走着。从前的日色也慢,看着太阳慢慢地升起,慢慢地落下。那些贫穷而美好的日子,甘甜,温暖,如春日里满树的槐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