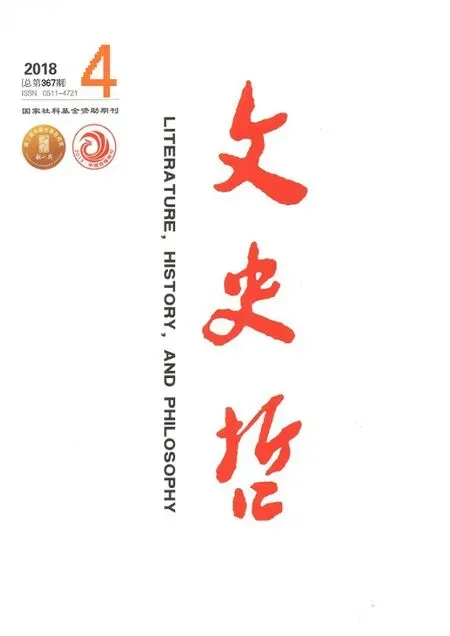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唐文明
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关于理由与原因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原因属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解释,理由则属于对历史事件的意向性解释。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差异的对比,可参见[芬兰]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一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既然对秦政的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君主立宪派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往往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比。如王韬在发表于1874年的《变法》一文中说:“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4页。言下之意,周秦之变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是当下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而构成变法的一个内在理由。又如宋育仁在为陈炽1893年出版的《庸书》所写的序中说:“中国数千年之基,开务于尧舜,集成于孔子,先王之政,备于孔子之书,为万世制作。秦废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汉虽稍复经术,而政规已定,博士依违,莫敢正驳,六经治世之大律,迁流为文词帖括,无所用。习其书而亡其意,学术益卤莽灭裂。及其从政,舍经术而学于吏胥,在上者察其果所无能,则弃士流而专用市侩。”*宋育仁:《庸书》序,见《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页。陈炽在《庸书》正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黄帝以来,重贤累圣,文章功业震古烁今。至于秦而天下之祸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经春秋战国之乱而大半凌夷,及秦政并兼,鞅、斯变法,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澌灭净尽而百无一存。天恻然闵之,于其间生一孔子,宪章祖述,删诗书,定礼乐,表纲常名教之大,以维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数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第7页)这里不仅将“秦废先王之道”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变革的一大关节,而且明确指出汉代虽然“稍复经术”,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同样是言远而指近,意在直面当下的处境而鼓吹变法。
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来刻画中国历史,这个看法其来有自,在有清一代,代表性的论述首推作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这样论断他所说的“古今之变”:“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页。在黄宗羲看来,与“恻隐爱人而经营”天下的古圣王相比,秦以来的君主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一家之私产,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以三代为理想的政教典范,而且在于否认秦以后的任何时代在根本品质上能与三代相媲美,还进一步认为至元代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而是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的观点,或如萧公权所说:“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4页。
就更远的思想渊源而言,黄宗羲的看法来自宋儒。宋儒普遍有回复三代的主张,以三代为切实可行又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认为秦以后的时代——包括汉、唐在内——在根本性质上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以至于魏源曾基于他的敏锐观察说,“宋儒专言三代”*魏源基于对历史情势的考量指出三代的制度不可复,比三代更早的上古之风亦不可复:“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阔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9页。另外,余英时亦以“回向三代”刻画“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参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84页以下。。宋儒何以专言三代?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必得关联于理学的兴起才能获得恰当、充分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三代作为政教典范确立于孔子。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三代理想的再次提倡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在宋代以前,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在汉武帝时,钱穆曾就此概括说:“汉廷学者,至武帝时,几无不高谈唐虞三代,而深斥亡秦者。”*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3页。钱穆并不认为汉武帝所为是真的回复三代,因此他特意申明说:“而汉武顾自以为唐虞三代,不知其仍为亡秦之续也。”考虑到钱穆反对把秦以后的君主制定性为专制,他的立论分寸仍值得认真对待。简而言之,钱穆的历史理解仍然深受黄宗羲的影响,即重视宰相对于君主的制衡。此义亦为晚清一些士人说绍述,如汤寿潜的《危言》中有《尊相》一篇,即发挥黄宗羲对宰相制度的高度肯定。汤寿潜主张宰相应当从官员中选举产生,而不应像原来那样直接由君主任命。对此,熊月之总结说:“汤寿潜心目中的宰相,既有很大权力,又经选举产生,实际上已和代议制度下的内阁首相相差无几。”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宋代亦标榜“以儒治国”,以至于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因而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再次被大力提倡。

既然三代理想构成批判秦政的基础,而这一点也早已是儒门共识,那么,对于生在宋代的儒者来说,以道观史的关键就落在如何评价汉、唐的问题上。在朱熹与陈亮关于汉、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程朱一脉理学家以道观史的要点与识度。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认为汉、唐纯是功利,无道德可言,因而绝不能在道之流行的高度上肯定汉、唐,于是他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答陈同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3页。若要继续追溯,汉、唐的功利性质其历史根源仍在于秦政,如他曾论及后世为何不肯变更秦法时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189页。所以我们看到,朱熹论断汉、唐只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除此之外再不肯有更高的评价。
前文已经说到,回复三代的倡议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但是,仅从宋廷重视儒术这一点并不能充分解释程朱一脉理学家何以郑重其事地将三代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教理想。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才说得透。”*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20页。这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朱熹看来,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中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直至二程才说透了的“理”呢?换言之,理学家凭什么觉得他们能够回复三代?他们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其根本信心来自哪里呢?
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这里包含的独特看法就是很多人自以为熟悉但其实并未深究的理学家的道统观念: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至周而亡,孔子在“道不行”的处境中开出了圣人之教、圣人之学而为孟子所接续,之后中断既久,直至千载以后又为程颢等人所接续。那么,程颢等人如何接续孔、孟所传圣教、圣学呢?答案当然是理学的发明。
理学的发明其实是理学家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根本信心所在,这里的思想关联可简述如下。首先,理学家依据经典,对于三代如何可复提出了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其实现端赖于圣王的功德;圣王成就功德的途径是通过行仁政以养民、教民,圣王为教养民众而创设的核心制度以井田、封建与学校为最要;仁政必本于仁心,故而美德的培养——不仅包括君主的美德,也包括士大夫官僚和普通民众的美德——是行仁政的紧要处*这个理解可从多部经典中找到根据,但很显然,《孟子》中的“仁政”思想与《大学》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可能是最直接、最明白的。此外,关于圣王的制礼作乐,从功能来说在于寓教于政,从过程来说则在治功之后,如《乐记》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井田、封建、学校、礼乐等多种仁政制度,共同构成所谓“三代之法”。。其次,理学家以挺立教统、学统来定位孔子的意义,认为孔子开创的圣教、圣学为回复三代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由此发展出一个衡量历史的价值标准,形成一个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既然圣贤对于三代理想的实现不可或缺,那么,对于后世来说,想要再次回复三代,就必须有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作为依凭;孔子正是提供了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而为孟子所继承、发扬,但孟子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无人能够继承、发扬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因而这些时代在根本上无法与三代相提并论,即使像汉、唐那样以功效观之多有可观之处亦不例外。最后,理学家正是以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定位理学的发明并指出理学之于回复三代理想的重要意义:直至二程才真正将孔、孟以成德为主旨的圣教、圣学发明、开显出来,此圣教、圣学由隐至显的发明为三代理想的回复显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朱熹是理学家道统观的最后确立者,这里就是站在朱熹的位置上来叙述。。
概而言之,正是理学的发明使得理学家觉得把柄在手,颇为乐观地提出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这是理解理学家弘教行道之思想路线的要点所在。理学家赋予理学的这种独特的政教意义是“宋儒专言三代”的思想实质。从弘教行道的行动路线来说,可分别出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而以士子学人师徒间相传授、相修习此圣教、圣学为践行之本*此处笔者修正了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典型的表述来看,显然对于余英时所说的上行路线,“致君行道”是比“得君行道”更为恰当的一个的概括。。
晚清西风袭来之际,士人仍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表明源自宋儒回复三代主张背后的历史观念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即使弘教行道的政教路线并非清儒经世致用的共同取向,以道观史仍是他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共同方式。不过,晚清那些较早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有一定了解的士人在使用三代观念时因着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而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明显是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为惧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24页。他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述自然是在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对比中展开的:“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像王韬这样将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与三代相比拟,在甲午之前仍深深浸淫于儒教精神世界、对西方政治制度和运作又有一定了解和较高肯定的士人,是比较多的*可以加入这个名单的士人还有很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当时或后世影响较大的还可举徐继畬、郑观应、汤寿潜为例。徐继畬在1844年出版的《瀛寰考略》中赞扬华盛顿(译为“兀兴腾”)“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虽然美国并非君主立宪制,但徐继畬显然仍视华盛顿为君主,因而特别着意于他不以国为己之私产。引文见《瀛寰考略》卷下,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郑观应在1875年基本成书的《易言·论议政》中认为泰西上、下议院之设“颇与三代法度相符”,于是提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倡议。引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汤寿潜在1890年写成的《危言》中引用了徐继畬对华盛顿及美国宪政制度的赞扬,并就迹论心,比拟于尧舜三代,并发挥黄宗羲的观点,认为三代以后,“君日尊臣日卑”,且此趋势莫甚于明清,已开后来梁启超《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之先声。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195页以下。另外,像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的著作中也都提及三代以比拟他们所了解到的西方政治。关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刘明:《西学东渐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但我们也不应当将这种比拟作过分夸大的理解,仿佛说到底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士人因不懂中西之异而流于比附。其实他们在西方政治制度和运作中发现的“三代遗意”,主要在君民一体这一要点上。关联于前面说过的“宋儒专言三代”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思想脉络:既然三代理想实现的关键在于君民一体,而秦以后的“尊君卑臣”使得君民隔绝,无法达到君民一体,既然在君主的贪欲面前,即使有理学成圣成贤之教也不能奏效,无法单纯通过德行修养实现三代理想,既然来自西方的宪政制度及其实际运作能够达到君民一体,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秦以来愈演愈烈的“尊君卑臣”的问题,那么,没有理由不将宪政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如果说这个刻画特别强调了西方优良政治中宪法的意义,那么,还必须指出,宪政背后的基本理念正是后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流布于中土的民权观念。这也意味着,如果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民权得不到真正的伸张,也就是说,君民一体无法达到,那么,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熊月之说:“将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故事相比附,这在近代也具有普遍性,前起魏源,下迄康有为,都是这么说的。”可见,对于这些主张变法的士人以三代比拟西方现代政治,他是从民主而非宪政的侧重点来理解的。引文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158页。。这就是酝酿于晚清时期的新的政治思想脉络,作为摆脱秦政的应对方案而被逐渐提出并付诸行动*如果考虑到对于宪法和民权的重视非但不应排斥、更当高度评价美德修养传统之于政治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应当在重法、重民的基础上再加上重德。。
二


历史进化论的引入是理解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所在。康有为与严复都明确基于历史进化论而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基于历史进化论改写了《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运》的“大同”、“小康”说,在这个新的思想方向上处于起点的位置,以至于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72页。严复也服膺历史进化论,而以自由民主为历史的归宿,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对于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影响巨大,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中,尽管具体观点多有不同,但都有一种基于进化论而提出的历史目的论作为他们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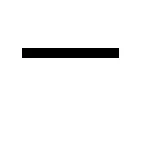
在这种根本性转变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古代经典中圣王叙事的另外两种政教理想被挪用来为基于进化论而提出的新的历史目的论背书,三代则因理想性不够而遭到贬黜乃至废弃。首先是敷陈于《礼运》开篇的大同理想,在晚清被很多人挪用来刻画世界历史的最后归宿。前面已经说明,即使像宋代理学家那样觉得把柄在手,有弘教行道的高度自信,也不过是以三代为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从不敢蔑弃小康而轻言大同。但是,在古今转换的端口,因着西风的东来,尧舜之大同遽然取代了三代之小康,一跃而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了。对于《礼运》开篇的大同叙事在晚清的影响,熊月之总结说:“这段话在整个近代大放光彩,农民领袖洪秀全把它全文录入《原道醒世训》中,并据此创编了《天朝田亩制度》;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写了《礼运注》和著名的《大同书》,对此大加发挥;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将此一再引用,并全文抄赠友人;无政府主义者特地写了《礼运大同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39页。其实要论中国现代思想激进化的根源,恐怕非得追溯到历史观念上的这个巨变不可。
被挪用的另一种来自古代经典的政教理想发明于老、庄,后世不断有继承者,在魏晋时期特别被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所发挥。这个思想典范的特征是,在治世之理想时代上,被回溯至尧舜以前的羲农时代或更古;在思想实质上,则表现为无君论。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无君则庶物定,无臣则万事理。”鲍敬言则说:“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而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葛洪:《抱朴子·诘鲍》,《诸子集成》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90页。孟子以“无君”批评杨朱,陶渊明所记桃花源的社会特征是“虽有父子无君臣”,说明杨朱、陶渊明也是无君论的服膺者,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儒者的政治关怀——对〈桃花源诗并记〉的解读与阐发》,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1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外,《伯牙琴》的作者、生活于宋末元初的邓牧,也是这个政教理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无君论从根本上批判君主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僚制度,在晚清自然能够被用来为民权思想张目,但其思想的激进性决定了其更易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如1907年8月10日在何震主办的《天义》第五卷图画栏刊登了一幅老子像,图下注“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即视老子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明家。又如,1907年10月30日《天义》第八、九、十卷合刊载刘师培《鲍生学术发微》一文,开篇即以“废人治”的无政府主义论定鲍敬言的思想:“中国舍老、庄而外,学者鲜言废人治。至于魏晋之际,学士大夫多治老、庄家言,而废灭人治之昌言,实以鲍生为嚆矢。”*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49页。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与后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史关联,可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政教理想,分别对应于经典中的尧舜、三代和羲农,虽然旨趣各异,但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三者在反对秦政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随着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引入,对秦政的批判也有了新的把握和表达方式,此即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论断秦以来的中国政治。
直接以君主专制来论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肇始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政体分类关联于不同民族社会生活的整体精神,确立了政体研究的新原则。在他看来,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和以荣誉为原则的君主政体来自西方的政治传统,分别代表西方人的古与今,而以恐惧为原则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来自东方的政治传统。在分析中国的政治制度时,孟德斯鸠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礼教的特别之处,从而意识到单纯以君主专制来论断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其不恰当性,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论断,因而在以“混合政体”描述中国的政治制度后又说中国“也许是最好的专制国家”*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李猛:《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李猛揭示了孟德斯鸠以君主专制论断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时面临的矛盾和困惑,并通过分析指出,这一现象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无需多加说明,可以看到,以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来论断并批判秦政,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正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内在批判。不过,由于两种批判背后的历史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其思想归宿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虽然在话语层面旧典被频频挪用来说明新轨*对于新的思想归宿,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说得很明确:“18世纪之学说,其所以开拓心胸,震撼社会,造成今日政界新现象者,有两大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受其说而醉心焉,曰:其庶几以此大义移植于我祖国,以苏我数千年专制之憔悴乎?”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82页。。以最典型的“大同”说为例,现代以来,大同的话语可谓甚嚣尘上,但新话语中的大同无论从思想语境还是思想实质看都不再是原来的大同。历史观念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评价标准,特别就儒教传统而言,人伦的价值被大大削弱,尤其是人伦的政治价值,在新的历史观念之下几乎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应地,对于古代中国政教传统及其结合方式的整体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仍以梁启超为例,既然君主专制被认为是走向共和之前的一个相邻阶段,那么,基于政体进化的思想而对君主专制有所肯定就是必然的*如《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最后说:“凡国家必经此四级时代而后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国内无数之小群,泯其界限,以成一强固完整之大群,非专制不为功也。尧舜之有大造于中国,即在此焉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27页)就理而论,如果要让一个儒门服膺者认可尧舜之有功于中国在于建立君主专制,这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啊!。对礼教的评价也是如此。即使我们设想,梁启超充分领会了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并接受了他的看法,从而认为正是礼教使得专制时代的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专制国家,他也仍会像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所作的分析那样,认为除了地理环境因素之外,礼教客观上扮演了维护君主专制的重要角色,甚至认为礼教就是比西方式的“有形的专制”、“直接的专制”更难对付、更值得批判的“无形的专制”、“间接的专制”*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82页。。
三
摆脱秦以来一直未有根本性改变的君主专制政治,构成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思想动力。从欧美社会发展出来的共和主义的“两种具有紧张性的典范”,也同样规定了中国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一为激进的民主共和主义,主张建构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从而使人民成为唯一可能的主权者;另一则为宪政共和主义,强调法治观念以及相应的权力分立宪政体制。”*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页。依据这个分析框架,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差别,不过是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的差别:改良派主宪政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或可保留,并寄希望于民众的不断开化;革命派则主民主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必须废除,且在激进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有趣的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分析与批判在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的分别与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处以章太炎在评价黄宗羲时的前后变化为例来说明。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在晚清批判君主专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不待言。早年的章太炎也是黄宗羲的景仰者。据说,“太炎”二字即取自“黄太冲”的“太”和“顾炎武”的“炎”。在写作于1897年的《兴浙会序》中,章太炎盛赞黄宗羲说:“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异于明者,亦不得久存其社。乌呼伟欤!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1899年2月10日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书〈原君篇〉后》,一开篇即说:“黄太冲发民贵之义,官天下之旨,而曰天子之于辅相,犹县令之于丞簿,非夐高无等,如天之不可以阶级升也。挽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则一人之尊,日益骞损,而境内日治。太冲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19页。此段文字又见于《訄书·冥契》。另,在1898年《与李鸿章》的信中,章太炎标举黄宗羲“知君民之分际”。可见,这个时期的章太炎不惜以“圣”称赞黄宗羲,且同时从民主与宪政两个方向上理解黄宗羲的先知性洞察。
不过,应当指出,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章太炎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则是他在景仰黄宗羲的这个时期的一个思想变化的脉络,也恰恰涉及民主与立宪之间的路线差异与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张力。在1928年写作的《自定年谱》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条下,章太炎在谈到他与康有为门人的思想分歧时曾明确以王夫之的《黄书》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举:“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下),第755页。康门重立宪,太炎重民主,这是双方分歧所在。重立宪者重民权,但不以民主为保障民权之必由;重民主者必然重立宪,但又以立宪不能使民主真正落实为忧。
1907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短文《衡三老》,一改原来对黄宗羲的高度评价,认为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的意图是“将俟虏之下问”,因而与顾炎武和王夫之完全不能相比*此短文后收入《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这主要是从气节方面批评黄宗羲*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黄宗羲辩护,认为章太炎“俟虏之下问”的批评不合实情,因为《明夷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48页注。。章太炎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强烈批评见于1910年发表于《学林》的《非黄》一文,一开篇即以“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评价《明夷待访录》。针对黄宗羲提出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章太炎展开批评,认为黄宗羲“听于治法”的论调在实践中难免流于“听于乱人”。具体来说,学校制度与宰相制度都是黄宗羲阐发出来的三代之法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分别提出批评,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朋党产生的根源*针对学校制度,章氏批评说:“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遍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针对宰相制度,他批评说:“丞相既立,六部承其风指,则职事挠;不承风指,事相挈曳而不能辑。故立相则朋党至,朋党至者,乱法之阶。”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125、127页。。于是,在历陈听法、尚贤之弊后,他总结说:“举世皆言法治,员舆之上,列国之数,未有诚以法治者也。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好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129页。
联系同时期的其他文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章太炎何以改变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其实早在1908年7月10日刊载于《民报》第22号的《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一文中,章太炎就将黄宗羲与王夫之加以对比,以激烈的口吻批评了《明夷待访录》,可以看作是《非黄》一文的先声:
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固无可非议也;至其言有治法无治人者,无过欺世之谈。诚使专重法律,足以为治,既有典常,率履不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学校,使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荣?此则过任治人,不任治法,狐埋之而狐掘之,何其自语相违也?余姚少时,本东林、复社浮竞之徒,知为政之赖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术以自焜耀。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术,正与余姚异世同奸矣。*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15页。
从这段引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章太炎“非黄”的背后是对立宪政体的极度不信任,其实质可以概括为藉民主以批评宪政*朱维铮将章太炎“非黄”的思想转变关联于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的政见异趋,见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同样发表于1908年《民报》的《代议制然否论》一文中,章太炎以“恢廓民权”为念,对代议制大加鞭挞,认为代议制是“封建之变相”,“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311、318页。。与此相关的是,章太炎从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中看到了“超于尚贤党建者犹远”的因素,且出于平等思想对秦政作出一定程度的肯定:“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章太炎:《秦政记》,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64页。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章太炎在这里对秦政的肯定与前述梁启超在政体进化论的思想框架内对秦政的肯定其实意思差不多,二者都是以“恢廓民权”为念,所不同者在于,章太炎因为看到了代议制政治的可能弊端从而走向更为激进的民主主张,也预示了后来现代中国政治历程中民主压倒宪政的激进道路。